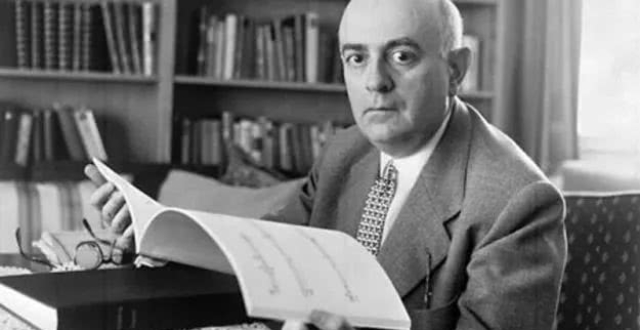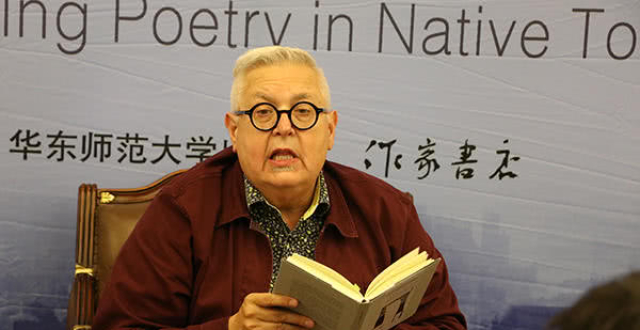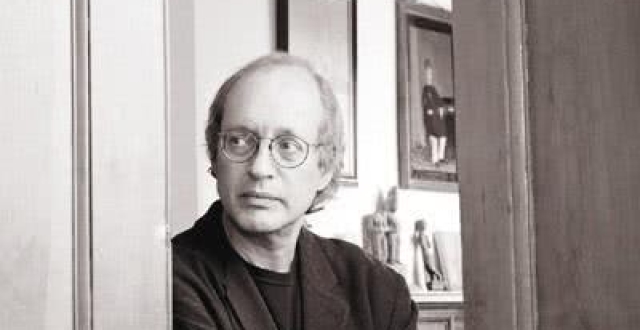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張進
費爾南多·佩索阿是一個個體,也是一個群體。這一複數性源自他寫作的最大特點——“異名”寫作。他創造出一百多個有具體職業、思想特徵的“異名”,並以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思想為基礎寫出風格迥異的作品。
這種“自我分裂”的傾向在佩索阿六歲時即有展現,十六歲時第一次以異名查爾斯·羅伯特·阿努發表作品。他認為,用“異名”寫作是他“對人格分裂和偽裝懷著持續而根本的傾向”,而“異名”的數量之多無疑反映出佩索阿自身的極度複雜性,以及他孤獨的深度。他將本體隱身於由“異名”組成的眾人之中,構建著文學史上罕見的複雜體系,又實現了對世界的逃避。
佩索阿筆下最著名的三位“異名”是卡埃羅、岡波斯和雷耶斯,其思想與創作風格各不相同。卡埃羅自然、真實,主張親近自然,雷耶斯則受過良好的教育,詩歌講究韻律,而岡波斯則是一名感覺主義者,對生活持有徹底的悲觀態度。在眾多“異名”中,岡波斯的思想是最靠近佩索阿的,儘管他們的人生經歷並無相似之處,但在看待生活的悲觀態度上,兩者最為接近。因此,了解岡波斯,也成為了解佩索阿本人的一個重要途徑。
近期,岡波斯(實為佩索阿)的詩集《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出版,借此機會,我們採訪了譯者楊鐵軍,以期通過呈現岡波斯的精神面貌、寫作特點等,挖掘出佩索阿複雜面目中的重要一面。

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1888-1935),葡萄牙詩人、作家。1888年生於裡斯本。生前以商業翻譯謀生,利用業餘時間寫作,至死默默無聞。四十七歲病逝時留下了兩萬五千多頁未整理的手稿,包括詩歌、散文、文學批評、哲學論文、翻譯等。佩索阿的作品世界由眾多的“異名者”組成。
對現實只能采取拖延的態度
新京報:佩索阿的“異名”之一岡波斯在詩集中大致展現了怎樣的精神面貌?
楊鐵軍:岡波斯隻信任感覺,所以想要用盡所有可能的方法去感覺,因為那才是生活的真實。現實對於他來說是不真實的,所以他在現實中永遠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岡波斯在想象中曾無數次是愷撒,甚至比基督更“人性”,比康德更能寫,但在現實中,卻在旅行的前夜收拾不好“行李”,永遠無法成行,處於一種絕對的“矛盾”之中。當然,這種“永遠無法出發”的旅行不可避免令人聯想到死亡。
岡波斯對現實只能采取拖延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生活從定義上來說,也許就是對死亡的拖延,所以他害怕生活,“感覺”是他唯一的真實,唯一的武器。而思想和行動,就是對感覺的背叛,讓人朝向死亡多邁了一步。
新京報:據說岡波斯可能是最接近佩索阿本人的,兩人接近之處主要表現在哪裡?
楊鐵軍:從表面上看,岡波斯年輕的時候是一個花花公子,留學蘇格蘭學海軍工程學,周遊世界,性格豪放恣肆,和佩索阿本人的生活毫無相像之處。但岡波斯應該是佩索阿想要成為,卻沒有成為的那個人。岡波斯回到葡萄牙後,陷入絕對的悲觀,對現實,甚至對自己采取輕蔑嘲諷的態度。這也應該是佩索阿本人的態度。
卡埃羅是一個“創世者”,在現實中不可能存在,岡波斯雖然在現實中有存在的可能,卻不是佩索阿本人的性格,但正因如此,卻成為佩索阿的“寄托”。所以,佩索阿本人對“岡波斯”有珍愛之情,一直到生命的後期,他還在不斷發展岡波斯。岡波斯後期的詩和前期的詩風有明顯的區別,幾乎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寫作風格有演進有變化的異名。

佩索阿詩歌手稿。
預演“後現代”生命境況
新京報:你說佩索阿的這部詩集具有“前瞻性的洞見”,具體如何理解這裡的“前瞻性”?
楊鐵軍:佩索阿採用了一百多個“異名”,每個“異名”都有自己的生平、寫作風格,異名之間還互相批評。佩索阿本人卻在這樣的異名系統中消失了。他所有想說的話都是通過“別人”之口說出來的,從佩索阿到他的這些異名是一條單行道。
從理論上來說,你無法從這些異名推導出佩索阿本人是“絕對真實”的。因為佩索阿根本不相信一個統一性的、本質性的主體。自我只能是分裂的。他就好像一個天文學意義上的黑洞,只能從周圍星體受限於它的吸引力推導出黑洞的存在,卻不能直接觀看。
從這個意義上說,佩索阿前瞻性地預演了幾十年後的“後現代”生命境況。因為後現代的基本前提就是從尼采的上帝死了開始,一直發展到“作者死了”,“文本死了”。在佩索阿那裡,傳統意義上的作者泯滅了,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作者”。文本也不是那種要構築作者主體一致性的有機體了,而是涵蓋了詩歌、小說、爭論、批評、小品文、諷刺、新聞、法律文書等各個門類,突破了多年後被後現代所摧毀的“文學性”。
新京報:這部詩集展現出的岡波斯對生活的思考,似乎是矛盾的。在一些詩裡,他的悲觀展露無遺,認為生活是虛無的,感到“倦怠”,“萬物皆夢”,但從另一些詩中又可以感受到他對生活的渴望,乃至欲望,你如何看待岡波斯的這種矛盾性?
楊鐵軍:岡波斯對現實生活是蔑視的,對自己在現實中的尷尬境地一方面悲歎、自憐,另一方面也是持一種嘲諷的態度。他悲歎自己不是一個蠢人,那樣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獵取生活。他悲歎自己只能是住在閣樓上的夢想家,而且連自己夢裡的“軍隊”都是一支敗軍。他在夢中無數次成為愷撒,但是在現實中卻永遠是失敗的。美好只存在於他失去的外省的童年。
這種矛盾性其實代表了一致性。因為現實的失敗,必然會寄托於夢,岡波斯的感覺主義也是一種符合邏輯的退守。相反,想象中的無所不能,“沉迷”感覺,必然導致現實的失敗。另外,岡波斯對所謂的成功是嘲諷的,對失敗他也是嘲諷的,沒有矛盾之處。換句話說,你這裡所說的“矛盾性”,在別人身上自然是矛盾的,但在佩索阿身上,卻僅僅是一個矛盾修辭,指向的結論卻是一致性。

《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費爾南多·佩索阿 著,楊鐵軍 譯,雅眾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5月版。
寫作的“直接性”是最重要的啟發
新京報:哈羅德·布魯姆將佩索阿和惠特曼相比,說“他是給‘自我’‘真我’以及‘我的靈魂’重新命名的惠特曼”。在這部詩集中,對這方面的思考也有很多,如詩句“不管我是什麽,不是什麽——全都是我。”岡波斯對“自我”的思考具體是怎樣的?
楊鐵軍:岡波斯雖然渴望“同類”,渴望於“同類”建立兄弟之情,但是這種惠特曼式的擁抱,在岡波斯那裡卻有拒絕的味道,因為“同類”太少,幾乎找不到,而惠特曼是那種擁抱一切的包容。惠特曼的自我是無邊的,有包容萬有的雄心。而佩索阿的自我的無邊只存在於想象之中。他對現實幾乎有一種潔癖式的厭惡。
新京報:除了情感和思想,這部詩集的技巧有哪些特點?你在序言中也說在翻譯過程中學到了一些具體的技巧,運用到了自己的詩歌創作。
楊鐵軍:佩索阿,尤其是岡波斯,對我們寫作者最重要的啟發就是“直接性”。一種迫切的、甚至是不惜一切的直接性。最諷刺的是,這種直接性,必須得通過一個虛構的人傳遞出來。但這也許是文學寫作最深奧的秘密。
這樣的直接性對一個中國作家來說很難,一方面是因為處境不同,文化性格不同,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命運是一個複雜的各種話語系統相互衝突的糾纏體。在這樣的文化命運中達到“直接性”也許只能以悲劇收場。但我認為直接性還必須是我們要為之努力的目標。從具體寫作上來看,“直接性”是一種能力,需要艱辛的付出才能做到。
我確實從佩索阿那裡學到了一些具體的東西,比如我寫於2006年的一首詩《比喻》,開頭是:
如果雨點落下來而不匯集,
不凝固,每個雨點都將成為個體,
好像河岸的鵝卵石,
那麽我們就會發現存放的困難。
還有一首詩《枝頭小鳥》的結尾:
許多年前我失去的一切
許多年後我通過你找回
就在那個不知名的枝頭
那個撲棱棱顫抖的枝頭
顫抖的枝頭
枝頭
最後三行依次遞減重複,造成了一種小鳥飛走、枝頭顫抖的視覺效果。這也是得益於佩索阿常用的“遞減重複”的手法。這些都是小技巧了。最重要的還是剛才說到的直接性,而那是很難學的,涉及一些根本的問題。
新京報:佩索阿幾個“異名”的寫作,有著很大差異。在翻譯岡波斯的詩歌時,你會比照其他“異名”如卡埃羅的詩,以求在譯文風格上產生明顯的差異性嗎?
楊鐵軍:在佩索阿這幾個詩人異名當中,我偏愛岡波斯的風格,似乎能達到一種我口寫我手的暢快。岡波斯的詩不押韻,形式不求整飭,所以有一種不容置疑的明晰,即使他表達的是猶疑。我沒翻過卡埃羅,假如我去翻的話,必然會反覆斟酌,給他找到一個漢語中能暢言的語氣。再比如雷耶斯的古典主義形式,還有韻律,也必須得反映在譯文中。翻譯一個不同的作家,必須體現他不同的風格。
作者 新京報記者 張進
編輯 何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