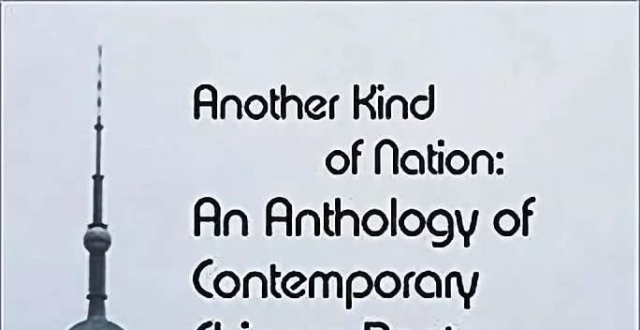談及戰後當代美國詩壇,約翰·阿什貝利(John Ashbery,1927-2017)是個繞不開的名字,甚至一度是核心人物。1975年,他出版的詩集《凸面鏡中的自畫像》獲得普立茲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為詩人贏得廣泛聲譽。詩人一直生活在紐約,直至2017年9月3日去世。

John Ashbery, PHOTOGRAPH BY BY LYNN DAVIS

近日,《阿什貝利自選詩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策劃出版,該書由阿什貝利從十部詩集裡,選擇了138首詩, 包括短詩、俳句、散文詩和重要的長詩。讀者和研究者可以對阿什貝利的詩歌創作有較完整的了解,進而觸發新的解讀。
作為後現代詩歌的代表人物之一,約翰·阿什貝利的詩具有驚人的力量,他的每一部詩集,如《一些樹》(由W.H.奧登選入“耶魯青年詩人叢書”,1956)、《網球場宣言》(1962)、《春天的雙重夢幻》(1970),還有那首著名的《凸面鏡中的自畫像》(1975),都在進行語言的實驗。這使得他的詩歌語言支離破碎,經驗材料混雜,邏輯斷裂、跳躍,頗有“語言的勃洛克繪畫”之感。事實上,阿什貝利本人也的確受紐約行動畫派的影響,曾在《藝術新聞》就職,他的詩歌和抽象表現主義繪畫淵源頗深。
這種“解構性的寫作”,對於譯者來說,無異於一座高聳的大山。詩集譯者、詩人馬永波在接受南都記者專訪時表示,翻譯難度給他造成的“智力壓迫”,曾經讓他失眠整整一周。但過後,恰恰是這種晦澀難懂吸引著他繼續翻譯,因為,“我想了解他晦澀背後的成因。”
——訪談——

“離開了阿什貝利,後現代詩歌便無從談起”
南都:這套詩集和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約翰·阿什貝利詩選》在內容上有何區分?能否介紹一下約翰·阿什貝利在中國的出版譯介史?
馬永波:2003年河北教育版的那上下兩冊的阿什貝利詩選,當時翻譯時基本是整體移譯,參照的是當時我手頭有的他的一些詩集,《一些樹》《網球場宣言》《山山水水》《片段》《春天的雙重夢幻》《三首詩》《凸面鏡中的自畫像》《船屋的日子》《正如我們所知》《影子列車》《一排浪》,翻譯時也沒有進行自己的遴選,基本原書有什麽就譯什麽,總體上可以算做是他詩歌的一個匯編。

而新版的這套雙語詩集,是阿什貝利的自選詩集,是他從自己從以往詩集中重新編選出來的精華本,這些詩集與上述開列的單行本是一致的,只是排除了《片段》這一本。具體篇目的取捨,兩者有相當大的差別,應該說,新版選擇的篇目數量要少一些,兩者重複的篇目也佔據一定比例,我沒有具體統計過。如果有學者有耐心就版本學進行研究,相信從後者能更好地看出詩人自己的取向。作為這種等級的詩人,他對自己作品和詩美學目標的把握,是非常清楚的,甚至超過了其他的選編者,能夠反映出作者最為內在的心靈線索和文學訴求。我相信,自選集更是“研究性”的選集,它面向的不僅僅是普通讀者,他對專業研究人員也具有重要的指示意義。除了新譯的部分,兩個版本重複的篇目,我也根據原文逐句進行了修訂,基本上等於是重譯,兩版相隔近二十年,我對文本的把握、資料儲備,乃至我自己對詩學本身的理解,都有了相應的變化,這些在修訂中也能反映出來。
在我大量翻譯阿什貝利詩歌之前,是鄭敏和趙毅衡翻譯的幾首引起了我的興趣,當然,對他的關注也是和我對整體上的所謂後現代思潮的興趣有關,紐約派畢竟是美國後現代詩歌的重鎮。除了這兩位,應該還有幾位譯者零散翻譯過他的詩歌,但我相信做過整體性研究的人不多。哪怕就我的翻譯而言,也只不過是阿什貝利在漢語中歷險的開始,這兩版的詩選,提供了一份研究參照的相對充分的資料,對他的更進一步的譯介與研究還有待展開,尤其是理論研究方面。
南都:你對阿什貝利的關注和翻譯是怎麽開始的?
馬永波:深入接觸阿什貝利的詩歌,應該是1994年,偶然得到了他的詩集《凸面鏡中的自畫像》,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此前的兩三年,我就開始為北師大出版社翻譯《1940年後的美國詩歌》和《1970年後的美國詩歌》,前一本中亦包含有阿什貝利的詩,但整本的詩集尚不得見。實際上我對英美詩歌的關注和翻譯,一開始僅僅是出於開闊視野的需要,還是為了自己的寫作增加營養,加之當時漢語中就已經隱約有了後現代詩歌的提法和實驗,我也想借此將“原裝”的後現代弄弄清楚,以資比較。那一年我用了隻一周時間就將這本兩千多行的詩集全部翻譯了出來,當然,也遭受到阿什貝利的晦澀和複雜帶來的智力壓迫,結果便是失眠一周的代價。
南都:也正是他的這種“晦澀和複雜”吸引著你?
馬永波:阿什貝利吸引我的地方,恰恰在於他散漫不羈和晦澀難懂,我想了解他的晦澀的成因,這必然涉及到他對詩歌的理解。他的解構性的寫作,當時對於漢語來說,還是很難消化的東西。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他詩歌中的經驗性和寬廣的意識範圍,這些都是偏重抒情的漢語詩歌所欠缺的。
南都:約翰·阿什貝利被視為自艾略特、華萊士·史蒂文斯後,最有影響力的美國詩人之一,那麽,他在美國現代詩壇大致處於一個什麽位置?
馬永波:戰後或者說當代美國詩歌,流派眾多,優秀的詩人也層出不窮,既繁榮,又呈現出也許本該有的“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狀態,各個流派和集群各行其是,探索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毋庸置疑,阿什貝利可謂是核心人物之一。
1956年,阿什貝利的第二本詩集《一些樹》便被奧登選入耶魯青年詩叢,從那時起,作為紐約派主要成員,阿什貝利便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態勢。尤其到了1990年代,在整個世界詩歌範圍出現了對20世紀現代主義詩學的修正與變革,尤其對於作為聯合思想與情感的意象徵詩學工具的修正,那其後的詩歌更具有包容性,能夠容納來自不同語境的異質性的聲音,意象往往與敘述、論說混合起來,並伴隨著哲學沉思與精確的事象觀察。很多詩人在不同的語言中出入,嘗試各種語言方式的可能性與極限,將語言的冒險與個人生活和公共世界重疊,甚至模糊彼此的界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阿什貝利,他詩歌中多重與多變的知覺標誌著當代詩歌的異質混雜,其跳躍性是對現代性“簡便的一致性”的一種抵抗。單從這一點上來說,阿什貝利可謂引導潮流的人物,而且不局限於美國詩歌,他的影響是世界性的,處於主流之中。離開了他,後現代詩歌便無從談起。
南都:阿什貝利自己曾說,奧登是第一個對他產生重大影響的詩人,這種影響具體怎麽體現?
馬永波:阿什貝利詩歌總體上偏於經驗和智性寫作,延續的是艾略特、史蒂文斯、奧登的沉思傳統,阿什貝利自己曾說,奧登對他產生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史蒂文斯,奧登詩歌中對口語的使用,使抽象變得具體鮮活的令人吃驚的方式,奧登對工業意象的使用,等等。玄學詩、19世紀詩歌以及約翰·濟慈,也是讓阿什貝利頗為感興趣的。其次,阿什貝利又受到了法國超現實主義和達達派的影響,即便詩人自己並不承認這點,而是聲稱自己得益於德語和斯拉夫語詩人,理由是法語的“明晰性”無法讓詩寫得“朦朧”。即便如此,總體上說,他的詩歌中還是有相當濃厚的超現實主義的因素。智性思辨和超現實體驗在他詩歌中融為一體,無疑是對原始的超現實主義的某種擴展。阿什貝利承認,他的詩歌是從潛意識起源的,但它途中要經過有意識的頭腦並且受到它的監督。他不相信自動寫作,因為它並非整個精神的反映,只有部分的邏輯與合理性。
南都:文學評論家角谷美智子認為,約翰·阿什貝利的寫作“有關詩歌的形成,有關藝術家從混沌中絞出秩序的嘗試”,對這句話應該怎麽理解?
馬永波:“有關詩歌的形成”的詩,換個說法可以稱之為“關於詩歌的詩歌”或者說“元詩歌”,這一點,美國詩評家海倫·文德勒曾言及,當一首詩被說成是關於詩歌的詩時,“詩歌”一詞往往指涉著很多東西——人們如何從自己經驗的隨機性中結構出可理解的事物;人們如何選擇他們喜愛的東西;人們如何整合喪失與痛苦;人們如何用希望和夢想將經驗變形;人們如何感知並強化和諧的瞬間;人們如何實現濟慈所稱的“靈魂或智力命定擁有的同一性的感覺”。元詩歌的主要技巧可以歸納為——關於一個人在寫一首的詩;關於一個人在讀一首詩的詩;凸顯詩歌的特定慣例的詩;非線性的詩,各個詩節的閱讀順序可以打亂的詩;元語言評說的詩,即一邊寫詩一邊對該詩進行評論,評論也是詩的正文的一部分;作者意識只是詩中眾多意識之一的詩;預測讀者對詩歌有何反應的詩;詩中人物表現出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在一首詩中……
阿什貝利關心的不是經驗本身,而是經驗滲透我們意識的方式,我們如何從繁複的材料中建構起有意義結構的方式。而經驗之被人所感受的特點往往是跳躍、斷裂、含混和不完整的。因此,阿什貝利的詩中總是存在著諸多彼此牽製和反詰的力量或者語調,他往往將來自不同語境的材料混合起來,並置和疊加起來,消除其中時間的線性結構,而抵達某種同時性的共在。這樣的詩歌注重的是過程,經驗變化的過程,思維流動的過程,思想之間的運動。因此,意義和隨機性是混合在一起的,不可分離的。含混和確定性是一對相關的悖論,這一點,阿什貝利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的一段話可能有助於我們的理解,他說:
“萬物處於一種運動與演進的連續狀態,如果我們抵達了一個時刻,我們所說的確定性,就在這裡,這是宇宙的終結,那麽,我們當然就必須與那之後繼續的一切打交道,然而,含混似乎是要把進一步的發展考慮在內。我們會認識到,現在的時刻可能是永恆的時刻,或者是一系列永恆時刻之一,每一個都將與它類似,因為,在某些方面,它們就是現在,而不是在其他方面,因為到那時現在將成為過去。”
南都:《凸面鏡中的自畫像》為詩人贏得了廣泛的聲譽,這首詩涉及到許多藝術問題,能否介紹一下他的詩歌和繪畫,尤其是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淵源?
馬永波:阿什貝利曾在巴黎從事藝術評論工作多年,浸淫其中。他回到紐約後,更是與奧哈拉等其他紐約派詩人一起,與抽象繪畫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有時也像波洛克使用顏料那樣,把詞語當作顏料揮灑,因此詞語在他的詩歌中獲得了原初的質地和本體論的凸現,而不再僅僅是表意的工具而已。1962年出版的詩集《網球場宣言》,是詩人最不可解的一本詩集,他在其中進行了激烈的語言實驗——打破短語,單獨用字——可以稱做語言的波洛克繪畫,文本支離破碎,顛覆了可以認知的知識秩序。1965年回到紐約之後,阿什貝利任《藝術新聞》執行編輯,由於工作的緣故,與先鋒音樂及繪畫的接觸更為密切,深受影響。阿什貝利認為,抽象表現主義是從超現實主義中生長出來的,根據他的判斷,抽象畫家從超現實主義那裡借鑒的最主要技巧就是“自動主義”,它在波洛克手裡成了具有創造力的手段。與意義的真實相比,詞語擁有更多客觀的真實,這一點無疑受惠於抽象繪畫。
阿什貝利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的影響,但是,他沒有止步於此,他又從德·基裡科和坦蓋那裡學會了描繪非個人化的自畫像,這使得他與抽象繪畫的自動主義區分開來。他觀察到,坦蓋的那種耐心、精細、古代大師般的技巧,有別於波洛克和克萊恩自動的行動繪畫,其中的主導原則似乎並不是那麽自動主義的,而是充滿了自我克制,因此更能夠反映出精神的現實,而非個體意識,同時反映出這精神知覺到的世界,這種狀態按照蘭波的著名說法便是“我是另一個”。阿什貝利心目中的超現實主義不是青春期日記式的本能噴發,而是高度形式化甚至過於精細複雜的洛可可框架。自我克制和精心結構有助於他完善成為另一個自我的技術。那麽,阿什貝利是如何做到這點的?他如何創造出一個他者般的自我的?其方法是收集起這個世界的現成品,就像法國新現實主義那樣,利用大機械生產出來的物品的品質,使過度的自我關注延展向其他關聯物。這種“挪用”現成品的目的在於意指作品本身以外的一些心理狀態和文化語境,這一由杜尚開創的手段,應用到詩歌裡,有助於形成不同語境的對詰和互否,形成詩歌內部聲音的複調性,這樣,詩就成了一個各種力量博弈的戰場,既不是主觀抒發,也不是客觀呈現,而是主客混融。這些,也許和立體主義的同時性也有一定的關聯。
《凸面鏡中的自畫像》就可謂這種觀察與自我觀察的混合體,這首詩更像是一個人對自己大腦的抄寫,一系列的意識狀態的相繼呈現,感受和沉思交替,乃至達到出神的玄思。對世界的觀察和對自我的觀察是互為表裡的關係。抽象表現主義者把作品當做是自身向存在生成過程的某種記錄,具有一種“反指涉性的知覺”。這首詩起碼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主題,就是詩人與傳統的關係,是一種既可以親密交流又受到警告的關係,面對迫切希望到達現在的傳統,我們在心懷感激的同時,仍然保持著現代自我的謹慎。詩人在這裡提示出的是某種個人與傳統、個人與他者的辯證關係。
南都:從表面上看,阿什貝利的語言材料有很大的隨意性,給閱讀帶來某種程度的“障礙”,你在翻譯中如何轉換,如何捕捉這種獨特的氣質?
馬永波:阿什貝利重視藝術變形的力量,對於傳統實錄式的現實主義是采取拒絕態度的,他的詩多採用自由聯想性的意象,且具有典型的後現代主義者對於過程的重視,他往往呈現詩歌構成的過程本身,他也喜歡採用拚貼手段,各種異質語境的材料信手拈來,並置在一起,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這些,都造成了他的詩歌晦澀難懂,歧義性很強。在他看來,語言既是意義的傳達者,又是阻礙意義表達的障礙,語言同時具有澄明與遮蔽的雙重屬性。因此,他的很多詩都意在揭示語言和意義之間的複雜關係,意義產生的過程,意義的源頭不是詩人的主觀,也不是詩歌文本自身,它不取決於讀者的理解,更不在於外在世界,而是詩人、詩歌、語言、讀者、現實等等因素織成的一張多重關係的網羅。這些,都對翻譯構成了壓力。而且,阿什貝利對於抒情詩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將一套巨大的社會語匯帶了進來,大眾言論、報章俗語、商務和科技用語,以及流行文化和經典作品的征引,甚至陳詞濫調,比比皆是,有的很難索解。而且,他的詩歌一概沒有任何注解,似乎他所拚貼的那些文化碎片是任何人本就應該熟悉的,可是由於文化和視角的差異,很多文化關聯物的解構性使用,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去鉤沉和還原。阿什貝利龐雜散漫,機智幽默,他喜歡在不同層面的經驗片段之間進行“跳接”,這樣一來,造成的意義錯置和斷層,往往讓人恍然一驚,這是閱讀他詩歌的樂趣之一。但是,這種幽默背後,我始終認為他骨子裡有一種淒涼甚至悲哀的情調,這些,都是在翻譯過程中需要仔細體會並予以充分傳達的。因此,我主要采取直譯,盡量保留原作的形體結構,他的構詞法和句子結構,不做過多的“歸化”整合。這樣做,有利於語感的模擬,也為漢語增加一些新奇的表達方式和詞語組合。漢語的語言結構一直都比較單純,相信通過翻譯,我們能夠使漢語獲得組織複雜結構的能力。
漢語詩人不是文化太多,而是文化太少
南都:有一種觀點認為,詩歌的翻譯者首先應是一個詩人。詩人譯詩,是否等同於一次創作?
馬永波:詩人譯詩歷來爭議不斷,我個人並不覺得詩人和學者要截然分開,有很多學者,本身就是詩人,這樣的人來翻譯詩,當然有優勢。詩歌具有神秘性,沒有詩歌寫作經驗的學者,恐怕對於詩意本質很難有切身體會,進入文本的能力也會大打折扣。翻譯者對於詩歌的理解和詩才,往往決定了譯作的成色,翻譯者的文學信念製約著翻譯過程,嚴重的時候會完全偏離原作的詩學立場。因此,我認為,一個合格的詩歌譯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合格的詩學學者,翻譯是細讀,翻譯首先要把握住原作的詩學理念,而不能憑自己的理解隨意生發。比如,阿什貝利的散漫不羈同時又富有智性,我們就同樣得用散漫不羈的語言來應對,我們不可能把他譯得像泰戈爾那麽華麗,正如同把泰戈爾的莊嚴譯成口水似的滑稽詩,也同樣是不合適的。其次,合格的詩歌譯者最好也是優秀的詩人,翻譯是靈魂上的交流,如果雙方位置不對等,也很難有好的效果。詩歌譯者不一定首先是一個詩人,有的詩歌譯者自己不寫詩,或者詩寫得很差,但不排除他的翻譯詩有價值,兩者不能完全劃等號。但我依然認為,最好的詩歌譯者應該是最好的詩人和最好的詩學研究者。至於把翻譯當成是再創作,這個觀點我一直不敢苟同,我反倒認為,翻譯就是亦步亦趨,原文怎麽說,就怎麽譯,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意象、思想和語言結構。即便二度創作,也要有個限度,不能偏離原作的詩學理念和風格特徵。如果把翻譯看成是根據原作的意義和意境,自己重寫一首詩,那純屬於大逆不道。
南都:徜徉在另一種非母語的詩歌裡,對你進行母語的詩歌創作有何助益?
馬永波:我從大學英語課堂上開始嘗試翻譯詩歌,當時只是好奇,90年代初開始大量的閱讀和翻譯,這個興趣一直持續到現在,算起來也有近三十年。可以說,這三十年中,詩歌翻譯從愛好,慢慢變成了一種研究性的學術興趣,它始終是和我個人的詩歌創作分不開的,究其實,還是為了我自己的寫作。翻譯的好處不但在於可以開闊視野,它更可以鎮靜心神,尤其在一個變動不居、各種誘惑隨時都可能使人離開詩歌的時代,翻譯需要的沉潛和耐心,都有利於讓自己安靜下來,這種安靜的功夫本身就是精神的專注,是對詩歌之外誘惑的自覺抵製。從翻譯中獲取的營養是說不盡的,英美大詩人的精神氣質,首先對我們就是一種教育和激勵,他們的詩學理念,他們對事物的觀察和信念,他們微觀上的詩歌技藝,都會對我們的寫作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南都:又或者是負面作用?80年代以來的漢語詩人,幾乎無不受外語詩歌的影響。
馬永波:我認為這裡基本沒有什麽負面的作用,甚至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漢語詩歌要逐步建設的漢語詩學的現代性,離不開一個更大的參照系。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漢語詩人不是文化太多,而是文化太少。視野決定了胸懷,漢語詩歌要變成世界詩歌有機的一部分,必然要放開胸懷,海納百川,東西互融,由此,才能開啟一個更為遼遠的境界,才能真正明白,世界詩歌的前沿在哪裡,漢語寫作又走到了哪一步,我們在詩學傳承的鏈條上又處於哪一個位置,還能再做些什麽。我的翻譯著力於英語系統的詩歌,尤其是現代主義及其後,我相信這個工作起碼在詩學理念上對我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但在語言風格上,我倒覺得對我沒什麽大的影響,因為我的生存經驗本身就是內在於漢語的,是本土經驗,這個內核是沒有變的,只不過可能表達它的方式和別人有所不同。而就我的觀察而言,尤其90年代以降,漢語詩歌的一個弊端,來自於某種急功近利,尤其在對待外來影響方面,我們的詩人往往是局限於文本表面的模擬,而對於原作的深層動機,甚至對人家的精華,不但缺乏了解,而且有所屏蔽,學習的多是表面的技巧。阿什貝利在漢語中的接受就有這樣的問題,大多數人學的只是表面的語言機智,而對於詩人的精神境界難有企及,甚至對於他的詩學理念都不甚了了,就急於模仿,我相信,這樣來吸收“營養”那只是死路一條。我翻譯了阿什貝利這麽多詩,他的詩學理念對我有影響,我卻沒有學習他的語言風格,因為,翻譯成漢語的阿什貝利的所謂語言風格,裡邊大部分是我的語言風格的反映。在漢語中模仿阿什貝利,實話說,只是在模仿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