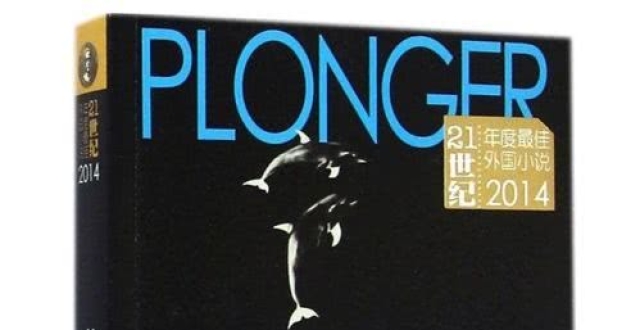在中國文學史上,似乎沒有人比魯迅更具備話題性:在中小學語文課本上,魯迅是被選入篇目最多的作家,也因其晦澀難懂,成為學生們暗自生怕的作家;在教材的編撰上,魯迅的作品被替換,也往往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在社交媒體上,魯迅的“名言”與白岩松的段子一樣流行,儘管絕大部分的網絡流行語都不是魯迅說的……
魯迅是文化符號,是精神象徵,是輿論場中的代言人……在這些現象背後,隱藏著魯迅的接受史問題:在不同的時代,他被挪至不同的位置。借用胡適沒有說過的那句“名言”:“魯迅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像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對魯迅《故鄉》的文本接受史研究一樣,即使在民國時期,不同陣營的人也會對魯迅的文章采取不同的闡釋;1949年以後,魯迅的作品廣為傳播,被公認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改革開放以來,魯迅的形象逐漸回歸,人們發現他兼具金剛怒目和菩薩低眉兩面,在生活中是一位頗為有趣的“大先生”。
自魯迅涉足文壇以來,對他的文本闡釋就已經歷了革命闡釋、官方定性、學術爭論和民間話語四個階段。無論爭議也好,仰望也罷,魯迅就站立在那裡,隻待我們用自己的方式接受。每一重視角的背後,都滲透著思維模式、話語方式、價值判斷和現實感受。

藤井省三,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研究生期間曾作為中日恢復邦交後第一批中國政府獎學金學生赴複旦大學留學,曾任東京大學教授,現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海外人文資深教授、名古屋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專攻中國現代文學及魯迅研究等。著有《愛羅先珂的都市物語》《魯迅〈故鄉〉閱讀史》《魯迅事典》《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等。
作為日本第三代魯迅研究學人,近些年來活躍於中日學界之間的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甚至將村上春樹與魯迅置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無論是在《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還是在《魯迅的都市漫遊》,藤井省三都花費了不同程度的筆墨來分析二者的異同。通過文本分析和研究論證之後,藤井省三提供了另一重爭議性的觀看視角:魯迅和村上春樹之間存在著譜系關係——村上春樹自處女作《且聽風吟》發表以來,一直執著於魯迅和近代中日之間的歷史記憶。
藤井省三是1949年以後日本第一批留華學生,當年的論文便是對魯迅短篇小說《故鄉》的文本接受史研究。藤井省三借助魯迅《故鄉》這篇短文在不同時期的不同闡釋話語,重構了現當代中國的文學空間。從藤井省三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僅僅從單篇文章在不同時空的文本闡釋,便能呈現不同方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話語情境下,對魯迅及其文本的話語爭奪。三十年後,藤井省三依然沒有“放過”魯迅,從魯迅《故鄉》的中國閱讀史研究,轉入了魯迅《故鄉》的日本閱讀史研究,與此同時還聯合東亞和美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對魯迅及其文本進行專題合作研究,比如東亞視野下的魯迅阿Q形象系譜研究。
近期,藤井省三的《魯迅的都市漫遊:東亞視域的魯迅言說》由新星出版社引進出版。這本著作原本屬於岩波書店的教養啟蒙系列,前半部分追蹤了近現代東亞都市空間裡的魯迅人生,後半部分更像是東亞視域下的魯迅接受史。在這本書的後半部分,藤井省三依然將魯迅和村上春樹放在一起進行系譜化的比較。在他看來,無論喜歡也好,厭惡也罷,魯迅是近代工業社會中的東亞文化原點,而村上春樹是後現代社會的東亞文化新原點。
藤井省三對魯迅的研究,既帶來了觀察的新視角,也帶來了解讀的新爭議。無論如何,最應該尊重的共識,就是“將魯迅還給魯迅”。
采寫 |嚴步耕
1
日本人對魯迅的接受史
經歷過怎樣的變遷?
新京報:從少年時期接觸到魯迅,再到現在對魯迅的不斷研究,在不同時期對魯迅的感受是否發生過變化?
藤井省三:我讀魯迅,已近六十年。對於魯迅作品的理解,隨著年齡的增長也一點點地發生了變化。比如我第一次讀到的魯迅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說《故鄉》。那時的我,還是一個寫著暑假作業讀後感的小學五年級學生。不知為何,當時的我,比起對同輩的“迅哥兒”和“閏土”,更感興趣的反倒是作為敘述者的“我”,那個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性。“我”告訴閏土想要什麽都可以帶走,可是閏土卻把碗和盤子藏在草灰裡,這是閏土對“我”的背叛。想到這一點,我感到非常悲傷,於是把這寫進了讀後感。
“草灰裡藏的碗盤是閏土偷的”,基於楊二嫂這種說法的解釋,是當時日本幾種中學國語教科書中對於《故鄉》一文的普遍解釋。我在家中兒童房找到《青少年世界文學全集》,獨自看完了全書50卷中的第44卷“現代中國小說集”,書中給出的解釋和我多年後在中學語文課本中學到的是完全一樣的,卻和1949年後中國方面對於《故鄉》的解釋全然不同,這簡直不可思議。

《魯迅的都市漫遊:東亞視域的魯迅言說》,[日]藤井省三著,潘世聖譯,新星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到三十多歲,我開始了解到中日兩國的教科書存在“閏土犯人說”(日本)和“閏土無罪說”(中國)的區別。等到進入四十歲,我對《故鄉》在中國的閱讀史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民國時期,“懸置說”是主流;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中學生群體也出現了“閏土犯人說”的主張。於是,我開始在東亞的時空中去理解《故鄉》。當我也到了五十多歲,開始把楊二嫂當作同齡的中年女性看待(雖然在上世紀20年代,50歲與其說是中年,不如說是老年),我意識到作為敘述者的“我”雖然聽她說過很多話、看她做過很多事,但卻始終無法理解她的內心世界。她和閏土一樣,是不會主動說話的“下人”。
在我的孫子們一個接一個地出生後,對於“我”的母親,我開始感到困惑。雖然她不得不賣掉亡夫祖傳的宅子,遷居到“相隔二千余裡”的“異地”生活,孤寂且忙碌地活著;但面對二十年後回到家鄉的兒子,怎麽能對他的妻兒不聞不問呢?以至於我不得不懷疑,作為敘述者的“我”,是不是單身或者正和妻子分居?我也關心起閏土的孩子們。閏土來見“我”的時候,第一次帶著和宏兒同齡的第五子水生來,第二次為什麽不帶水生來,而是帶著五歲的女兒來呢? 隨著我年齡的增長,這類新的困惑出現了。

《魯迅〈故鄉〉閱讀史:現代中國的文學空間》,[日]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新京報:日本對魯迅的接受,是否也如中國一樣,隨著社會變化而產生不同的闡釋空間與解讀方式?
藤井省三:是的。在日本,自1909年綜合類雜誌《日本及日本人》介紹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共譯的歐美短篇小說集《域外小說集》以來,已有一百多年漫長的魯迅閱讀史。對魯迅的解讀發生變化,是在中日關係變得緊密(無論變好,還是變壞),以及日本人在絕望中試圖抵抗的時候。
1920年,在京都大學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的青木正兒,發表了一篇題為“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的論文,文中把魯迅稱作“未來可期的小說家”,“他的《狂人日記》就像一個迫害狂的驚駭幻覺,開拓了中國小說家至今尚未涉足的領域”。青木是在充分肯定中國新文化運動巨大影響力的基礎上介紹魯迅的。
最早刊登魯迅作品日語譯文的,是北京的日文周刊《北京周報》(1922年6月4日,第19號),譯者是周作人,作品是《孔乙己》。在此之後,《北京周報》還刊登了魯迅自己翻譯的《兔子和貓》和魯迅的採訪報導等,致力於介紹魯迅。
在日本,魯迅度過了七年留學生活,周作人待了五年,而且周作人和弟弟周建人的妻子是羽太信子和芳子姐妹。周家三兄弟和母親共同住在北京時,從東京訂閱了《讀賣新聞》,還會在家中定期舉辦沙龍,講評1904年創刊於東京的《新潮》等日本文藝雜誌。另外,在五四運動時期,包括《北京周報》的記者丸山昏迷(1895-1924)在內,大約有1500名日本人居住在北京。這個日本人社群,在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魯迅文學作品的最初日語譯文,是由周作人翻譯、發表在北京的日文周刊上的。這件逸事,也反映出近代史上親密而複雜的中日關係。
芥川龍之介(1892-1927)在1921年作為《每日新聞》特派記者,在上海、北京等中國各地旅行之際,魯迅將他的《鼻子》《羅生門》兩篇小說翻譯並發表在了北京報刊《晨報》上。這兩篇文章隨後收錄進了《日本現代小說集》(1923)。在北京逗留期間,芥川龍之介閱讀了魯迅的譯文,非常滿意,“自己筆下的情緒躍然眼前”;1925年,他還特意寫了一篇題為“日本小說的中國翻譯”的隨筆,高度評價了魯迅的翻譯,稱其“與現代日本對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相比也毫不遜色”。

魯迅。
一直到上世紀20年代中期,在日本關注魯迅的群體,主要都是關心中國在五四運動後國家發展狀況的那些人。反過來說,除了與中國有特殊關係的人之外,魯迅的名字是不為大眾所知的。
1919年,魯迅將武者小路實篤的反戰戲劇《一個青年的夢》翻譯為中文;與之對應的,1927年,武者小路實篤主持的月刊雜誌《大和諧》10月刊譯載了魯迅的短篇小說《故鄉》。這是日本國內最早翻譯的魯迅作品。在1926年,中國開始了北伐戰爭,國民革命取得了進展。1927年4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事變”,結束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這一時期,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開始關注中國的左翼作家,並多次提及魯迅的名字,魯迅作品的翻譯也開始增多。1935年出版發行的岩波文庫版《魯迅選集》,對日本魯迅閱讀史起到重大的影響。而這本《魯迅選集》是由和魯迅有著深入交流的佐藤春夫,及其畢業於東大中文系的弟子同時又是魯迅學生的增田涉共同翻譯而成的。1936年魯迅逝世後,日本改造社在次年發行了《魯迅大全集》全七卷,魯迅在日本文壇從此成為一個不可磨滅的名字。
如何理解統一的中華民國,對於那些想要在中國大陸擴張自己利益的帝國主義者,以及渴望中華民國社會主義化的日本左翼來說,都是一個大問題。尤其對於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左翼和希望與中國合作的日本自由派來說,魯迅是他們理解中國的重要線索。
日本的左翼沒能阻止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反而幾乎被帝國主義者所扼殺。儘管如此,自由主義派在被控制言論自由後,仍不斷發出對侵華戰爭的質問。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開始,這一年日本出版了《大魯迅全集》全7卷。該全集的編輯顧問是茅盾、許廣平、胡風三位中國左翼人士和內山完造、佐藤春夫兩位日本自由派人士,譯者還包括在上海流亡期間與魯迅、胡風有過交往的日本共產黨員鹿地亙。戰時,鹿地亙在武漢結成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在重慶也持續著反戰活動。(記者按:應該是在桂林發起成立的)

《大魯迅全集》,日本改造社,1937年版
之後幾年內相繼出版了幾本關於魯迅的著作:1941年,小田嶽夫(1900-1979)出版了世界第一本魯迅傳記《魯迅傳》;1944年,竹內好出版了評論性傳記《魯迅》;1945年,太宰治出版了以在仙台生活時期的魯迅為原型的長篇青春小說《惜別》。自此,日本人對魯迅的接受達到頂峰,這也反映出對日本侵華戰爭的質疑。
戰敗後,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對中國人民革命的關心高漲。不過,美國佔領軍采取了嚴格的言論管制。但是,在1952年4月日本恢復獨立後,次年竹內好翻譯的《魯迅評論集》(岩波新書)、《魯迅作品集》(築摩書房)、小田嶽夫和田中清一郎共譯的《魯迅選集》第二本(青木書店,1953)等書就紛紛出版。戰敗後的日本人,是想通過魯迅了解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2
魯迅和村上春樹之間
存在著譜系關係
新京報:《東京外語支那語部》是你比較早期的一部著作,能否簡單介紹一下該機構與中國文學之間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對中日文學之間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藤井省三:東京外國語學校(現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部,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促進了中日關係,而且在介紹當代中國文學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今約170年的中日關係,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晚清到甲午戰爭時期,第二階段是中華民國成立到太平洋戰爭時期,第三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到文革結束,第四階段是改革開放四十年。
在最初的半個世紀,中國雖然在鴉片戰爭之後飽受歐美列強侵略之苦,與日本相比,卻是更早學習西方、邁向近代化的“發達國家”。例如18世紀60年代的江戶幕府,引進了在上海、香港發行的《六合叢談》、《香港新聞》等中文報紙,在原文上加以訓誡,再翻印出版。創建於1875年的北洋水師號稱“亞洲第一海軍力量”,其主力艦“定遠艦”曾在1886年停泊於長崎,當時甚至發生了數百名中國水軍上岸與日本巡警在街頭鬥毆的事件。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軍事大國。
但在之後的半個世紀,中日兩國的力量關係發生了逆轉。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為契機,日本加入了歐美列強的侵華戰爭,不久成為最大的侵略國。同時,日本人對中國的輕視也在增加,古典文化暫且不論,“當代中國文化並沒有值得日本人學習之處”的看法佔了主導地位。
在第二階段的中日關係史上,在日本有一群語言學家密切關注著中國掀起的“五四運動”,對新出現的文學樣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們通過漢語教育,努力把中華民國年輕的精神面貌傳達給日本人。在這群人中,就有東京外國語學校中國語部出身的教官和同校的出版人。東京外語組借助漢語教科書、學習冊,以及從中國翻譯而來的書籍,介紹了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鬱達夫、徐志摩、茅盾、巴金、凌叔華等作家,幾乎囊括了中國近代文學的主要作家。
東京外語組和中國文化界的國際交流,不單單局限於文字,不久也發展成個人的交往。有位出版社社長曾打算把體弱多病的魯迅接到日本療養,也有一位漢語教師把巴金接到家裡為他提供長期住所,還有位私立語言學校的老師曾教胡風日語,幫他找到教授漢語的教職。
從“五四時期”到1940年期間,這個東京外語組專注於介紹同時代的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界密切交流。不幸的是,在中日戰爭時期,他們作為翻譯官被派到中國前線,成為侵略的先鋒;日本戰敗後,被追究戰爭責任,受到開除公職處分,不再受容於全國的國立大學和公立大學,東京外語組也就此消失。

《東京外語支那語部 : 交流と侵略のはざまで》,[日]藤井省三著,朝日新聞社1992年9月版
在《東京外語支那語部》出版之前,一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介紹和研究是從1930年竹內好等人成立的中國文學研究會開始的,但實際上竹內好這一代人受到了東京外語組很大的影響。
新京報:回到魯迅的問題。魯迅的很多寫作略帶隱語式言說,從都市漫遊的角度出發,外在於文本的書寫方式是否會存在脫軌的冒險?
藤井省三:語境研究,也就是說對創作環境進行研究,再結合文獻研究和文本分析,能取得很大的成果。我覺得,倒不如說,像“文革”時期 “石一歌”的《魯迅傳》那樣由後世意識形態主導、無視作品創作背景的研究,“脫軌”的危險性更大。
新京報:你在書中說,村上春樹成為了東亞文化的新原點。是否等於說魯迅是東亞文化的舊原點?
藤井省三:魯迅是近代工業社會中的東亞文化原點,村上春樹可以說是在後現代社會中成為了新原點吧。雖然還有其他可以作為原點的作家,但比較有特別的地方在於魯迅和村上春樹之間存在著譜系關係。
3
戰後的日本作家,
通過模仿魯迅來描寫日本
新京報:在中文版序中,你說到研究重點轉移到“魯迅與日本”這一領域。在《魯迅的都市漫遊》中,你似乎更側重於書寫魯迅曾經待過的都市空間在當時是怎樣的,對於魯迅在那些都市空間內部產生的內在經驗著墨較少。我們該如何從魯迅精神史的角度看待魯迅的日本經驗?在你看來,這些日本經驗又是如何轉化為中國實踐的?
藤井省三:正如我在《魯迅的都市漫遊》“中文版序”中所寫的那樣,“本書原為日本的學術出版社岩波書店所刊行,屬該社教養啟蒙系列叢書‘岩波新書’中的一冊”,只是我對魯迅研究的一小部分。首先,與魯迅在日本經歷相關的《摩羅詩力說》等“魯迅初期”的研究很重要吧。我在《魯迅、周作人的〈論〉與文學——〈河南〉雜誌上論文的比較研究》(1981)等論文中有詳細論述。
其次,魯迅在1909年回國後仍然會閱讀大量日語圖書雜誌,和許多日本人交流。魯迅與日本的聯繫,持續了一生。關於這一點,我曾在《先知先覺的都市故事——一九二〇年代東京·上海·北京》(1989)、《魯迅與日本文學——從漱石·鷗外到清張·春樹》(2015)等書中進行過研究。其中一部分曾被翻譯成中文。魯迅的內心問題,我在《俄羅斯的影子——夏目漱石和魯迅》中,也以俄國作家安德列耶夫為輔助線進行過論述。
新京報:你曾就魯迅《故鄉》的中國閱讀史做過梳理,從中國人對《故鄉》文本闡釋的話語變遷來反映中國文學的歷史空間。在《魯迅的都市漫遊》“中文版序”中,你談到“通過日本的《故鄉》閱讀史,也可以切實地把握現代日本的流動軌跡”,能否大致介紹一下日本的《故鄉》閱讀史?
藤井省三:日本關於魯迅《故鄉》閱讀史的研究,從今年初才正式開始。所以,請允許我保留自己的回答。但有一點我可以明確地指出,《故鄉》閱讀史受到1935年發行的岩波文庫版《魯迅選集》的重大影響,這本《魯迅選集》是由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共同翻譯而成。
新京報:在《魯迅的都市漫遊》中,其中有一部分論述的是日本/東亞對魯迅的模仿所構建成的東亞文學史,不同時期對魯迅的模仿有著怎樣不同的精神特質?
藤井省三:我比較一下大江健三郎(1935— )和村上春樹(1949— )吧。1947年,大江健三郎先生從四國的小山村進入新製中學時,他的母親作為魯迅的忠實讀者,送給他一套佐藤春夫譯的岩波文庫版《魯迅選集》。從此,大江健三郎就愛上了魯迅的作品。大江健三郎先生在處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之前寫的一首詩,其中一句“滿懷希望的恐怖悲鳴”,是從魯迅的短篇小說《白光》的末尾引用的。
在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1959)中,大江健三郎先生描寫了19世紀50年代日本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群像,其主人公“南靖男”被他的戀人、一名為美國人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稱為“我的天使”。這位姓南的青年,可以說是大江版的“阿Q”。日本人雖然從美國佔領軍那裡獨立了,但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仍然是美國的半殖民地,大江健三郎試圖通過日本的“阿Q”來刻畫這種根植於半殖民地的自立。
村上春樹第一部作品的第一句是,“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且聽風吟》1979)。這一句是由魯迅《野草》中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所觸發的,我認為是對魯迅文學的致敬。此後,村上春樹先生經常借鑒《阿Q正傳》,並塑造阿Q式的主人公。其中,特別有趣的是《1Q84》這部描寫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長篇小說中的第三個主人公“牛河利治”。他從相貌、性格、境遇到名字,都是阿Q的翻版。村上春樹很喜歡玩構詞遊戲,“牛河”這個姓氏不用訓讀“USHIKAWA”,而是用音讀“GYUKA”的話,就能從“GYUKATOSHIHARU”中拚出一句“HARUGI TO AKYUS”(春樹和阿Q們)。在描寫進入後現代轉型期的日本時,村上借用了“阿Q”這個形象。
戰後的日本作家們就像這樣,通過模仿魯迅來描寫各個時代的日本。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
4
魯迅對惡者強烈批判,
對弱者常懷同情
新京報:同樣在序言中,你談到自己致力於召集東亞和美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進行專題合作研究,其中有一個國際合作研究話題是“東亞的魯迅阿Q形象系譜”,能否跟我們簡單分享一下“形象系譜”的研究成果?
藤井省三:“東亞的魯迅阿Q形象系譜”,是2009年至2012年四年間我們進行的共同研究。例如,韓國東國大學教授的金良守先生,把旅日朝鮮人作家金達壽(1920-1997)作品《樸達的審判》的主人公“樸達”的人物形象,與魯迅的“阿Q”進行比較,,提出阿Q的冤魂作為一種“亞洲的停滯性”,或者說“敗北主義”;他在九泉流浪之後,於1950年重新投胎為韓國的底層農民樸達。全力抵抗統治勢力、不屈服於嚴刑拷打、面對司法部的百般刁難總是“嘿嘿”一笑的樸達,他不屈的精神延續至今仍未消失。在日語中, “樸達”和“我們”同音,也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Faye Kleeman(阮斐娜)提出,太宰治的《惜別》用“取樣”、“模仿”、“嫁接”的方式,再一次重申了魯迅文章中所包含的精神。
新京報:那麽,在你看來在當今的東亞視野下,該如何去談論魯迅的精神遺產?
藤井省三:魯迅精神是對人類整體抱有希望的同時,對惡者強烈批判,又對弱者常懷同情。在後現代社會,尤其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時,這種精神能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
新京報:在魯迅與胡適之間,素來存在著比較的視野。你也曾經寫過一本《現代中國的輪廓——通過從魯迅、胡適到鄭義、莫言的文學來解讀》。就你的閱讀史或研究經驗,胡適是否存在著某種東亞傳播現象?你又是如何看待這兩位民國學人之間的比較?
藤井省三:有關胡適的問題,我認為我在《她是紐約達達派——胡適的戀人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的一生》(王惠敏訳、《魯迅研究月刊》1997年6月)這篇論文中已經回答了,這是我於1995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康奈爾大學進行三個月的研究後得出的成果。魯迅和胡適,可以從日本留學經歷和美國留學經歷,以及異國戀愛經歷的角度進行比較。戀愛,不僅僅是一種現實經歷,還包含了讀書、看戲、觀察周圍人的體驗。
日本也有像新渡戶稻造(1862-1933)這樣的著名知識分子,他們雖然都是學者、高校行政人員、政治家,但沒有魯迅那麽大的影響力。
新京報:你還寫過一本著作《魯迅與紹興酒》,從酒的角度來解讀現代中國文化史,能否簡單分享一下這本書的大致觀點?
藤井省三: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工作,主要分為作品、作家研究和對日本國民的中國現代文學介紹兩類。我負責翻譯魯迅、張愛玲、莫言等作家的作品,也為閻連科、余華、慶山(舊名:安妮寶貝)、韓寒、郭敬明等作家的作品寫書評。但在日本,隨著少子化趨勢以及閱讀量下降,圖書市場每年都在縮小,針對日本國民的啟蒙活動也未必能取得很滿意的成果。
因此,我開始點評介紹中國電影,以電影為契機開展影評活動,借此讓大家關注中國文學。成果之一,就是《隔空觀影:藤井省三華語電影評論集》(葉雨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這本書。可是,介紹電影也還不足以增加喜愛中國文學的讀者,我就想,以中國的酒為線索來介紹現代文學怎麽樣?於是,我開始寫《魯迅與紹興酒》。
四十年前,我作為中日兩國第一批公費交換留學生來到中國。在這本書中,我回顧了這四十年來學習、遊玩的經歷,以我作為文學研究者和電影評論家的視角,描繪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歷史。我特別聚焦了華語區各地在“公宴”、“私宴”這類飲酒場合的文化特徵和各類文人的個性,將那些難以忘懷的情景展現給讀者。
在責任編輯的建議下,我選取《魯迅與紹興酒》作為書名,其實關於魯迅的內容不到兩成,也有魯迅的粉絲對此抱怨。不過話說回來,我覺得這本書還是為中國現代文化帶來了新的日本粉絲。

《魯迅與紹興酒》,[日]藤井省三著,東方書店2018年10月版
新京報:文本的接受史,往往存在著正反兩面。你在書中談論的更多是正面接受史,不知日本是否在某些時期也存在著對魯迅的反面論述?
藤井省三:自從日本1909年首次報導魯迅以來的110多年間,恕我孤陋寡聞,我從未聽說對於魯迅的批評。非要說的話,竹內好在評論性傳記《魯迅》(1944)中作出了一些充滿偏見的批評,比如“《肥皂》乃愚劣之作,《藥》是失敗之作”、“我認為《傷逝》是惡劣的作品”之類的。松本清張(1909-1992年)誤讀了《故鄉》,寫出了反《故鄉》的小說《父系之手指》。但在戰後,竹內好收回了自己的惡評,把魯迅抬到了與中國官方對魯迅的評價差不多高的位置。
5
非常期待中國學者
對於莫言接受史的研究
新京報:你曾出版過《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一書,包括在《魯迅的都市漫遊》一書中,都存在著這麽一個新穎而又有爭議的論述:村上春樹的文本受雇於魯迅的影響。但我知道,柄谷行人並不認為村上春樹的“1Q84”中的“Q”源自於魯迅的“阿Q”,包括中國也有學人曾就你的這份論述有過分析,你怎麽看待這兩位學人對你的回應?
藤井省三:柄谷先生的發言,是什麽時候在哪裡發表的呢?我在雅虎等網站上搜索了“柄谷行人 1Q84 阿Q”,但沒有找到。請告訴我更具體的信息。(記者按:此問信息出自後述論文,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楊微微發表於《北方文學》的《Q氏是日本版的阿Q?》,文中言及柄谷行人認為村上春樹筆下的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不具有任何意義)在上面網址搜索了一下,找到了楊微微先生寫的論文《Q氏是日本版的阿Q ?——試評藤井省三〈魯迅的“阿Q”與村上的“Q氏”〉一文》,但沒能下載。於是,我試著從CNKI下載這篇論文,但搜索“楊微微”、“Q氏是日本版的阿Q”,都沒有找到。楊微微的論文好像沒有收錄在CNKI中。因此,我沒能拜讀。
不過,我還是讀到了楊微微論文的第一頁。楊先生對拙著《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第六章第一節《魯迅的“阿Q”與村上的“Q氏”》(244-247頁)提出了批評。但我用拙著的一半篇幅,通過文本分析和研究來論證了,村上自處女作《且聽風吟》發表以來,一直執著於魯迅和近代中日之間的歷史記憶。我希望楊先生能根據拙著《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全書內容提出意見,批評指正,儘管考慮到篇幅,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日]藤井省三著,張明敏譯,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7月版
新京報:除去村上春樹與魯迅之間的爭議,你也曾抨擊過林少華對村上春樹的翻譯。此外,你還與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之間發生過文學論戰。如今回頭來看,你怎麽看待這場論戰?
藤井省三:我並沒有“抨擊”林少華教授的意思。我用《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全書一半篇幅,將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對村上春樹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比較研究。同時,我也討論了三地對村上文學的翻譯各自具有怎樣的特色。翻譯傾向和讀者論一樣,是文學接受研究的重要部分。東京大學舉辦村上春樹國際研討會時,我也邀請了林少華教授和香港版譯者葉蕙蘭、台灣版譯者賴明珠進行演講。
和陳映真先生也並非所謂的“論戰”。陳先生誤讀了我的台灣文學研究,引用了我從未寫過的話,批評我讚美日本統治台灣。因此我提醒您,那是誤讀。在學生時代,我就讀過陳先生的小說,並且當時非常擔心他會受到國民黨舊政權的言論鎮壓而入獄。20世紀60年代冒著生命危險為言論自由鬥爭的作家,卻在21世紀壓製學術自由,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新京報:你也是較早翻譯和研究莫言的學人,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20年代,日本對莫言的接受史是否也存在著變化?
藤井省三:日本對莫言的接受,也隨時代而變化。莫言接受史的特點是,在初期受到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否定,反而受到大江健三郎等作家和川村湊等文藝批評家,以及法國文學、美國文學、拉丁美洲文學等歐美文學研究者們的高度肯定。作為翻譯家和研究者,我正處在莫言接受史的漩渦之中,我反而非常期待中國學者對於莫言接受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