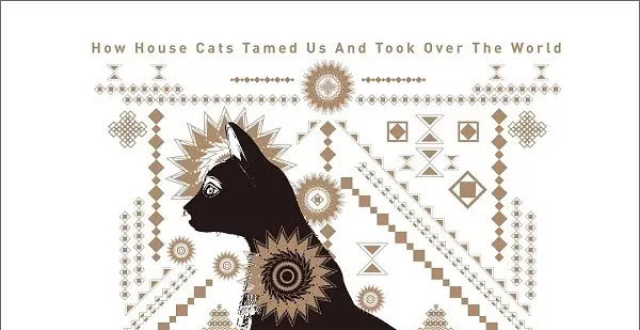《奧斯維辛的攝影師: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紀實》是我翻譯的第二本書,也是我在人生的非常時期投入精力時間和情感相當多的一本書。譯稿跟著我輾轉德國哥廷根、南京、台北、北京、成都甚至是醫院病房,七易其稿,才最終面世。

2018年9月初我才拿到樣書,此時距離此書正式出版已過去了兩月有余,看到書封面上三組照片,以及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略感自豪。興奮之餘,這幾天都在胡亂地、故意不按章節地翻看,譯書時的點滴往事漸漸憶起。
這本書的翻譯工作是我自己爭取來的。我不過是從朋友那邊聽到了有這麽一本書在尋找譯者,就趕緊毛遂自薦取得了書稿。青少年時期看過的三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逃離索比堡》《鋼琴家》和美劇《兄弟連》是一直留存在記憶中的關於二戰期間猶太人悲慘遭遇的影像,長久以來揮之不去。而我長年在德國留學、工作、生活的經歷又讓我多次面對或者逃避這個德國人尚且禁忌不表的母題,我堅決地接下此書的翻譯工作,為的是更近一步接觸歷史,接近真相,求個明白。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作者恩格爾曼的語言簡單平實,講述的方式極為直白,就像一本完全不加修飾的日記,將一件件事、數個重要的日子娓娓道來。此書主要是主要面向青少年讀者的,因此我能理解作者使用語言的方式,如此這般白描“人間煉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生活,這些貌似極為平淡樸實的德語,讀起來卻更讓人有觸目驚心不忍卒讀之感。
正如書中導言所說的,“談論奧斯維辛並非易事”,翻譯有關奧斯維辛的書也並非易事。
首先是語言方面。 和我上一本有關海德格爾哲學的譯作不同,這次原書的德語相對簡單易懂很多。可越是簡單,翻譯起來就越需要字斟句酌,唯恐譯得流水账一般,讀者三五句便不想再看。又怕譯得過於意譯,偏離原著冷靜克制及平實的風格。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SS”,即德語的Schutzstaffel,到底是譯為“黨衛軍”還是“黨衛隊”就讓我翻遍了資料,看遍了國內最知名的幾個軍事論壇。我搜羅並一一閱讀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幾乎所有迫害猶太人和集中營題材的書,例如,萊維的《這就是奧斯維辛》《這是不是個人》《被淹沒的與被拯救的》,勞倫斯裡斯的《奧斯維辛:一部歷史》,阿倫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溫迪霍爾登的《天生幸存者:集中營裡三位年輕母親與命運的抗爭》,還有同樣題材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願者》《幸運男孩:從奧斯維辛幸存的回憶》和《來自納粹地獄的報告》。這些書對“SS”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譯名,多數譯為黨衛軍。

“SS” flag
在繼續埋頭鑽研、苦翻資料後,最終我還是決定不隨大流,把“SS”譯為黨衛隊。“SS”並不是德國的正規軍隊(德國國防軍),在初期更像是一個兼有保鏢性質的宣傳小分隊。之後希特勒命令黨衛隊從難以控制的衝鋒隊中獨立出來。“衝鋒隊指揮官無權向黨衛隊下達命令”,他還規定了黨衛隊的任務是“主要在黨內行使警察的職責”。在黨衛隊頭目希姆萊的把持下,黨衛隊逐漸滲透到其他國家機器中,包括警察和軍隊。黨衛隊可以逮捕任何被懷疑是“國家敵人”的人,不經審判就將其投入“保護性拘留營”即集中營中。集中營的管理和發展全部操縱在黨衛隊手中。
而在二戰中真正參與作戰的,令歐洲顫抖的希特勒的精銳“禦林軍”,是經由德國國防軍認可下籌組訓練的黨衛隊特別機動部隊(SSVT),幾年後希姆萊將這支軍隊命名為武裝黨衛隊(Waffen-SS)。國內普遍的譯名黨衛軍多半是因為將“SS”誤認為武裝黨衛隊了。

在芬蘭的Waffen-SS士兵,圖片來自Wikipedia
另外,相同題材書中出現的同樣的詞,比如“營區”“技能犯/職能犯”"卡波”等,也都在斟酌之後再決定是否使用同樣的譯名,以便和已有的普遍譯法保持一致。但是之於我,尊重歷史和準確性是第一位的,一致性其次。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了,對集中營及迫害猶太人這段黑暗歷史,國人及中國歷史學家的研究並沒有讀者想象的那麽多,至少市面上可供參考的此類題材的書沒有研究二戰戰爭史的書那麽多。作為譯者,我對這段黑暗歷史做了相對多的功課,深感對戰爭的反思和對人性之惡乃至集體無意識之惡的理性思考,應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如布拉塞所願:“集中營的歷史永遠不再重演!”
其次,“當你久望深淵,深淵也會回望你”,尼采的名言在我譯書的過程中一語成讖。翻譯有關奧斯維辛集中營題材的書其實是個很痛苦的過程。在翻譯過程中我要面對大量投射自身的情感、極度的憎惡納粹之惡、對集中營犯人的同情,同時又要在強烈感情下保持翻譯的公正態度,選擇冷靜克制的用詞。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印象最深的是,家人幾乎每天都關心我翻譯的進度,我每天告訴他們的基本都是同樣的話:“今天又死了五個”或是“今天又是誰誰死了”。死、毆打、虐待、折磨、屠殺,這些詞出現的頻率極高,而我還要為了不重複用詞而對這些詞進行微調,比如打有毆打、暴揍、虐打之分,死有打死、射殺、毒死、折磨致死之分。
翻譯時,由於某些場面和過程的描寫非常直白,很容易產生畫面感,有幾次自己都覺得書中描述太過殘忍,要離開工作喘口氣換換腦子。我甚至做過噩夢,夢見自己和納粹黨魁希姆萊一起巡視集中營,那些瘦骨嶙峋的犯人一起往我腿上撲,每個人都是黑洞洞的眼睛,像地獄裡的鬼魂,可怕極了。書中第十一章最後一段寫道: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布拉塞)曾向魯斯基求情的事一直糾纏著他。……他大汗淋漓地從噩夢中醒來。”
未曾想過譯者也會和書中主人公有一樣的體驗, 這種體驗在我之前的翻譯工作過程中從未出現。而這種體驗恰恰對譯者來說又是另一層挑戰:對待手頭的翻譯工作,是感同身受工作的效果好,還是永遠保持一定的距離感,保持克制冷眼旁觀的翻譯工作效果好呢?作為譯者,如何把握這個其中的平衡度呢?這是我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但直到交稿也並沒有找到最後的答案。也許答案在我的譯文中,留給讀者們體會吧。
最後,請容許我用一小段篇幅來講述這本書翻譯過程中的私人感受。我在開頭提到過這本書是在我人生的非常時期翻譯的。我多次把書稿和我時不時翻閱的參考書目帶到病房,和我的第一位讀者也是第一位校對者——我的父親進行探討。那時他已經接近人生的最後階段,身體不好但頭腦極度清醒。他不懂德語看不懂原書,只能對我的譯稿提出意見。但他和萊維一樣,是個冷靜客觀的化學家,對於譯稿中文字的客觀度和準確性,都有著極高的要求。文中幾處譯者注,都是在他的要求下加進去的。我不僅要面對書中一再出現的死亡,也要面對即將到來的至親之人的死亡,也許正因為此,我才對死亡、恐懼、絕望這些本不屬於我這個年齡的人的話題,有更深層的了解,更有切膚之痛。父親一字一句地看完了我的第三稿,稿紙上滿滿都是他用鉛筆寫下的修改意見,對於我沒有表述清楚之處他全部打了大大的問號,有這麽認真的讀者和校對者,我絲毫不敢懈怠,最後又校對四遍,把第七次改好的稿子交到編輯手中。
書出版了,父親人卻已不在。作者可以在書上寫上謹以此書獻給誰,譯者卻不能。那請允許我在譯者手記的最後一句寫上: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

簡介:《奧斯維辛的攝影師》講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在納粹集中營的真實經歷。威廉·布拉塞,一位波蘭攝影師,於1940年8月31日被納粹逮捕,隨後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編號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調入鑒定科,被迫為黨衛隊拍攝照片,不僅包括犯人的檔案照,而且還記錄下臭名昭著的“醫學試驗”。透過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頭的猶太兒童、用於“人種研究”的赤裸著身子的猶太少女、用於“醫學試驗”的雙胞胎……是一雙雙充滿恐懼的眼,一張張去日無多的臉,而他能做的太少。1945年,當蘇聯軍隊逼近奧斯維辛集中營時,布拉塞被要求銷毀所有照片,但他冒著生命危險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為見證奧斯維辛歷史的珍貴資料。但布拉塞卻再也無法端起照相機,因為那些恐懼的面孔總出現在取景器中,揮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