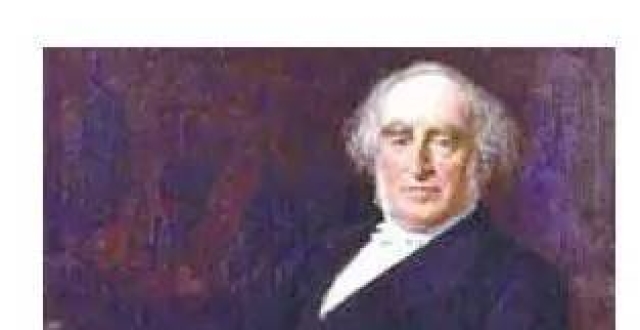本文摘自徐中約著:《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間的外交》,屈文生 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6月版,“雅理讀書”感謝譯者屈文生教授授權推送,若您閱讀後有所收獲敬請關注“雅理讀書”微信公眾號:yalipub。
丁韙良翻譯惠頓作品
在 1860 年《北京條約》訂立後中西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意識到在同西方交往時,掌握一定的國際法知識是必要的。新近設立的總理衙門(通常被人們理解為外交部,但實際上僅是軍機處的下屬委員會)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在1864年向朝廷奏稱:
竊查中國語言文字,外國人無不留心學習,其中之尤為狡黠者,更於中國書籍潛心探索,往往辯論事件,援據中國典製律例相難。臣等每欲借彼國事例以破其說,無如外國條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識,而同文館學生通曉尚需時日。臣等因於各該國彼此互相非毀之際,乘閑探訪,知有《萬國律例》一書, 然欲徑向索取,並托翻譯,又恐秘而不宣。

另一方面,外國人也意識到中國人需要國際法。目睹了中國人在外交交涉中釀下許多錯誤後,曾在1858年擔任過列衛廉公使翻譯的美國在華傳教士、出生於印第安納州的丁韙良讚成中國人需要翻譯一部國際法著作。在丁韙良有機會翻譯這部作品前,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的首席助手羅伯特·赫德,此前曾為總理衙門譯過亨利·惠頓所著的《萬國公法》一 書中有關常駐公使的論述共24條,其意明顯是在奉勸中國人應向國外派出常駐外交代表。當丁韙良在1862年開始翻譯時,他得到了赫德的鼓勵,赫德此時 剛剛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一職。
丁韙良1827年4月10日生於印第安納州立沃尼亞,是馬丁牧師十個孩子中的第八個。從印第安納州立大學和新奧爾巴尼神學院畢業後,於1850年到寧波傳教。在寧波傳教多年後,他獲得了一次休假回國的機會,當他於1862年返回中國的時候,決定在北京設立布道團。但是,上海傳教出版社負責人克陛存的突然死亡,使得丁韙良無法脫身前去北京,他在上海這座大都市居住期間,在華若翰的建議下,翻譯完成了惠頓《萬國公法》中的一部分;華若翰是1859—1860年這一非常時期的美國駐華公使,他認為惠頓的著作比歐洲同時期其他偉大的歐洲人的著作更能跟得上時代。

在將國際法引入中國時,丁韙良十分確信他是在將歐洲文明中的最優成果奉獻給中國,通過他的工作,中國政府能夠被拉近基督教世界一步。他在 1863年10月1日致朋友婁理華的信中提到,“一部大概能使這個無神論政府認可上帝及上帝永恆正義的著作;或許還能向他們傳授基督教精神”。他確信自己從事的事業“並非不適合一位感到有義務為其選擇傳教的國家尋求福祉的傳教士去做”。對於選擇惠頓的作品,他說:“對於作者的選擇,我問心無愧。我起先傾向於瓦特爾;但細細想來,這位地位卓越、用語顯豁的作者的作品如用於指導實踐,可能會顯得有些過時;將之引入中國無異於向他們講授托勒密的宇宙學。惠頓的著作除了能將國際法科學寫到今天,還是公認的全面公正的集大成者,它也正憑借這點進入了歐洲各 國的內閣。”在得知惠頓的該作品在西方是訓練翻譯工作者的必備書籍,也幾乎是歐洲和美國外交官的必讀書目後,他下定決心要讓中國人從這部普遍被接受的作品中受益。
惠頓的《萬國公法》(1836年)是關於國際法原理的第一部英文著作,甫一出版,便受到西方國家的青睞。美國國務院曾在1855年向美國駐華公使寄出過一本,但最終並未送達。不想失去這樣有用的工具,列衛廉在 1857 年又用公費購置了一本。惠頓的接受度由此可見一斑。
丁韙良進行翻譯時得到過一些中國士人的幫助。他下大力氣翻譯這部著作意在向中國人展示調整國際關係的西方原則,並未期待從中國政府得到任何讚助。但他很幸運。1863年夏,在中法產生矛盾分歧之際,總理衙門大臣文祥請美國公使蒲安臣向他推薦一部西方國家都認可的國際法權威著作。蒲安臣推薦了惠頓的書,並答應翻譯部分章節。他寫信給美國駐上海領事熙華德時提到了此事,並欣喜地獲知丁韙良碰巧已在做這件事。他極力鼓勵丁韙良繼續翻譯,丁韙良遂於 1863 年 6 月抵達北京。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見到丁韙良的手稿後,因“其適應中國處理新關係的需求”而對此印象深刻,並答應向文祥匯報此事。

蒲安臣在1863年9月11日成功地安排丁韙良同總理衙門四位大臣會面(這種會見原本是不合中國慣例的)。當丁韙良呈上四大本手稿時,文祥問:“這裡包括那二十四條嗎?這會是我們向外國派出使臣的指南。”文祥所說的“那二十四條”當然是指赫德的譯文。交談間,丁韙良保證“此書凡屬有約之國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參酌援引。惟文義不甚通順,求為改刪,以便刊刻”。
恭親王已從蒲安臣處聽說該書翻譯手稿一事並急於閱讀此書。經過仔細閱讀,他發現該書十分有用但不易理解,他向皇上上奏稱:“檢閱其書,大約俱論會盟戰法諸事,其於啟釁之間,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請。”恭親王命四位衙門章京與之悉心商酌刪潤,四 人中有一位是翰林。通力合作半年後,譯著終於竣稿。在赫德的提議下,恭親王撥銀 500 兩資助印行,其中三百部被分發到各省地方官員以資參考。
作為整項工程的支持者,蒲安臣對於中國人的熱情極為感激並向國務院匯報說:“作為回應,我感謝了他們所做的工作,稱讚該書是調整國際關係的規則大全,我告訴他們,雖然它的規定不具成文法的效力或者說與條約中的義務也不相同,但是仔細研讀此書仍將極有用處。這部著作已如期印刷出版,朝廷還向不少口岸城市及帝國內地的官員下發了此書。”丁韙良將此書獻給蒲安臣。為慶祝著作得以翻譯出版,恭親王及其隨從和兵部尚書董恂兼衙門大臣拍照紀念, 後者的手上拿著一本丁韙良翻譯的《萬國公法》。
丁譯《萬國公法》的文本批評
丁韙良作為國際法自然法學派追隨者的背景在其譯文內可清晰地反映出來,丁譯《萬國公法》較惠頓的原書帶有更為濃重的自然法色彩,雖然惠頓也是自然法學 派的一員。儘管丁韙良翻譯的準確性還有許多待改進之處,但如果考慮到他是跨文化傳播者的先驅,他的表現堪稱奪目。但如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的作品在嚴格意義上講不能算作翻譯,而是對於惠頓作品的詮釋。丁韙良意識到了這點,他在英文序言中說:“這裡向大家提供的翻譯是一個不甚合適的節本,儘管我認為略掉某些囉唆的討論也是合適的,比如有關惠頓先生在普魯士任公使時其住宅受保護的內容;有關萊茵河、聖勞倫斯河以及密西西比河航行權等具體而無關緊要的細致規定。在某些情況下,我還會對原書內容稍加壓縮以略去某些不必要的太過瑣碎的論述,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我會做些擴充,以使論述更加清晰。”
經過編輯的翻譯文本呈現的是半文言論述風格,這對於中國知識階層而言不會造成任何閱讀障礙,但是當該譯本於1865年引入日本時,本人面臨的就不僅是許多奇怪的新概念,還有晦澀難懂的文本。“國際法”被丁韙良譯作“萬國公法”,“蓋系諸國通行者,非一國所得私也。又以其與各國律例相似,故亦名為‘萬國律例’雲”(“律例”是指法律和條例)。
譯本的前兩頁描述的是世界各國,接下來是兩幅東 西半球的簡明地圖,這在惠頓原書中是沒有的。丁韙良翻譯的術語,儘管不甚精準,但也達意,不過它們中 的大多數現已不用。丁韙良將“International Law”譯為“萬國公法”,如今已被箕作麟祥 * 博士於1873創造的術語“國際法”所取代。“Principle”當初譯為“例”*, 現在譯為“原理”;“neutrality”最初被譯為“局外”, 現在則用“中立”。其他兩歧之處見下表:

很多時候,丁韙良的譯文相當自由不羈,只能被視 作是釋義而非翻譯;例如他將“Congress of Verona(維羅那議會)”翻譯為“四國管制西國”。但是他的有 些翻譯很不錯,比如他用“主權”來翻譯“sovereignty” 一詞,這個譯詞今天仍在使用。
如果將丁韙良的譯文和惠頓的原文相對照,讀者就可發現他對長句是怎樣自由地翻譯的。這裡舉國際法缺乏“普世性”的例子。惠頓在援引格勞秀斯、賓克爾舒科、萊布尼茨和孟德斯鳩等人的觀點後說:
There is then, according to these writers, no universal law of nations, such as Cicero describes in his treatise De Republica, binding upon the whole human race—which all mankind in all ages and countries, ancient and modern, savage and civilized, Christian and pagan, have recognised in theory or in practice, have professed to obey, or have in fact obeyed.(根據這些學者,世上並無如西塞羅在其《論共和國》中描述的那種可以約束全人類的普世國際法。沒有一種國際法是全人類—不論年代與國別,古代還是近代,野蠻還是文明,基督教徒還是非基督教徒—已經在理論或實踐上認可的,已經宣稱了遵守或是在事實上遵守了的。)
如將丁韙良對這一段的漢譯再回譯到英文,則如下所示: Judging from them there is no universally practices law as is said in Te-li [De Repulica], fo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ase that is accepted by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barbarians or civilized, within or without the Church.(以是觀之,並無得哩所謂遍世通行之法。蓋未見有古今萬國、蠻貊文雅、 教內教外無不認識遵行之例也。)
這般自由翻譯(意譯)的例子,全書中俯拾皆是,但所幸並未丟失原文的大概意思。日本學者西周對丁韙良譯作有所批判但又比較克制,他巧妙地評價道,翻譯是一件如此艱難的工作,即便其中沒有嚴重的錯誤,
人們也會禁不住覺得在語義色彩和文本的表現力上會有差異。但是,丁韙良並不害怕批評,並宣稱他碰到的困難只有那些“精通中文”之人才會理解。“他們對於我此次表現的批評,我會洗耳恭聽,但這要等他們也完成了同樣艱辛的任務且翻譯得幾乎沒有什麽瑕疵時才好。”
丁譯《萬國公法》的反響
雖然清朝官員們對丁韙良和蒲安臣的好意和所做的工作表示感激,但他們對於外國人的真正用意和《萬國公法》的實用性並不確定。他們擔心這個看似中意的結果有可能是一個陷阱,並懷疑它是“特洛伊人送給希臘 人式的禮物”。對於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他們很難相信外國人會只想著給中國帶來利益而一無所圖。《萬國公法》能否被全面接受,取決於它的價值大小。
1863年,當蒲安臣帶著丁韙良把未譯竣的《萬國公法》交給總理衙門時,曾說閱讀此書對任何一國都有益處,但清朝官員立刻就起了戒心。恭親王將此上奏朝廷時說:“臣等防其以書嘗試,要求照行,即經告以中國自有體制,未便參閱外國之書。據丁韙良告稱,《大清律例》現經外國翻譯,中國並未強外國以必行,豈有外國之書,轉強中國以必行之理。因而再三懇請。臣等窺其意,一則誇耀外國亦有政令,一則該文士欲效從前利 瑪竇等在中國立名。”

1864年,就在總理衙門編輯《萬國公法》手稿期間,一起外交事件的發生給清朝官員提供了驗證其實用性的機會。彼時普魯士和丹麥兩國正在歐洲交戰。新任普魯士駐華公使李福斯在當年春天乘軍艦抵華時,發現了從大沽駛離的三艘商船。他立刻將它們作為戰利品扣留。總理衙門對將歐洲兩國間的爭執引入中國提出抗議,擔心中國如坐視不管,可能會引發各國將該水域認定為公海的訴求,一旦如此,依據西方法律,它將不屬於任何國家。恭親王向朝廷解釋說:“且外國持論,往往以海洋距岸十數裡外,凡系槍炮之所不及,即為各國公共之地,其間往來佔住,即可聽各 國自便。”因此,他必須向普魯士公使抗議,以確立中國對該水域的管轄權限,並預防外國人可能對該水域提出各國公共洋面的請求。
普魯士公使辯稱,按照戰時歐洲戰爭法的規定,扣 押的地點距離海岸已足夠遙遠。恭親王堅持認為,該地點不屬於公海而是中國“洋面”,也就是“領海”的意思。“洋面”是漢語中既有的指稱沿岸海域的名詞, 相當於西文中的“maritime territory”(領海)。丁韙良將後者譯為“各國所管海面及海口”,不如“洋面”簡明。儘管恭親王是第一次運用國際法,但他沒有明確宣告他援引此法。他對領海原則的隱秘援用還有更有力的依據,那就是中普間已訂立的條約。他對李福斯說:“中國所轄各洋,例有專條,各國和約內均明此例。貴國和約內載有中國洋面字樣,較各國知之尤切,何得雲 殊不可解?”恭親王以擬拒絕定期接待普魯士新任公使為名,強化了抗議力度,他譴責李福斯以不恰當的方式開始履行其公使職責李福斯看到事態的嚴重性後 釋放了上述三艘丹麥商船,並賠償了洋錢1500塊。
丁韙良對於清朝運用其譯文的結果自然感到十分欣慰。1864年7月19日,他不失時機地告訴友人婁理華:“通過援引《萬國公法》中的一節,中國人近來促使普魯士的軍艦釋放了其在海岸捕獲的三艘丹麥船隻。”
通過綜合運用領海原則、條約及拒絕對李福斯的公使大臣接待等策略,恭親王為中國取得了外交勝利。惠頓作品的實用性業已確認,總理衙門是故上奏皇帝批準印行此書。恭親王在奏折內寫道:“臣等查該外國律例一書,衡以中國制度,原不盡合,但其中亦間有可采之處。即如本年布國(普魯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國(丹麥)船隻一事,臣等暗采該律例之言與之辯論,布國公 使即行認錯,俯首無詞,似亦一證。”朝廷隨即同意印行並在各省下發該書。

當修訂後的譯文印出後,丁韙良請總理衙門為該書作序並將四位“代為刪削此書之章京”的名字一並寫在序言之內。恭親王將丁韙良的意圖解釋為“藉中國之文物聲明,以誇耀於外國”。作序一事委託給總理衙門大臣董恂完成,完成編輯的四位章京等姓名也一並附列在序內。恭親王本人未能作序,大概是擔心引來朝廷內極端保守派方面的攻擊,他不願落一個與外國人交情深厚的名聲。丁韙良對此事的失望,可能會被洋務專家、日後擔任駐日本國副使張斯桂為該書撰寫的長篇序言所抵消。
董恂的序言十分簡短,態度也不明朗。他寫道:“今九州外之國林立矣,不有法以維之,其何以國?此丁韙良教師《萬國公法》之所由譯也。韙良能華言,以是書就正,爰屬歷城陳欽、鄭州李常華、定遠方濬師、大竹毛鴻圖,刪校一過以歸之。韙良蓋好古多聞之士雲。”
張斯桂的序言則數倍長於董序,頗為詳細地討論了西方的整體情況。在對英法兩國的強大和繁榮稱頌後,他又稱讚俄國的西化是國家通往自強之路的理想方式,他讚賞華盛頓致力於長官美國人民取得獨立而並未建立家族王朝。他將現代歐洲比作先秦時期的中國,俄羅斯像秦國,英法兩國好似楚國和晉國,美國像齊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則好似魯國和衛國,土耳其和意大利,猶宋與鄭。然後,他筆鋒一轉開始細述中國的寬巨集大量:“今美利堅教師丁韙良翻譯此書,其望我中華之曲體其情而俯從其議也。我中華一視同仁,邇言必察……凡重譯而來者,莫不畏威而懷德,則是書亦大有裨於中華用,儲之以備籌邊之一助雲爾。”
這兩篇序言顯示出中國人的西方觀已有提高。兩篇序言都公開承認中國之外還有強大而獨立的國家存在,這不亞於一場轉而放棄傳統天下共主觀念的革命。張斯桂序言後半部分的高調和傲慢大概是為了保留顏面,借中國的寬巨集大量抗衡西方國家的鋒芒。這也不失為避免保守勢力抨擊的策略。足以令人稱奇的是,對於這次引入外國知識一事,朝廷內並無明顯一致的反對意見,這大概是出於“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共識。間接批評這件事的跡象也只有一個。1867 年,醇親王在一份密奏內批評“董恂則一味媚夷,為之刻書作序”。就整體而言,朝廷和保守派對恭親王巧妙地在奏折內提到的“其中頗有製服領事官之法,未始不有裨益”這一判斷感到 十分欣慰。
對其譯書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丁韙良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他發乎於心地讚賞中國人對於那些過去2000年裡本來完全不清楚的新概念新理念的消化能力。他在其英文序言中樂觀地評價說:“對於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中國人做好了接受的準備。在他們的國禮及正典書籍中,他們承認人類命運終極仲裁者的存在,各國國王和親王接受他的授權並對他直接負責;理論上講,沒有人(比中國人)更願意承認終極仲裁者的法律是鐫刻在人心之上的。國家被視為非自然人,國家間的相互義務也是基於這一準則推演而出,中國人對此完全理解。”沉浸在有些膨脹的狀態中,他甚至寫道:“我相信《萬國公 法》譯本的影響只會僅次於《聖經》譯本的影響。”
丁韙良翻譯此書獲得的物質報酬是持續不斷的。把翻譯終稿交給恭親王時,他開玩笑地說:“閣下當然要 給我一枚獎章。我再別無所得。”他說這話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部著作會對他日後的事業產生巨大幫助。他在1868—1894年長期擔任同文館總教習及國際法教授,在1898—1900年間擔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總教習,一生獲得許多崇高的榮譽。
為了給自己在這部著作翻譯中所做之貢獻邀功,蒲安臣不失時機地告訴國務卿蘇厄德:是他成功地“使中國政府繼受並出版了惠頓的國際法”。他寄給美國國務院一本據他說是首印本的《萬國公法》,另外一本則作為個人禮物送給了蘇厄德,後者對此表示感謝並評價道:“中國政府對於國際法表現出的學習熱情再怎麽稱 讚也不為過。”美國使館的一位代辦衛三畏則擔心這本書會對治外法權特權形成衝擊:“中國和日本兩國官員對這本著作的切實學習,有可能會引導他們致力於把國際法的習慣與原理運用到他們同外國的交往之中。這將會使他們逐漸看到,他們同那些國家已訂立條約中的治外法權原則,是對西方國家和基督教國家間生效習慣 法的重大修改。”他隨後表達的期望是:“如果西方國家能夠聚焦於把這些東方民族提升到他們的水準,而不是鼓勵以治外法權原則顛覆本地的原則,那該會多麽 地令人愉快啊!”

國務卿蘇厄德給衛三畏回復時稱,他將中國人的熱情視作“中國對待西方文明的態度有了進步的證 明”。在1865年12月15日的一則公文中,他指示蒲安臣邀請中國向華盛頓地區派出一名外交代表:“鑒於大清帝國如今可能有了尊重公法義務的想法,我們覺得皇帝陛下的政府可能會顧及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這也體現互惠原則,至少也是我們盡到了禮數,他們派到這裡來的外交官可保證我們將依據兩國訂立的條約和國際法履行我們應對中國承擔的義務,他可以向中國政府報告這點以及其他感興趣的事 宜。”中國公使更可以照料僑居在加利福尼亞州的中國臣民,這對中美兩國都有利。蘇厄德甚至願意提 供一艘美國戰船將第一位中國外交官載往美國。
對於這一友好表示,清朝無動於衷。中國人不願這麽快就邁出這般巨大的步伐而棄傳統的對外交往制度於不顧。丁韙良的譯本或許更加堅定了他們的立場,因為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若不願遣使,他國亦不得相強。惟就常例而論,倘不通使,似近於不和。然通使雖為當行之禮,斷無必行之勢。其行與否,當視其交情厚薄、 事務緊要而定。”
英國在京公使卜魯斯從始至終在鼓勵丁韙良,他評價說:“這部著作很有用,它會告訴中國人西方國家做事所遵循的原則,武力並非這些國家唯一的法 則。”俄羅斯公使巴裡玉色克上校在 1863年告訴蒲安臣,俄羅斯政府希望中國能夠拉近同國際大家庭的關係,並能接受國際法項下的義務。丁韙良深受鼓舞,並因此在其前言中寫道:“(英法俄)三大國家一直是中國的夢魘,但它們將會放棄以犧牲中華帝國利益為代價而尋求擴張的野心,如果說它們的確懷有過尋求擴張的野心的話;相反,三國會團結起來去完成一件更為高尚的、造福人類的事業,它們將努力提升國際大家庭成員中這個歷史最為悠久、人口最為密集之 國家的地位並為其謀求福祉。”

另一方面,對於丁譯《萬國公法》之行徑,也不乏仇視者的回應。據丁韙良回憶,法國公館代辦哥士耆曾憤怒地詢問蒲安臣:“那個打算讓中國人領悟我們歐洲國際法的人是誰?殺死他—扼死他;他會讓我們陷於無盡的麻煩之中。” 在華外國民間團體對於丁譯《萬國公法》的反應不一。他們自封為西方文明在東方的衛道者和發揚光大者,故總顯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樣子;但作為不平等條約的受益者,他們又擔心中國人運用西方的方法來擊敗西方。上海《北華捷報》刊登的一則社論很有代表性:“我們為中國提供的武器在日後到底是會瞄準我們,還是只會轉向新的征服者,現在還不好說。我們現在的目標應是乘水流還在水源的附近而極力遏製 住它,並把它引向合適的管道。”
快,關注這個公眾號,一起漲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