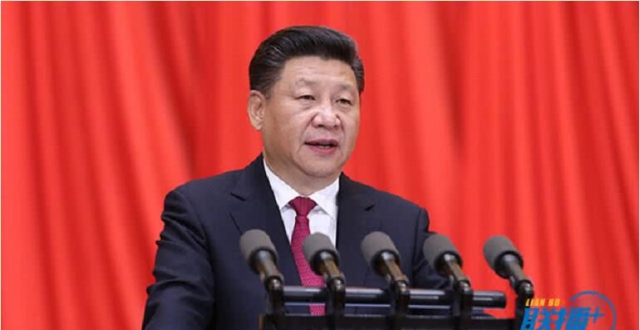昨日(11月12日),金庸告別儀式在香港舉行。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俠義江湖滿足了中國人對於另一個民間社會的文字想象。在他的武俠世界,總伴隨著日月神教、神龍教、明教等江湖組織的身影,構建了有別於廟堂控制的另一種民間想象。在最後一部武俠小說《鹿鼎記》中,金庸借鑒了秘密社會組織天地會的歷史與傳說。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的確總有著天地會或白蓮教等秘密社會的身影。他們或劫富濟貧,或落草為寇,甚至像天地會那樣致力於改朝換代。

由陳小春主演的《鹿鼎記》(1998)劇照。不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者科大衛(David Faure)認為,“多少我們以為是實體的名詞,隻不過是思想上的認同”,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實體的天地會。點擊劇照圖片查看往日文章《就像天地會從沒存在過,幻想的歷史需要考證》。
天地會的起源傳說,始於鄭成功和反清複明之間曖昧不明的歷史傳說。在中國近代史上,另一個民間社會組織,與天地會的起源同出一轍,那就是四川的哥老會,四川本地人稱之為“袍哥”。
既然袍哥與天地會的神秘起源歸於一宗,理所當然地,它們的活動目的也就殊途同歸了。尤其在近現代反清革命的歷史浪潮下,民族主義者或革命家們都急欲拉攏這樣的社會組織,一起加入驅逐韃虜的排滿革命隊伍。在組織的政治意識形態相同的情況下,這類組織就更容易被調動起來。

由劉德一(於2008年離世,年63歲)主演的《傻兒司令》(2003)劇照。該劇更早有《傻兒軍長》《傻兒師長》等,一度是川渝地區的熱播劇。
作為四川當地獨有的社會組織,袍哥在《傻兒司令》和《讓子彈飛》等影視或小說中,我們或多或少地能夠看到它們的身影存在。甚至在近代歷史的重大事件比如成都血案和保路運動,乃至於抗日戰爭中,無論是國軍抗戰,還是共軍拔城,袍哥都扮演著重要的社會作用。
那麽,袍哥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神秘組織呢?它為何能夠在中國近代史中扮演這麽重要的角色呢?在現代警察社會形成之前,袍哥這樣的民間組織又在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結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
今年10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笛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揭開這個民間社會組織的真實面目。作為國內新文化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師出著名漢學家羅威廉的王笛,早些年通過《街頭文化:成都公共太空、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館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等研究著作,向我們展示他在微觀史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底,讓我們從微觀的視角重新發現了中國社會的另一種面貌。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蕭軼
王笛從民國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沈寶媛的田野調查報告,發現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殺女凶案。正是借助這份塵封了70多年的畢業論文和被遺忘了近80年的家庭慘案,經過王笛30余年的不懈努力,在故紙堆中重返歷史現場,為我們講述了那個蒼涼悲愴的袍哥江湖,揭開了袍哥組織的神秘面紗,同時也為我們展現了傳統社會的民間秩序。

《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
作者:王笛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

王笛,1956年生於成都,1978年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習,1999年獲得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後任美國得克薩斯A & M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大紫江講座教授。2016年受聘擔任澳門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主任。著有《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街頭文化:成都公共太空、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等歷史專著。
袍哥江湖是如何誕生的
新京報:最開頭,還是想讓你大致概述一下袍哥的發展史。
王笛:簡單來講,袍哥就是四川的哥老會。哥老會的起源,歷史學界也是眾說紛紜。按照哥老會、天地會、洪門等講述的自己的故事,可能都有共同的起源,就是1661年鄭成功在台灣金台山開山堂結盟,類似於金庸《鹿鼎記》裡對韋小寶的司機陳近南的描述,鄭成功1670年把他派到四川雅安開精忠山,開始了哥老會在中國大陸的活動。但是關於袍哥的起源,也有各種其它的說法。比如說,有的說哥老會在清代原來叫啯嚕,但這也沒有定論,現在也沒辦法證實。但是,也並不能說它早期的故事就沒有意義。也有說來自《詩經》的“與子同袍”,意思是兄弟情誼。袍哥的經典文獻《海底》,把自己的歷史和鄭成功連在一起,政治用意和意識形態都很明顯,就是強調他們是反清複明的組織。從早期文獻來看,清政府對這個組織一直都在進行鎮壓。從各個時期頒發的禁令看,袍哥也一直在與國家進行對抗。
在大概十年前,我寫過一篇英文論文,在《晚期中華帝國》上發表,這是一個專門講述19世紀的中國的專輯,孔飛力寫的前言,另外還有五篇文章,我的文章談的就是袍哥的語言:通過袍哥的語言,來看他們的歷史和發展。我提出的觀點,就是哥老會的真正大發展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因為《海底》的印行和散布。按照袍哥《海底》的說法,1683年,清軍攻陷台灣,他們把這些早期的文獻放進一個鐵匣子,扔到了海裡。1848年,有個叫郭永泰的四川人,宣稱從漁夫那裡得到了最早期的金台山結盟文獻原件,然後把它整理出來。
《海底》作為一種文獻,也可能和鄭成功一點關係都沒有,也可能就是郭永泰自己創造的,或者他那個時代的人一起創造的。用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說法,很可能它的重要性就在於“發明了”他們的歷史和傳統。由於《海底》的這種影響力和號召力,他把袍哥的早期歷史和反清運動聯繫起來,所以在十九世紀以後,組織擴散非常之快,而且《海底》中的那些語言和歷史的講述也成為一種工具,便於他們的交往和溝通。

《成都江湖海底》內頁,圖片來自孔夫子舊書網。
在清代他們持續發展,在辛亥革命中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武裝起義等,並一度從秘密成為了公開組織。但是在民國政府建立以後,又開始禁止哥老會,到民國政府時期也是一直采取禁止的態度。但問題在於,整個民國時期,在政府的不斷限制之下,袍哥反而蓬勃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根據40年代的資料統計,有人說估計達到了四川人口的一半,也有人說達到了2/3。根據袍哥樊紹增的估計,四川成年男子的90%以上是袍哥。
1947年,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廖太初寫了一篇英文論文,發表在一個研究亞洲的加拿大雜誌《太平洋事務》上。在社會學的科學調查下,他估計佔成年男子的70%。其實,過去我也一直持懷疑態度,這麽高的比例是不是有所誇張?但是,這些年我閱讀檔案的結果,還真是印證了他們的說法,我想70%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大概在1951年左右,成都市政府要求各個茶館雇員,不管是做工的摻茶的,還是做表演的,都必須向政府登記。在登記表中有一欄,“是否參加過任何黨派”。根據現存的這些統計表,70%以上的說就是“無黨派,有袍哥”。1949年以後,下(底)層其實也沒受多少衝擊,大量的勞動人民參加袍哥,實際上也是為了尋求社會保護。例如加入某個行業,如果沒有袍哥背景的話,受到欺負毫無辦法,因為官府幫不了你,警察也幫不了你,那就只有靠袍哥這種組織。

沈寶媛畢業論文封面。
到了1940年代,袍哥的影響從上到下都看得到,政府、軍隊裡都有它的成員。比如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張瀾,民國時期當過四川省長、成都大學校長,這麽高的知識分子也參加過袍哥。再到城市裡的議會選舉,在40年代要參加議會的選舉,沒有袍哥背景,根本就無法選上。當時的報紙報導就說,在重慶有個政客瞧不起袍哥,他為人很清高,認為袍哥是三教九流之輩,不屑於來往。結果,他去參加重慶市議會選舉,才發現沒有袍哥的幫助是不可能獲得選舉的。事後,他不得不去投靠袍哥。結果呢袍哥對他反唇相譏:過去你瞧不起我,現在要來臨時抱佛腳了?
共產黨對袍哥在四川的影響也非常清楚,提前就做好了相關的準備,要利用袍哥的影響。在抗戰勝利以後,共產黨就派了杜重石作為地下黨加入袍哥,再通過民盟主席大袍哥張瀾,以袍哥的名義,創辦起《正義周刊》雜誌,在成都宣傳反專製、反國民黨、爭取民主的活動。當共產黨進入到四川以後,實際上他們早就已經建立了相關的聯繫,利用袍哥力量幫助共產黨接收城市和鄉村。因此,共產黨進入四川時,並沒有遭到袍哥的強烈反抗。
但是,為什麽後來又發生了袍哥暴亂呢?我在《袍哥》這本書裡也涉及這個問題。當時的鄉村是順利接收的,但接收四川以後就問題來了。共產黨的大軍,再加上大量的國民黨投誠部隊和俘虜,都需要糧食。但是在1949年底解放軍進入四川之前,農民的糧食和稅收已經交給了國民黨。但共產黨也需要糧食,徵收不到糧食,難免采取了一些激進的手段,結果引發了所謂的“土匪暴亂”。實際上,所謂的“土匪暴亂”,就是袍哥長官的地方暴力抗稅,這當然是以卵擊石的做法。不過,從今天來看,即使袍哥沒有武裝抗爭,結局也不會有任何差別的,因為新政權絕不可能讓一個能夠和國家對抗、對民眾有強大影響的社會組織長期存在。

新京報:袍哥在四川人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袍哥這種社會組織的存在,對川西社會傳統的塑造有著怎樣的影響呢?對於當下是否仍然存在某些方面的影響?
王笛:袍哥在四川的人口佔這麽大的比例,它的影響當然是非常深刻的。到20世紀辛亥革命以後,在每一個城市和鄉村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力量存在。到了40年代,如果地方政府要推行任何政策,如果沒有袍哥參與的話,就根本不可能實行,有的政策根本不能推行到地方上去,比如說收稅、征兵等等。
那麽,袍哥的影響為什麽會達到這樣的影響程度呢?這就是四川特定的歷史所造成的。辛亥革命以後,軍閥混戰,一直到1928年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全國,四川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四川真正被納入了中央政府管轄,直到抗戰快爆發的1935年。而在此之前,四川實行的是防區製,就是軍閥割據,分區管制。這種缺乏中央集權的政治格局,給了袍哥一個非常好的擴展機會。實際上,袍哥逐漸主宰了地方社會,控制了地方行政,包括地方治安。這種特定的四川歷史,為袍哥在地方的權威奠定了基礎。比如,20年代時四川土匪橫行,那麽地方治安由誰來維持呢?政府沒有力量穩定地方秩序,最後還是得靠袍哥。我在《袍哥》一書中的主角雷明遠,只是一個佃農,沒有經濟實力的,他的興起就是帶著他的袍哥兄弟平定土匪,從而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這種英雄氣概讓他混了幾十年。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大學生沈寶媛在下鄉之前,並不是已經準備好了要去研究袍哥這個課題,她當時的出發點是了解地方的權力結構,比如說鄉村怎麽管理的,誰來管理等等。到了那個地方,跟地方的各種人們聊天以後才發現,要了解地方權力結構,就必須研究袍哥;不研究袍哥,就沒辦法了解地方權力關係。就這樣,她把研究的焦點放到袍哥的身上,研究課題就是這樣形成的。所以,袍哥對鄉村社會的影響,乃至日常生活的乾預,都是非常之明顯的。
袍哥及其文化對今天的生活仍然或多或少地產生著影響。雖然在1950年代初,袍哥被徹底打垮了,但他們的許多“黑話”,已經融入了我們的日常語言中。比如“落馬”這個詞,過去指袍哥兄弟遇難了,現在指貪官垮台了,現在不僅僅是四川,其他地方都這樣表述。再比如打滾龍,就是指在底層社會混。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袍哥的影子都還在,更不要說存在著袍哥故事的影視劇小說,比如《讓子彈飛》就和袍哥有關。我在成都讀小學、中學的時候,就有同學講他們家父親或者親戚就是袍哥。
延伸閱讀:理解秘密社會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作者: 王學泰
版本: 同心出版社 2007年7月
我們對歷史一直存在誤解
新京報:在《袍哥》中,你寫到:“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川西農村基本沒有扮演任何角色。”而同時在兩湖、兩廣和江西等地,農民運動卻火如荼。再追溯遠一些,歷史上川西平原很少有農民起義,能否詳細說明一下這種情況?為何同樣是農業生產地區,這三個地方卻反而成為了農民起義的活躍地區?
王笛:我覺得有這麽幾個因素。一是成都平原是中國內地最富庶的地區,自從先秦時期都江堰修建以後,保證了穩定的農業生產,生態穩定,物產豐富,生活安定,農民生活相對其他地區舒適。在我70年代下鄉的時候,農民經常對我緬懷過去的時光,稱他們原來都隻做半年的活,夏冬是農閑的時候,隨便打理一下菜地,要不就做點小生意。但是人民公社以後就瞎折騰,搞得一年到頭都累死人,說過去做半年的勞作就足夠養活家裡了。在這種情況下,誰願意參加農民起義呢?農民起義也都是窮的地方比較容易爆發的,生活過不下去了,就會對現實不滿,窮則思變。實際上,農民是最希望安定的,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是不會鋌而走險的。
第二點,我覺得這跟川西平原的社會契約關係很大。《袍哥》書中雷明遠的案例就能說明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想象中,作為袍哥副首領,他手裡有槍,可以隨便開槍殺人,包括他自己的親生女兒都成為他槍下的受害者。但是,奇怪的是,由於他沒有按時交租,地主立馬就把40畝田給收回去了,這直接就導致雷明遠的衰敗,因為一幫小兄弟要由大哥罩著,平時為他賣命,那麽在他家蹭吃蹭喝。現在他無法給小兄弟提供任何好處了,那麽兄弟的忠心也就發生轉移了。為什麽地主敢於這樣做呢?就是因為這種契約關係,你沒交租,地主就可以收回,馬上轉租給另外一個人。這種契約關係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如果他既不交租又不還田的話,地方上的勢力是不會認可的,而他的聲望就是建立在這種遵守契約的基礎之上。
延伸閱讀:理解秘密社會

《天地會的儀式與神話》
作者: (荷) 田海
譯者: 李恭忠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18年9月
所以,我們對過去社會的知識,經常是建立在曲解或者想象之上,以為過去完全沒有秩序的社會。在傳統的穩定的社會系統下,士紳是需要做表率的,一到社會需要救濟的時候,他們就會在地方上做各種慈善,開倉放糧做粥廠,鄉村中的土豪劣紳其實是極少數的。我的《袍哥》有提到,那時候長工短工到了農忙時得吃五頓飯,其中有兩頓酒,地主雇傭他們,對他們的辛勤勞動必須抱以必要的尊重。
在土改以前,四川的土地分布其實是相對平均的,大地主也非常少,以中小地主、自耕農為主。在40年代時的關於四川租佃制度的研究裡,根據各種統計資料和當時社會學調查和經濟學調查,兩級分化並不是很嚴重。後來由於革命的需要,加上官方話語的塑造,我們所知的川西農村社會與實際情況之間的差距,是越來越大。

新京報:你也寫道,由於移民的流動性,宗族勢力並不如南方強大,但諸如江西也同樣存在大量移民,尤其是從閩粵兩地遷徙來的客家人,同樣存在著宗族勢力或者說宗法制度,一方面是凝聚自家實力,另一方面也為了抵禦土客之爭,甚至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時還特意提醒革命工作需要避免把土客矛盾帶入黨內。為何會出現這樣的不同局面呢?遊民文化與袍哥文化之間存在著怎樣的聯繫呢?
王笛:我不清楚江西的情況,但我覺得江西沒有出現像湖廣填四川這麽大規模的移民現象。實際上,好多四川人也是江西、兩湖、兩廣遷徙過來的,長途遷徙到長江上遊地區。根據我的統計,清初的時候,四川土著只剩下50萬人,大多數人口都是從外地長途遷徙過來的,土著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大。他們不知道到了長江上遊,或者到了四川以後,到底生活會是怎樣的景象,一開始就不敢拖家帶口地過來。實際上,遷徙群體以青壯年為主,大家族或者大宗族的遷徙非常困難。當然後來立穩腳跟了,也可能把親屬或同宗們陸續聚集在一起,但所佔的比例畢竟不大。所以,在四川,像華南地區出現的那種宗族主宰村莊的情況並不明顯,在城市中間更難見到了,都是經過幾代人的發展才慢慢建構起來的。
但是,移民到了陌生地方,需要各種幫助,那麽社會的組織就變得格外重要。在四川,很多組織就跟移民有關,比如同鄉人為主的會館,和同業為主的行會。例如來自江西的瓷器商,成立有自己的公會。但是,袍哥是可以囊括各個階層,而且地域分布非常廣的一個組織。而且,袍哥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只有地方的分支。一般來說,袍哥建立了一個山堂,或者建立一個公口,相對獨立存在,它並不隸屬於某個中心,所以它地方性比較強。像成都一個城市可以有三四百個公口,以仁義禮智信來分不同的堂口。當然,他們有時候也可能會聯合起來,如我在書中描述過一個退伍軍人在40年代就把威遠縣周圍幾個縣的袍哥聯合到一起。
新京報:那麽,就像在《袍哥》一書中,你寫到一個地方社會的“制度”和“力量”是多維度的,有著多種因素對地方的社會形態進行著塑造。為何這種傳統的社會秩序沒有形成諸如托克維爾特別強調的自治傳統,或者說形成某種大的社會傳統呢?而總是以地域性為特徵,卻沒有形成國家制度建構意義上的大傳統呢?
王笛:在我看來,其實是形成了地方自治的。羅威廉在研究漢口的時候,實際上他不同意馬克斯?韋伯關於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資本主義,是因為沒有形成城市意識和城市認同的說法。羅威廉研究了漢口各種同鄉會、善堂和行會等社會組織,發現無論是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這些組織都有自己的活動方式。後來我在研究成都時也發現,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是存在誤解的。我們總認為城市人沒有把城市當作自己的家,到城市去就是為了掙錢,掙錢後還是要回到老家的,死後屍體也得運回老家去的。當然,中國人自己也這樣說。其實,如果你去讀歷史文獻,你會發現,成都人對自己生活的城市的認同感是非常強烈的,這從他們身份、習俗、文化等方面都顯示出來。在晚清警察出現之前,城市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是自治的。

20世紀初的漢口。
在過去的城市裡,政府的角色非常有限,甚至沒有市政府。中國的城市真正有了專門管理機構,是1902年警察出現以後,才開始有衛生、交通管制之類的存在。在過去,城市衛生都是由城市的自治組織來管,比如行會、同鄉會、土地會等等。我舉個簡單的例子,過去,在清明節前,成都的土地會挨家挨戶地收錢,然後整個街區甚至幾個街區一起舉辦宴席,唱戲娛樂,吃完宴席唱完戲,就開始清淘陰溝(通水溝)。過去成都街上的陰溝都是死板蓋住,到了春天就把石板撬開,把下面的汙泥全部清出,農民就運到城外當肥料,這些根本不是政府來做的,全是由社會共同體來自己組織。那時候的社區意識和自我認同感,可能比我們現在強多了。
清末新政以後,在國家管理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才逐步介入城市管理,開始取代傳統的社會組織。到了民國,這種傳統的社會組織基本上被摧毀。現代化的國家認為,要把傳統的這些東西去掉,才能進行現代化的國家管理。可是,政府又無力乾預城市的一切事務,舊的傳統被摧毀了,新的制度又沒有出現,再加上沒有財力、物力、人力等等,城市生活中的好多事情實際上無人過問。這就是為什麽民國時期的成都水災非常厲害的原因了。
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誤解。好像是現代化的國家管理機器誕生之後,才有了城市管理。實際上,中國傳統城市是市民自己來管理的,社會的這種機制是長期形成的,從宋代以來就一直是小政府、大社會,讓社會組織與市民參與社區事務。現代國家乾預太多,不少人已經習慣於任何事情要依靠政府,而國家也樂意把資源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大國家、小社會的路子。
延伸閱讀:理解秘密社會

《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
作者: (荷蘭)田海
譯者: 劉平 王蕊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17年11月
歷史需要看到真實的人
新京報:在《袍哥》的序言中,你說本來想寫一本更為巨集大的《袍哥:一個秘密社會的歷史與文化》,但最終先擱置了這項寫作計劃,先完成了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不知道是否方便透露一下兩本著作存在哪些不同之處?
王笛:實際上,這是我一直在做的研究課題。從80年代開始,我就想寫袍哥,但是資料搜集比較難。經過30多年的資料積累,現在我認為可以寫一個比較全面的袍哥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專著了。不過,我不是像通史那樣來寫它,我的構思是三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寫袍哥的歷史和神話,或者說是“迷思”(myth),就是一些他們自己的傳說。第二部分是寫袍哥的儀式和語言,第三部分寫袍哥的網絡。
可以看得出來,這有點人類學的角度。原來是準備用一本書來完成這三部分,由於資料非常豐富,決定每一部分寫一本書,最後形成“袍哥三部曲”。現在出版的這本《袍哥》是聚焦於一個家庭,是帶有文學性描述的微觀史,而“袍哥史”三卷本是從17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三百年來相當全面的歷史,不過不會像現在《袍哥》這本那麽有文學性,但更具學術性。
新京報:在書中你也談論了“女人的命運”,有人說,中國近代婦女解放,從氣質、服裝到髮型,由於動蕩不安的革命形勢,從“文小姐”到“武將軍”的女性權利變遷史中,都呈現出男權化的象徵,以被迫消滅自己作為女性獨特性為代價,你怎麽看待這種說法呢?這是否對後來乃至當下女性通往自由之路產生某些影響呢?
王笛:其實,像秋瑾這些人還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從晚清現代化啟動,讓婦女發出聲音,或者主張婚姻自由、男女平等,顯然是受到西方的影響。但是無論是晚清,還是民國,依舊是主張女性魅力佔主角,女人男性化走的還是極端的少數例子。這種男性化的真正提倡和倡導,實際上是到了1949年以後才開始的,宣傳“男的能乾,女的也能乾”這類鐵娘子榜樣。其實,民國時期婦女們還是穿旗袍,很女性化的。到了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工農兵時代,這種抹殺男女區別的文化才真正發展起來。
如果看晚清民國時期的照片、繪畫和小說就知道,大家閨秀還是作詩、畫畫、刺繡等,這些都是作為女人美的一些常見的描述。但是為什麽人們會有婦女男性化這種印象呢?因為我們看到的都是那些站在時代前列像秋瑾那樣的異類女性。我是研究普通民眾史的,我知道她們並不能代表整體的女性,其實在女性中所佔比例也很小。即使我們來看當時的知識界,儘管受到西方的影響,但大多數的大學生、中學生和一般的中國婦女,以及男人對她們的審美,還是在正統的路子上。

民國女性。
新京報:我讀完《袍哥》後有個感受,不知道是否正確,就是感覺小敘事的成分較多,大歷史背景下的袍哥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似乎並沒有過多的著墨,也就是大的社會網絡之中的社會互動性稍顯弱了一些?比如成都血案、保路運動和抗日戰爭之間的袍哥角色都沒怎麽去寫……
王笛:對,主要還是因為時段。我這本《袍哥》的敘述時間圍繞的是1940年代,保路運動就是把它稍微提一下,主要還是著重在40年代。但接下來的“袍哥史”三卷本,絕對是事無巨細,會非常全面,而且資料也非常豐富。在袍哥的資料上,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世界上沒有誰能有我這麽豐富的資料,我持續了30多年的努力,很少有人做課題持續了這麽長的時間。
新京報:在《袍哥》一書中,能夠看到文學寫作與歷史研究的合流,甚至給我的感覺是文的成分比史的成分要大很多(從一般意義上來說),這就涉及一個文與史的結合的問題。在你看來,文與史之間到底存在怎樣的聯繫?
王笛:我一貫主張多學科結合,歷史學應該要和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等學科進行交叉。從司馬遷開始,中國歷史寫作本來就是有文學傳統的,反而到了近代以後,注重社會科學的方法,導致歷史研究缺乏細節,也缺乏人物塑造。如我第一本著作《跨出封閉的世界》,完全使用的是社會科學的方法,注重數字和統計。再看《袍哥》這本微觀史,講究敘事和描述,雷明遠這個人就有血有肉。在《跨出封閉的世界》中,書裡是看不到人的,只看得到事件,這就是巨大的不同。
所以,寫微觀史的時候,文學描述是完全可以利用和借鑒的。但我要強調的是,無論寫什麽歷史,畢竟都不是寫小說,不可以隨意去想象歷史,每一句話都得有根據,不能靠小說家的想象。這畢竟是史學著作,跟寫小說不一樣。就像在《袍哥》這本書裡寫到的川西平原的地理環境、田地、水牛、鴨子等看起來像是文學性的描述,但我的每一個描述都是有根據的。所以,雖然這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展開,但讀者看後面的注釋也是非常詳細的,可以找到資料的出處。
延伸閱讀:理解秘密社會

《發現另一個中國》
作者: 王學泰
版本: 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6年5月
我們的歷史太缺乏細節了
新京報:從辛亥革命前十年的經濟研究到《跨出封閉的世界》,從《茶館》《街頭文化》到《袍哥》,從國家層面到都市社區再到特殊群體,你的關注點越來越細,地域也越來越小,體現了你在歷史研究中的趣味性轉變,其間的變化是怎麽發生的呢?歷史觀念是怎麽發生變化的呢?
王笛:我覺得有兩種原因。一是到美國以後的學術訓練,在美國的學術訓練是多學科的交叉。而且,我讀博的時候就開始研讀新文化史的著作。西方歷史學語言學的轉向是1980年代以後,從社會科學向人文的轉向,對我有一定的影響。《街頭文化》和《跨出封閉的世界》,風格是大大不一樣的。在《跨出封閉的世界》裡,光是統計表就有200多個,一切都要把它轉化為數字說話;但在《街頭文化》裡,一個表都沒有,從數字轉向了歷史敘事。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史學觀的轉移。過去我們在國內受的歷史學訓練,還是一種英雄史觀,關注的是帝王將相、政治家、知識精英、大事件等等,並不關心民眾的歷史。雖然主流歷史學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是誰真正關心人民的歷史呢?我們過去看歷史,是站在上面從上往下看,歷史學家也站在上面俯視人民,而對皇帝、領袖、知識精英等,卻是仰視的。我認為,現在的歷史學應該回到社會的底層,從下往上看,站在人民的角度來寫歷史。我的《街頭文化》《茶館》《袍哥》,實際上都是這樣一種視角。
新京報:你出國前後……因為那個年代應該有城市史研究,跟那段時間有沒有關係?
王笛:出國前後是在90年代,那時候國內也開始了城市史的研究,其實我是也參與其中的。最早的都市研究都是中國社科基金資助的,最早有四個城市,即研究上海、天津、武漢和重慶,我參加的是重慶的城市史研究。但是早期的這些研究都是非常傳統的歷史方法,雖然也受到西方都市學的影響,但在方法上沒什麽突破。我真正的改變,還是到了美國受到西方的學術訓練以後,發生了方法論和史學觀的改變,整個思考問題的方式都不一樣了。
延伸閱讀:理解秘密社會

《元代白蓮教研究》
作者: 楊訥
版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6月
新京報:新文化史引進中國後,不僅在出版界,同樣在學界,乃至於社會讀者群體,形成了越來越龐大的一個歷史閱讀潮流,但與此同時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批評,就像新文化史是對以往歷史研究範式的叛變,其他歷史研究方向的派別也對新文化史進行了反撲。在你看來,新文化史是否可以從自身的角度去回擊那些反撲的批評呢?
王笛:批評可以理解的。史學本來就該多層次、多角度、不同的研究取向,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史學。如果大家都一窩蜂的來搞文化史,忽視了政治史、經濟史和戰爭史等等,那也是不平衡的歷史了。因此,歷史研究需要多元化。對於新文化史的批評,可能最大的問題就是碎片化的問題,認為新文化史研究的都是小人物,關心的都是小問題。在碎片化這個問題上,我專門有篇文章討論,總的觀點是,目前中國史學不是碎片化的問題,而是缺乏細節的歷史。因此,等許多年以後,等碎片化真正成為了問題,我們再來擔憂和糾正也不遲。現在至少在中國,還不成其為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的新文化史和微觀史還沒起步。在西方學界開始批評新文化史、微觀史,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家的有關研究已經持續了這麽多年了。
為什麽碎片化的歷史學會受到批評?根據我的觀察,是因為西方開始出現了批評的聲音,而且還有專著出版,但是我們的學者就立馬認為我們也出現了類似問題了。說實話,我們的史學研究還真的沒有到所謂過分碎片化的地步,我們的歷史研究還沒有那麽深。比如你去看日本的、歐洲的城市研究,那個事無巨細,令人歎而觀止。說老實話,碎片的歷史研究我們還沒有開始呢,可以去強調某方面研究可能有所偏頗,但是並沒有成為一種問題,現在擔憂這個問題其實還早著呢。現在的問題,反而是我們對歷史的碎片研究還遠遠還不夠。
新京報:我看到你的《茶館》第二部已經出版了,較之於第一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茶館這種都市公共領域又發生了怎樣的社會變化呢?會在國內出版嗎?
王笛:英文版已經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翻譯也已經交給北京大學出版社了,大概明年下半年可以出來。
在民國時期,政府也試圖乾預茶館,但影響還是有限的。在1949年以後,由於不鼓勵休閑,認為坐茶館是浪費時間和金錢,茶館不斷地萎縮,從50年代60年代到“文革”這一階段就達到了最低點。但在改革開放以後,茶館的數量一下就直線上升了,因為它們存在的土壤仍然在那裡。無論行政手段如何限制,只要社會的土壤在那裡,一旦有了條件,它們一下就猶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而且限制比民國時期還少。因為民國時期還有同業工會,同業公會就會去限制它的數量,以免發生強烈的內部競爭等等。在民國時期,600多家茶館就算是全國最多的了,平均差不多每條街都有一家。現在沒有數量的控制,兩個月前我看到成都市政府發布的數據,成都的茶館達到了9000多家。不過,成都這座城市也擴大了好多倍。
《茶館》第二部,主要是分成兩部分來寫的。第一部分是公共生活的衰落,從50年代到“文革”結束;第二部分是公共生活的恢復和發展。最近幾個月我也有幾篇相關的中文文章發表,在《開放時代》《澳門理工學報》《南國學術》等雜誌上,都有關於社會主義時期茶館的研究論文發表。

王笛在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封面。
新京報:聽說你正在著手做一項“五四”運動100周年的研究,“美國對五四運動的反應”,從大量歐美報章去梳理原始記錄來展開相關的研究。能否提前給我們講述一下 你的發現呢?西方對中國五四運動到底存在怎樣的反應?
王笛:明年就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了。資料收集倒是早就齊了,但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這項研究在明年是很難完成了。這個課題的來源,是我十多年以前給美國學生開寫作課的結果。因為美國學生不懂中文,但是寫作課必須要用原始文獻來寫研究論文,於是我就使用五四時期美國一些主要報紙,如《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時報》《基督教箴言報》等西方媒體對五四運動的報導,指導學生撰寫研究論文。後來我發現,儘管五四運動已經過去這麽多年了,利用美國媒體來了解這個運動卻基本沒有,我就一直想完成這個課題。實際上,我主要是著重在美國的媒體是如何看待中國五四運動的。當然,不光是五四運動,還包括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一直到20年代初期整個階段。
從美國的新聞媒體上,能夠看出美國各界是如何關注中國問題的,包括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包括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問題,特別是關注中國在凡爾賽會議的訴求問題。因為當時威爾遜就提出要建立國聯,要改變過去列強對弱國的態度,甚至對戰敗國也不訴求割地賠款,要建立一個新的和平的國際秩序。所以,威爾遜想要幫助中國,對中國的處境是非常同情的,但為什麽最後又放棄了中國,怎麽又沒有支持中國的訴求呢?我要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整個複雜的過程,從西方媒體特別是美國的主流媒體來看,當時美國是怎麽考慮的。非常明顯,當時美國的主流是站在中國一邊的,認為幫助中國就是幫助世界和平。但是新聞媒體也非常擔憂,特別是在五四以後,中國越來越傾向於倒向蘇聯,他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擔憂。後來所發生的歷史,也就真的印證了美國媒體的擔憂。
當然,雖然我隻研究到五四前後美國媒體的反應,但從美國對中國的新聞報導能夠看出:中國當時在世界大格局的國家地位到底如何?當時的中國政府自己又做出了多少努力?西方對中國的期望在哪裡?中國對西方的期望在哪裡?中國對美國的期望在哪裡?他們的矛盾點在哪裡?為什麽中國會在凡爾賽會議上經過了努力但是終究沒有達到自己的訴求?我就想去分析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
過去的這段歷史的研究,隻關心中國的資料,關心中國人是怎麽作出反應的。現在,五四運動快100年了,我想換一個角度,西方是怎麽看待這個問題的。這樣就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研究範式,就是站到世界的格局之下,去研究五四運動的歷史取向。但是這個整個過程研究起來非常複雜,難度超過了我的想象,所以進度也比較慢,估計明年是出不來了。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蕭軼;編輯:西西;校對:薛京寧。題圖素材來自《讓子彈飛》(2010)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