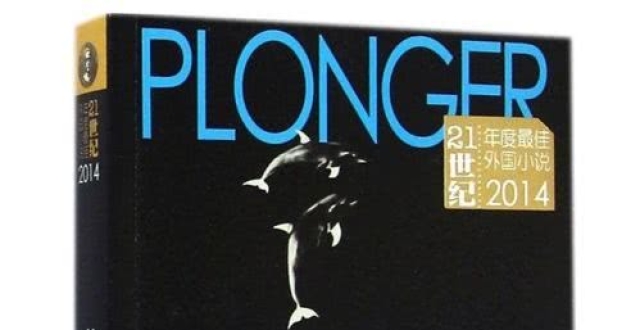2月13日晚,《北京日報》率先發出著名翻譯家戴驄先生去世的消息:記者從上海譯文出版社獲悉,原來早在6天前,2月7日7時,戴先生就在上海駕鶴西去,享年87歲。據出版社相關負責人透露,因為當前疫情影響,戴先生的葬禮已從簡辦理。
對於外國文學作品來講,有些老翻譯家的名字就是譯著品質和譯文質量的保證,比如董樂山、王道乾等等,戴驄在俄語文學翻譯領域的地位,無疑也屬於該行列。回顧戴驄一生的譯作,幾乎每本都是經典,比如《金玫瑰》、《紅色騎兵軍》、《哈扎爾辭典》等等,都在讀者中擁有極佳的口碑和影響力,一版再版,長銷不衰。
發現蒲寧
1933年,戴驄出生於蘇州,原名戴際安,戴驄是他為自己取的筆名,源於“青驄馬”。“一種很普通、很平凡的馬,但它能吃苦耐勞。希望我在文學翻譯的路上也是這樣。”戴驄接受採訪時曾經解釋道。
戴驄從事翻譯工作是從部隊起步的。他1949年入伍,1950年畢業於華東軍區外語專修學校俄語系,曾在部隊擔任譯員多年。1952年調至上海出版界,歷任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蘇聯語文學及亞非拉文學編輯,上海譯文出版社《外國文藝》雜誌編輯、編審等職。
根據目前能查到的資料,戴驄最早翻譯出版的一部譯作是前蘇聯作家安德烈·烏比特的長篇小說《新的源流》(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年),這部小說用現實主義筆法描繪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拉脫維亞的農村生活。這個階段,戴驄搞翻譯都是領導布置的政治任務,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

《新的源流》
戴驄真正開始大規模自主選擇翻譯出版作品,還要等到改革開放以後。“文革”期間,他在無人看管的出版社資料室裡發現了俄國作家蒲寧的原版書,“我渾身為之一震。原來俄羅斯現代文學中,除了卓婭、舒拉、保爾、奧列格之外,還有我所未曾見到過的世界,還有我所未曾讀到過的把人作為人來描寫、細膩地觸及人性因而令人回腸蕩氣的小說”。於是,他很快便著手翻譯,並在1981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蒲寧短篇小說集》。

《蒲寧短篇小說集》
這是戴驄翻譯出版的蒲寧的第一部作品。從此,戴驄便與浦寧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始系統性地譯介這位俄國作家。他除了和鄭重合作在安徽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浦寧選集》第一卷《新路》(1983年)和第二卷《最後的幽會》(1988年)外,還以個人名義出齊了三卷本的《浦寧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主編體量和內容更加完整的五卷本《浦寧文集》(安徽文藝出版社,2005年)。
重譯經典《金薔薇》
195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時翻譯的蘇聯作家巴烏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薔薇:關於作家勞動的劄記》。1987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由戴驄重譯的《金薔薇》,並更名為《金玫瑰》。

《金薔薇》李時譯本
新譯本出版後,戴驄給著名學者劉小楓寄去了一本。劉小楓讀完後,以“默默”為筆名,在1988年第6期《讀書》雜誌上發表了名篇《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重溫〈金薔薇〉》。在這篇文章裡,劉小楓回憶了自己初讀《金薔薇》時的感受,並將之上升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遭遇:
“我們這一代人曾瘋狂地吞噬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著語錄的教誨,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切竟然會被《金薔薇》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給取代了!我們的心靈不再為保爾的遭遇而流淚,而是為維羅納晚禱的鍾聲而流淚。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說,理想主義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們已經開始傾近怕和愛的生活。”
“《金薔薇》流入這一代人的心中,使其‘天生’而來的理想主義得以脫胎換骨。真正的理想應該是對受苦和不幸的下跪,應是懂得怕和愛的生活本身高於歷史理性的絕對命令,應是奔向前去迎候受難犧牲者基督的復活。”

《這一代人的怕和愛》
劉小楓這篇文章連同《金薔薇》對後來的整個漢語思想界產生了巨大衝擊和影響,例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就描述過當時“刻骨銘心”的震撼感受:
“默默在文章中說,《金薔薇》竟然會成為他所隸屬的一代人的‘靈魂再生之源’,還有什麽樣的表述更能凸顯《金薔薇》對他那一代人在精神結構中起到的作用呢?也同樣不誇張地說,默默對《金薔薇》的解讀也重塑了更年輕一代學子的情感體認,進而把新的文明質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結構中。默默由此也把《金薔薇》重新帶入八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歷史進程,使大部分國人所陌生的怕和愛的圖景構成了新時代的結構性因素。”(吳曉東:《與一代人的情感結構》,《天涯》2019年第3期)
由此可知,戴驄重新翻譯巴烏斯托夫斯基生前增刪修訂版《金薔薇》的意義。《金薔薇》的俄文原版書名為золотая роза,其中роза一詞在俄語中既可以指“玫瑰”,也可以指範圍更大的種屬名稱“薔薇”。戴驄根據書中第一篇《珍貴的塵土》,認為巴烏斯托夫斯基想表達的主旨是,作家應該對文學事業、對人民懷有深厚的愛,鑒於玫瑰是愛情的經典象徵,所以堅持把書名翻譯為《金玫瑰》,而沒有沿用舊版、已為讀者熟知的《金薔薇》。

《金玫瑰》戴驄譯本,這一版的譯者署名為“戴聰”,疑為“驄”字訛誤
巴別爾與布爾加科夫
伊薩克·巴別爾的《騎兵軍》最早由花城出版社在1992年引進,譯者為孫越。不過論及影響力和讀者人數,戴驄的譯本都要更勝一籌。戴驄翻譯的《騎兵軍》初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書名在“騎兵軍”前加上了“紅色”二字,此後人民文學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文匯出版社又都曾多次再版。

《紅色騎兵軍》
在譯後記《星星重又升起》中,戴驄如此談及巴別爾最重要的語言特色:“巴別爾的文體樸質無華,而又鮮活無比,用巴別爾自己的話說,他的作品的語言‘必須像戰況公報或銀行支票一樣準確無誤’。他的作品洗練、簡潔,沒有浮泛之筆,寥寥數句便勾勒出了一個形神兼備的人物,塑造出了一個色彩鮮明的性格。他只需兩三頁的篇幅就可寫出別人需要一本書來寫的東西。”戴驄通過自己“明淨如詩”的譯文,忠實傳遞出巴別爾作品的這一特色。
繼《紅色騎兵軍》後,戴驄又接著翻譯了巴別爾的另一部短篇小說集《敖德薩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反響依舊熱烈。

《敖德薩故事》
儘管巴別爾的作品在中國和全世界都得到了無數稱讚,恢復了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不過巴別爾本人的命運卻十分悲慘。
除了巴別爾之外,戴驄還翻譯過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前蘇聯作家米·布爾加科夫的作品。布爾加科夫與巴別爾在同一年去世,也是一位在生前遭“默殺”、死後擁有巨大聲譽的作家。布爾加科夫善於使用怪誕詭譎的魔幻情節進行現實批判和諷刺。
1998年,作家出版社推出四卷本的“布爾加科夫文集”,包括《劇院情史》(石枕川譯)、《狗心》(曹國維、戴驄譯)、《白衛軍》(許賢緒譯)、《大師和瑪格麗特》(戴驄、曹國維譯)。戴驄參與了其中兩卷的翻譯工作,這套文集的其余譯者也都是老一輩的俄語文學翻譯家,堪稱經典譯作。

《大師和瑪格麗特》
奇書《哈扎爾辭典》
2009年,塞爾維亞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因心髒病發去世,很多媒體在紀念稿件中都再次提起十多年前那場著名的文壇官司——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是否在內容形式上模仿了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
《哈扎爾辭典》原書1984年在南斯拉夫出版,戴驄最早在俄文雜誌上發現了這部小說的節譯,隨後便與友人石枕川一起從俄文將之譯成中文,節譯版發表在1994年第2期的《外國文藝》上。四年後,南山、戴驄、石枕川三人合譯的全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譯者之一的戴驄介紹:“與1994年《外國文藝》上發表的版本相比,此次譯作過程參照了法、俄兩個版本,並汲取了英譯本的長處,篇幅從121頁增加到323頁,展現了《哈扎爾辭典》的全貌。”

《哈扎爾辭典》(陽本)
韓少功的小說《馬橋詞典》初版於1996年,該年年底,北京大學學者張頤武在媒體發文,公開指控《馬橋詞典》“這部被一些批評者以熱烈的歌頌稱為‘傑作’、‘後現代主義’的文本的著作,卻不過是一部十分明顯的擬作或仿作,而且這是隱去了那個首創者的名字和首創者的全部痕跡的模仿之作”。張頤武這裡的“首創者”當然指的就是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韓少功對於這種指控並不接受,隨後選擇起訴張頤武和相關媒體,法院在兩年後裁定韓少功勝訴。
關於這場爭論,《文匯報》記者也訪問過戴驄的看法。戴驄認為,“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和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內容完全不同,形式上偶有相似,比如每個章節用了符號標注的方式……文學史上,作品面目相似、意旨不同的作品不少。當年,有人指稱加西亞·馬爾克斯抄襲布魯加爾科夫,馬爾克斯怒斥了這種說法,但是他在看了布魯加爾科夫的作品後稱其為‘天才作品’。所以,不能因為文體上的略有相似就此推斷韓少功抄襲。”
關於《哈扎爾辭典》一書的無窮魅力,上海資深文學出版人曹元勇如是說:“打開《哈扎爾辭典》,亦即打開了一個穿越時空、融匯現實世界與神秘之域的超級文本;而對它的閱讀,則會成為想象力被徹底激活的過程。實際上,《哈扎爾辭典》的強大魔力不只會讓你沉迷於這部作品本身,它還會徹底激起你的好奇心和探求欲,讓你順著各種蛛絲馬跡,去搜尋一切與這部‘辭典’或它的影子相關聯的資料。”(《讓人著魔的》,《新民周刊》2013年第20期)
記憶與遺忘
除了上述作家作品外,戴驄還翻譯過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左琴科、阿赫馬托娃、希什科夫、列·安德列耶夫等人的著作。為什麽要選擇翻譯這些作家的作品?戴驄如此回答道:“翻譯左琴科、阿赫瑪托娃、蒲寧的東西,是反思的結果,試圖探討真正的人性是什麽。國人和前蘇聯人遺忘的角落、忽視的角落,甚至被蔑視的角落,我會去那裡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覓得值得被介紹的東西。”(《戴驄:我隻譯介自己引為同類的作家》,《北京青年報》2007年7月30日)
左琴科是前蘇聯最優秀的幽默諷刺作家之一,寫過大量諷刺蘇聯市民階層市儈習氣的短篇小說,他的作品早在民國時期就被譯介到中國,魯迅、柔石等左翼作家都曾翻譯過他的短篇小說。從1943年開始,因為《日出之前》這部小說,左琴科遭到抨擊,並被汙蔑為“誹謗者與賤痞”,長期生活無著、人格受辱,最終在貧病交加中去世。戴驄翻譯的《日出之前》(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在中國出版也並非一帆風順。其實早在1980年代後期,戴驄就應國內某家頗有聲望的出版社之約譯完了全書,還寫了一篇萬餘字的譯後記。不料好幾年過去,那家出版社因“征訂不到足夠的印數而無法將其發排”,戴驄不願為難對方,便承諾若將其譯稿退還,則無償廢除合約。結果,譯稿很快便從出版社退回,但那篇譯後記卻因為人事變動而不知所蹤。
繼百花文藝出版社之後,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再版《日出之前》,卻不明就裡地更名為《幸福的鑰匙》。新星出版社2012年再版時該書又被拆為上、下兩冊,恢復《日出之前》的書名。比書名更尷尬的是,三個版本的作者國別標注居然都不一致,1997年是蘇聯作家,2009年是俄羅斯作家,2012年又變成了烏克蘭作家。從此側面也能反映出中國出版界的混亂現狀。

《日出之前》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戴驄先生一生為人低調,儘管為讀者貢獻了那麽多一流的俄語文學作品,他卻極少宣傳自己或接受採訪。最後,借用巴烏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中的一句話來形容戴先生,雖然巴烏斯托夫斯基講的是作家,但同樣適用於這位默默耕耘、抵抗遺忘的可敬譯者——
“是什麽促使作家去從事他那種雖然有時令他痛苦,但卻是美好的勞動的呢?首先是他自己心靈的召喚。良心的聲音和對未來的信念不允許一個真正的作家像一朵不結實的花那樣在世上度過一生,而不把充滿他內心的巨大、豐富的思想和感情,慷慨地、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