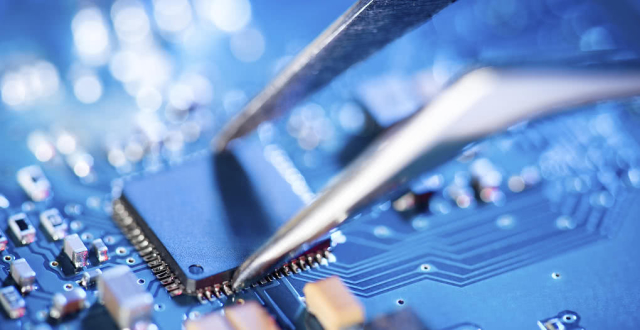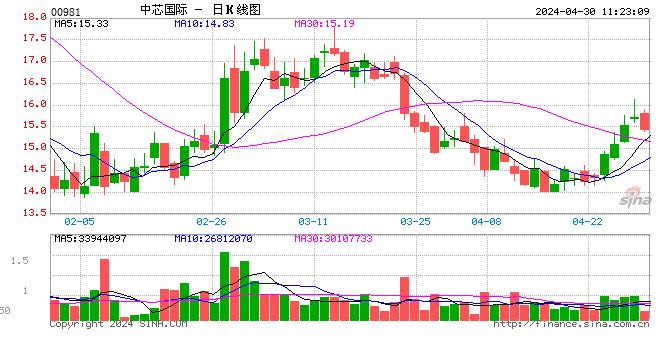技術全線落後,人才受互聯網行業擠壓,國產芯片從業者都需要懷著一顆赤子之心。

文 | 林北辰
中興的陷落,讓國人對“芯片”這個熟知已久的詞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根據《2017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現狀分析》報告,中國的國產芯片在核心集成電路中的佔有率極低,在通用電子系統等多個參數中,國產芯片的佔有率甚至為0。
2014年起,國家對集成電路產業投入的資金已達上千億規模,業內俗稱的“大基金”(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也即將迎來二期2000億元的投資。
然而,比起Intel、ARM等半導體巨頭的數十年研究,中國科研即使快馬加鞭也無法望其項背。
芯片的試錯成本高、排錯難度大,專利被巨頭壟斷,讓這個行業的發展注定艱難。這樣的困境中,一線從業人員生存狀態如何、對行業的看法怎樣值得考量。
界面新聞採訪了數位芯片行業相關人士,他們有的是從業十年的資深設計師,有的已經轉行,有的還在大學裡躊躇不前。
通過這些一線人員的故事,我們試圖探討在時代的桎梏中、在國際貿易戰打響的今天,國產芯片業究竟擁有怎樣的風貌,整個行業又將何去何從。
總體來說,芯片行業的從業人員大多有高學歷、名校背景,一旦入行,很少再選擇轉行。但一個殘酷的現實卻是,新鮮血液嚴重缺乏,越來越少的年輕畢業生願意選擇深耕芯片業。
韋晟:芯片設計經理 從業十年
複旦微電子系畢業後,韋晟加入了目前就職的這家芯片製造公司。在這家公司,他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前,國人對芯片行業的態度比現在要樂觀許多,互聯網的勢頭沒有如今這麽鋪天蓋地,芯片設計還是高精尖行業的上層選擇。像韋晟這樣的複旦畢業生,即使只是本科學歷,依然是就業市場上的香餑餑。
韋晟生性靦腆,對賺錢也沒有太多野心。找到工作之後,他覺得專業對口,又能留在上海,芯片設計是不錯的職業。工作的十年間,他和妻子在上海買了車,買了房,生了小孩,也見證了公司總部從海外遷回上海的全過程。
韋晟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成立於1995年。兩年之前,中國大力扶持紫光國芯,對他們這樣海外注冊的公司也提供了利好機制。紅利之下,公司順勢將總部遷回國內,總部設在上海。
公司雖然在海外注冊,上海的研究室卻一直是科研重點。對韋晟這樣的芯片設計師來說,總部的遷移沒有改變他的工作環境,而是為他的團隊爭取到更多的項目機會。
這家半導體公司主營電子消費品的芯片設計,專注於高集成度的多媒體soc芯片,擅長聲音處理與系統記憶體,在美國加州、上海、深圳和香港都設有分支機構。天貓精靈、智能音響等產品的問世,為韋晟帶來了更多項目,目前業內許多智能音箱內芯都能找到這家公司的影子。
設計師們規劃圖紙和模型,然後公司將製造的流程外包給台積電等企業進行芯片製造,最後再將成品的芯片拿回企業進行再次加工。
韋晟透露,除了華為海思,目前中國企業並沒有獨立製造芯片的能力,公司將製造外包給台積電,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技術的迭代落後。
台積電和Intel等頭部企業能達到的半導體最精細尺寸為7nm,為別的企業代工出來的產品多為14nm至16nm。這個數字對國產企業來說,還停留在28nm,更準確地說是在28nm向14nm的維度跨越。
工藝能達到的尺寸越精細,生產成本就越低。同一款芯片,如果中國要自主生產,成本至少是台積電的兩倍。若以時間丈量,國產企業與台積電的差距為5年以上的科研時間,目前的技術發達程度和台積電的上一代持平。
工作這麽多年,韋晟所在的公司一直是行業中上流企業,究竟哪家能造機器,哪家流片做最好,都是幾十年積累的成果,不是一波錢就能改變的現狀。他漸漸覺得巨頭們打下的江山,他們是不可能撼動了。
上海的工作相對忙碌,韋晟每天早上八點出門,開一個小時的車到公司,幾乎天天都是八點下班,周末的常態是隻休一天。遇上項目期,為了和同行拚速度,他還需要帶領團隊連續加班,一年之中,約有三到五個月都是這樣的狀態。
對於職業發展和國產芯片業的未來,韋晟沒有表示出太多熱情。同行的從業者鮮少轉行,因為硬體轉軟體要面臨技術上的難關,在同一行業,即使跳槽也很難拿到目前薪水兩倍的待遇。
韋晟認為,國產芯片業目前面臨的是企業與政府的雙重困境。
這樣一個投入巨大卻不常產出的科技領域,政府的扶持是改善行業現狀的基本要求,但外面的對手那麽強,國家如何帶領企業趕超是首屈一指的難關。對於已經身陷囹圇的國產芯片企業來說,要擺脫技術的桎梏,不再依賴進口,除了加強科研以外,市場與反壟斷也是持久的戰爭。
當問到中國芯片技術是否有機會和美國持平,韋晟無奈地說,“誰知道呢。我也希望我們能夠實現,但是這一天也許永遠都不會到來。”
梁宇:華為海思DFT工程師 從業一年
下午六點,成都的華為研究院門口準時出現了梁宇的身影。他的心情不錯,這是他本周第三天準時下班了。
2017年6月從電子科技大學碩士畢業之後,梁宇就進入了華為海思在成都的研究院,職位是DFT(design for test)工程師,主要負責芯片設計到投入市場之間的一整套測試流程。
臨畢業的時候,成績優秀的梁宇手上拿了十幾個offer,他最終選擇留在成都,進入國產芯片行業領頭的華為海思,女朋友也同在芯片行業的美國芯源MPS。
談及智能手機芯片,海思半導體在國內是繞不開的話題。海思公司成立於2004年,前身是華為在1991年創立的集成電路設計中心,系華為的全資子公司,華為手機搭載的麒麟芯片就是由海思生產。
DFT工程師的職業狀況,和芯片行業大公司的崛起息息相關。隨著數字芯片規模的壯大,芯片測試成本增加,準確定位錯誤發生地成為生產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小公司由於產能小、設計簡單,對DFT技術的要求並不高。而大公司裡的DFT工程師,要同時具有完備的前端與後端知識,是綜合型人才的一種,他們的數量也與產品複雜性形成正比。
雖然海思能夠自主生產,但許多技術專利還是需要和國外巨頭合作。以內核為例,華為的技術架構使用的就是英國公司ARM的專利。ARM不製造芯片,只靠知識產權就成為了Intel、IBM、三星、華為等公司的合作夥伴,是全球領先的IP提供商。
對此,梁宇覺得無可厚非。他認為,許多人把這個行業想得太多悲觀,中國芯片行業其實是良性發展,行業性質也決定不可能實現“大躍進”。芯片是一個全球化非常高的東西,流程長、周期長,有什麽配件造不出來,委託別家做,是每個芯片產商都會做的事情。如果不和美國相比,光看中國自己的芯片發展歷程,總體來說還是穩步上升。
正是由於DFT屬於高尖技術,應用領域相對狹窄,一旦入行,如果不是一心想離開,一般不會轉行。梁宇身邊的同學、同事幾乎都選擇了深耕半導體,在華為實驗室裡更是能見到從業四十年以上的資深人員。
即使互聯網對高校人才敞開大門,吸引各個專業的學生入行,但和他類似背景的畢業生,在芯片行業找到心儀工作也不困難。
DFT工程師的起薪20萬,以華為的薪資水準來說並不算高,卻足以讓梁宇在成都這樣的城市活得安逸舒適。女朋友是同行,他們彼此工作都忙,但每周末都有時間相聚。梁宇覺得,自己和全中國千千萬萬平凡的上班族沒有什麽區別。
成都的房價對年輕人十分友好,梁宇的工作前景也足夠可觀。26歲的梁宇覺得,是時候在成都買房、安家了。
林剛:軟體工程師 從業六年
夜晚的上海華燈初上,林剛結束了公司裡的培訓,走出公司的時候已經十點了。
他打了個長長的呵欠,心想項目快完成了,明天上午能不能晚點兒去公司。工作6年,林剛依然像當初剛入行的時候那麽拚。
林剛的本科和碩士就讀於上海某高校的微電子專業,畢業之後投身了軟體。
頗為戲劇的是,當時他到心儀的公司面試,應聘的職位是芯片工程師,卻被軟體部門看中,勸他留下來做安卓軟體開發。
芯片部門負責人還沒有給林剛回復,軟體部門的面試官就找上了他。面試官看出林剛性格開朗、思維跳躍,對芯片以外的行業也興趣滿滿,似乎並不是一心造芯片的樣子。
剛畢業的林剛沒有社會閱歷,在春風滿面的面試光面前稍顯局促。三言兩語,他就向對方攤了底牌,表示自己也沒有想好要不要進入略微枯燥的芯片行業。
但林剛也擔心,學了七年微電子,轉而開發安卓軟體,自己豈不是要從0開始,比一個本科畢業生還不如,怕浪費了自己的碩士學歷。面試官笑笑,拍了拍他肩膀,給了定心丸,“你芯片都搞的好,區區java和C++怎麽可能難倒你。”
一位負責設計,尤其是模擬設計的芯片工程師,至少要在行業上磨練三年才算得上“上手”。而這樣的磨練,如果不是在行業一流的公司,幾乎沒有意義。芯片行業有句流傳很廣的話,叫“第一名吃肉,第二名喝湯,第三名要完蛋”說的就是芯片業技術與資金都隻留存在頭部企業的殘酷狀態。
讀書的時候,導師曾經帶領林剛和班上的同學練習流片,學校給了導師二十萬元的經費,按理說已經不少了,但一次流片失敗之後,這二十萬元就打了水漂。
比起考驗耐心、投入卻不一定有回報的芯片,軟體行業的高薪和機遇對林剛具有十足的誘惑力。
如今,林剛已經做了6年的軟體工程師,他說對當初的選擇沒有後悔過。
像林剛這樣,學了7年微電子,最終投身互聯網的人才不在少數。光是他所在的研發小組,就有另外兩個複旦的微電子專業畢業生和他做了一樣的選擇。大學的同班同學,也只有6到7成還堅持在芯片行業。
直到今天,林剛看到中國芯片做出28nm晶體管,即將達成14nm的新聞時,還是會感歎,中美芯片業的差距在工藝上來說也許只有5年,但從商業角度來看,要追趕上搶佔了先機的巨頭,也許永遠不可能。
“如果我當時選擇了芯片工程師,那我可能一輩子都在做一件事。芯片行業就是需要你一直鑽研,是一個必須耐得住寂寞的行業。”
成月:美國模擬電路碩士在讀
在美國德州就讀模擬電路專業的成月,是眾多華人留學生中的一員。
本科畢業之後,成月申請了美國多所排名前50的學校。擺在她面前有兩個選擇:要麽堅持自己的喜好,到德州繼續學習模擬電路;要麽聽從學姐的建議,接下軟體的offer,將來從事電腦行業。
身邊人勸她,互聯網機會多,工資高,拿到綠卡的幾率也比較大。但是靠著對模擬電路的一腔熱情,她還是選擇了TAMU(德州農工大學)。
芯片行業有兩大分支,分為模擬電路芯片(analog IC)和數字電路芯片(digital IC)。
人們生活的世界裡,又分為模擬信號和數字信號。所有的數字信號都擁有非0即1的特性,而生活中的光與聲音所發出的信號是0到1之間的任意一種信號,稱為模擬信號。換言之,數字信號是單一的,而模擬信號是連續的。
將模擬信號與數字信號互相轉換的技術被稱為ADC(A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or),即人們常說的數字模擬轉換器。通過數字模擬轉換器將模擬信號和數字信號互相轉換,只能識別單一數字信號的手機才能夠識別人類發出的聲音,反過來也是一樣。
類似的功能在許多電子產品上都有所體現,可以說,ADC就是現實世界和二維數字的“翻譯器”。成月所研究的領域被稱為sigma delta ADC,是ADC的其中一個分支。
然而,她無奈地發現,這項十分重要的技術,卻由於資金耗費巨大、人才流向互聯網行業等原因,在中美兩國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芯片業從電路的設計、畫圖、版圖,至最終的流片(即製造成品),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整個過程要花費上千萬元。芯片恰恰是需要不斷試錯、多方領域共同合作的一個行業。昂貴的代價,高度集中的技術,讓學生們的實踐經歷缺失,對留在芯片這個行業也並不執著。
即使成月的導師已經是這個細分領域的“大牛”,她依然對是否繼續深造懷著觀望的態度。
同系的師兄讀了五年模擬電路的PHD,畢業之後華麗轉身去谷歌當了‘碼農’。棄芯片轉硬體,是許多ADC學生迫於就業、行情等壓力無奈的選擇。
拿到offer的學長回學校請成月吃飯,頗為感觸地勸她,即使喜歡模擬電路,空閑的時候多了解一下編程也是為自己留一條後路。
成月不禁問自己,當初拒絕別的offer,一頭栽進模擬電路,她的選擇是對的嗎?
由於發展時間久,行業趨於成熟,科研領域的每一塊土、每一片地似乎都被前人挖掘過,芯片業在美國已經算得上“夕陽產業”。
除去科研的瓶頸,行業薪資水準也在催促成月盡快轉行。隔壁電腦系的同學一個小時能賺50美金,而她們模擬電路的學生卻只能拿35至40美金的時薪。
對成月來說,如果想要繼續深耕芯片業,擁有美國的工作經驗再回國是她目前心儀的選擇。一是因為她在學校學的知識與國內實踐接不上軌,更重要的還是美國芯片業的工作經歷比她的學歷還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
然而,同許多華人留學生擔心的一樣,在中美芯片業差距依然顯著的現在,中國芯片業的投入產出比不平衡,常常投入巨資,卻無法得到理想的結果;如何平衡這樣的偏差,國家又是否會繼續對國產芯片這個昂貴的行業不計回報地投入資源,是成月躊躇不前的原因。
陳司:中科院博士生 從業兩年
90後陳司是中科院的博士在讀生,同時也是龍芯公司的芯片研發工程師。身邊朋友常說,陳司是徹徹底底的木訥理工男,平時沒事就泡在實驗室裡,連女朋友也不上心找一個。
芯片行業職位眾多,設計也分很多流程。陳司的職業屬於芯片設計的上層,負責寫verilog代碼、設計架構,除此之外的流程有物理設計、流片等。
陳司一邊讀書,一邊在龍芯做設計師。芯片的科研不比其他領域,入門要求高,對經驗和知識儲備更高。一直到研究生的時候,他才想好自己的職業方向。
中國芯片業與美國相比,無論上層設計還是製造生產都處於全線落後的狀態。陳司發現,芯片設計整個行業需要經驗積累,並不是出現幾個天才人物就能夠快速崛起的行業。
縱觀Intel的發展歷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設計芯片,目前的設計人員已經是全球頂尖了。但即使是Intel,對每一代芯片的推進都不能一蹴而就。
局限技術推進速度的因素在於兩方面:一是物理器件,芯片的基本單元——晶體管的尺寸越小,芯片運行的速度越高,這是頻率提升最重要的因素;二是架構改進,除去昂貴的試錯過程,對於架構的改良需要每個方面都投入人力和時間。
導師為陳司分析,目前中國芯片業的水準大約處於Intel的中期水準,這指的是設計。在設計以外的領域,才是中美芯片業難以跨越的鴻溝。
陳司常常想,如果有一天國產芯片技術趕上了國外巨頭的步伐,製造和流片都達到一樣的水準,中國芯片就能揚眉吐氣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
歸根到底,芯片不是產品。要造出好的產品如蘋果電腦、安卓系統等,還需要與芯片適配的頂層APP與作業系統。由於軟體硬體生態的不完善,即使芯片造出來了,中國製造依然不會成為首選。
幾十年的發展,電子消費業早就形成了特定的“圈子”。PC系統一般適配Intel的芯片架構,手機系統無論是蘋果還是安卓都是更適用於ARM架構的芯片。
中國製造的電子產品如果想要達到世界頂級,芯片之外,還需要設計一個與中國芯片配合良好的作業系統。在此之上,APP也需要大量人力和金錢的投入。只有生態完善了,中國製的CPU才真正獲得了競爭力。
重重困境之下,陳司卻更堅定了深耕芯片的決心。
他相信,正是由於中美兩國在芯片上的落差巨大,才更需要更多人投身科研。雖然做芯片設計的工資沒有軟體高,但現在正是需要芯片人才的時候。即使中國在芯片行業隻處於Intel的中期水準,但國外巨頭們的技術瓶頸與緩步發展給了中國科研追趕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