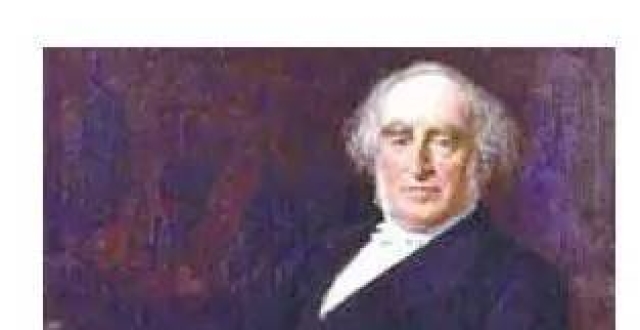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中華讀書報》2019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
郵發代號1-201
1
我從1991年9月認識倪慶餼先生,於今已29個年頭,不算太長,可也不算太短。在這段時間裡,我前前後後,寫了長短不一的八篇文章,或是評介倪老師翻譯的書,或是記述他的生平或和他有關的故事。最早的一篇是發表在《博覽群書》1995年第5期的《從柳無忌開始》,評倪譯柳無忌著《中國文學新論》,最近的兩篇則是發表於《光明日報》2017年3月28日的《知識如水,智慧如光》(評赫胥黎《水滴的音樂》),和發表於《隨筆》2017年第5期的《倪慶餼》。這八篇中,有兩篇篇幅稍長,有一萬字。不過,這幾篇文章,都是倪老師在世時寫的。他去年過世之後,我並未寫什麽。最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要出版倪老師的三本書,囑我寫幾句。現在再寫,就是第九篇了。我希望,這篇文章,能把我對倪老師的思念寫盡。

2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散文熱席卷全國。天津的百花文藝出版社領一時之風騷。當年,他們出了兩套大型散文叢書,一是中國的,叫“百花散文書系”,包括古代、現代和當代。還有一個是外國的,叫“外國名家散文叢書”,兩套叢書影響都很大。1991年時,就已推出第一輯十種,包括張守仁譯的屠格涅夫,葉渭渠譯的川端康成,葉廷芳譯的卡夫卡,戴驄譯的蒲寧,還有《聶魯達散文選》《米什萊散文選》等,這第一輯中的《史蒂文生遊記選》即為倪慶餼譯。由此開始,百花每年推出十種中國散文,十種外國散文。百花主持此事的副總編謝大光,每年請倪老師翻譯一本,連續若乾年:第二輯《赫德遜散文選》,第三輯《小泉八雲散文選》,第四輯《普裡斯特利散文選》,而盧卡斯和高爾斯華綏兩本,是在同一輯裡一齊出版的,可見當年譯者倪慶餼的熱情與多產。
倪老師翻譯這些作品,從選目開始,就有講究。他不是抓著什麽譯什麽,而是研究文學史,查找《牛津文學詞典》等工具書,專找那些有定評的大作家的作品,而且是沒有中譯本的。所以,幾十年下來,把倪譯作品集中放到一起看,就會看出其獨特價值:一是系統性,二是名家經典,三是填補空白,四是譯文質量高。他覺得,有那麽多一流作品還沒有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完全沒必要扎堆去重複翻譯那些大家熟知的作品,儘管那些作品會更賣錢。倪老師曾對我不止一次說過,與其自己創作二流甚至三流的所謂作品,不如把世界一流的作品翻譯過來,更有意義。如果沒有倪慶餼的譯介,這些英美一流作家的散文經典,一般中國讀者很有可能至今都不會讀到。
倪老師翻譯的作品,以英美散文為主,其中,又以英國散文最為集中。這個“美”,不僅指美國,也指北美,也就包括加拿大。這些作品包括史蒂文生的《驅驢旅行記》,康拉德的《大海如鏡》,威廉·亨利·戴維斯的《一個超級流浪漢的自述》《詩人漫遊記 文壇瑣憶》,多蘿西·華茲華斯的《蘇格蘭旅遊回憶》《格拉斯米爾日記》,阿爾多斯·赫胥黎《水滴的音樂》,希萊爾·貝洛克《海港集》《羅馬行》,《小泉八雲散文選》《高爾斯華綏散文選》《普裡斯特利散文選》《盧卡斯散文選》《愛默生日記精華》等等。倪慶餼已經出版的譯作,我有24種,加上今年即將出版的兩種,和尚未出版的《倫敦的鳥》,大約27種。這其中,又有四本關於鳥的書,自然引人注目。

譯者大概是真正體會到了赫德遜、邁納爾對鳥的那種感情。在大自然中,大多數鳥對人是無害的,其中許多還是有益的。又因為大多數鳥都很美,有觀賞性,而且能飛,就比草木更多了幾分靈動,與走獸比,則更多了輕盈與超凡脫俗的氣質。鳥,不論在東方還西方,自古就寄托了人類飛翔的夢想。大雁,夜鶯,紅雀,銀鷗,她們是串聯草木、湖泊和天空的朋友,是森林的精靈,也是天空中飛翔的天使。倪老師早年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他所有的譯作都貫徹一個宗旨,“即追求自然與人的精神的sublime”。這sublime,是崇高,是超凡,是升華,是向上的飛升。顯然,沒有什麽比美麗的鳥兒更能寄托這種追求了。
3
如果從1947年倪慶餼翻譯發表希曼斯夫人的詩《春之呼聲》算起,他的翻譯生涯長達70年。那時的倪慶餼還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一名學生。倪老師多年後能翻譯英美那些大作家的作品,而且,對這個事情常年保持熱情,與他當年在聖約翰大學所受教育關係很大。在聖約翰的那幾年,倪慶餼接受了最好的英語教育,特別是古典英語熏陶多年。
倪老師的外語修養,不限於英語。他曾對我講,俄語,德語,他也能讀,日語,他也粗通,因為他上小學中學的時候,就被迫學了日語。這些,都為他日後的翻譯提供了條件。一些原著中涉及的俄語、日語方面的問題,他都能直接解決。
1949年大學畢業後,倪慶餼曾在北京呆過一段,在某對外文化交流部門短暫任職。後因患肺病而被迫離職回湖南老家養病。1953年,他到湖南師范學院任教,開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國文學。十餘年的教學與研究,讓他“打通”了歐洲文學史的“脈絡”,這對文學翻譯工作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他當時在教學之餘,也偶爾搞一些翻譯,但他自稱都是“零碎不成規模”。“文革”期間,倪慶餼轉到英文系教語法。
上世紀70年代末期,倪老師調到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80年代以後,開始了他大規模系統的翻譯。
他的翻譯,完全手工。第一遍用鉛筆或藍色原子筆初譯,寫出草稿,會寫得較亂,改得密密麻麻;然後謄清,對著原書,用紅筆再修改一遍;然後再用鋼筆謄清。如是,至少三遍。一部十幾萬字的書,相當於他要至少抄寫四五十萬字。這幾十摞文稿,總計近四百萬字,都是他一筆一劃,一字一句,一遍一遍地寫,謄,精心打磨出來的。
正常狀態下,第一遍初譯,倪老師平均每天能譯兩三千字。如果身體狀態好,其他各方面又沒有什麽牽扯,原作又不是很難,一部十五萬字的書,兩個月左右可以完成初稿。但多年以來,大多數時候,一部書的翻譯時間要更長一些。
不過,作為譯者,碰到赫德遜《鳥界探奇》這樣的書,仍然意味著一種挑戰。這些關於鳥的散文、遊記,內容廣涉自然,博物學、動物植物方面的專業名詞,對譯者也是陌生的領域。他一個老人,就跑圖書館,一個詞一個詞地查詞典,找各種工具書來解決。這些,都需要大量的時間。

他願意花這麽大的力氣來譯這些書,當年在我看來,實在有點兒不太理解,因為書的內容與我們實在有點兒遠,又不是我們以前的知識教育所關注,於我們的世俗謀生更是一點兒用處沒有。而這其中,又數赫德遜寫鳥的書,更讓我覺得沒用——我對鳥兒的直感,一是父母在我小時候經常給我講他們在1958年,參加“除四害”運動打麻雀,二是我上初中時,和朋友在郊外用汽槍也打過一隻麻雀。——想想,自己是多麽的庸俗和目光短淺。
但倪老師特別有熱情。這主要是因為,他真的是喜歡赫德遜的散文,喜歡赫德遜這些關於鳥的描述和審美。這應該是與他內心的某些方面十分契合。他在赫德遜的文字中,在邁納爾的文字中,在他們對鳥兒的生活的描述中,找到了一種不同於凡世的別樣的生活。那也許是他嚮往的。他一輩子在塵世中躲避,掙扎,沉默,小心翼翼,守著自己的一份善良與職業尊嚴。而在這些作品中,他能找到自由與美,在那漫長的翻譯工作中,他能感到自如與自信,在這種自如與自信中,他感到了力量。那些年,他曾不止一次,當面和我說起他翻譯這些書的不易,要查各種工具書,為了一個名詞,都要花費很多時間。但同時,我又能在他的訴苦中,感到他的一種滿足。他是在自討苦吃,但是,他在這苦中找到了只有他一個人享受的甜。他最開心的時候,就是他拿到新出版的書的那天。他在這辛勤的工作中,得到了莫大的樂趣。
倪老師傾注到譯作中的心血和功力,完全地體現在譯文、注釋和譯後記中。注釋,體現了譯者的水準和認真。譯作中,對原著涉及的外國人名、地名、事件,西方文化的背景等都作了注解,對理解譯文有相當幫助,注所當注,精到,簡潔,要言不繁。他所寫的序言或譯後記,本身就是一篇篇文藝隨筆,信息豐富,評論作家作品簡潔,中肯,有見地。讀者可以從赫德遜《鳥和人》《鳥界探奇》和邁納爾《我與飛鳥》的譯後記中,印證我的觀點。

雖然倪老師所翻譯的,都是自己所喜愛的作家的作品,但他並非對其一味讚美,對其得失,他有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他對盧卡斯的看法是:“他寫得太多,有時近於濫,文字推敲不夠,算不得文體家,但是當他寫得最好的時候,在英國現代散文史上佔有一席地位是毫無疑問的。”而對於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雲(原名拉甫卡迪沃·赫恩),譯者認為:“我並沒有得出結論說赫恩的作品都是精華,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這種情況,由於他標榜搜奇獵異,因此走向極端,談狐說鬼,信以為真,這樣我就根據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捨。”他對作家的評價,都是從整個文學史著眼,把每個作家定位,三言兩語,評價精當。比如他認為,史蒂文生“作為一個蘇格蘭人,他把英格蘭與蘇格蘭關係上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作為他的歷史小說的背景,在這方面,他的貢獻堪與司各特相提並論。奠定他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的,還有他的散文。他是英國散文的隨筆大師之一,英國文學的研究者公認他是英國文學最傑出的文體家之一”。他為每部作品寫的譯後記,都是一篇精辟的文學評論,概括全面,持論中正,揭示這個作家的最有價值的精華;語言簡潔、優美。譯者倪慶餼,不止是不為流俗所動的了不起的翻譯家,還是一位有見識的文學史家。
儘管倪老師在英國散文方面下的力氣最大,但他的視野並不止於散文。他還譯過小說,比如史蒂文生的《巴蘭特雷公子》。這個史蒂文生,就是寫過《金銀島》《誘拐》《化身博士》的那個史蒂文生。譯者好像特別喜歡這個作家,翻譯、出版了他的三本書。倪老師特別欣賞的作家,還有一個,就是赫德遜了。他前前後後翻譯了赫氏的三本散文,除了已經出版的《鳥和人》《鳥界探奇》,還有一本《倫敦的鳥》,譯出已有十幾年,至今尚未出版,原稿還一直在我手裡。這幾部書,都是赫氏關於鳥的散文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他也翻譯赫德遜的長篇小說《綠廈》。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由大明星奧黛麗·赫本主演,得過奧斯卡獎。他也譯過理論著作,柳無忌《中國文學新論》。雖以英國散文為主,但也旁及北美,如愛默生、傑克·邁納爾、華爾納等。他還寫過一些論文,如,《哈代威塞克斯小說集的悲劇性質》《王爾德·〈莎樂美〉·唯美主義》,還有研究翻譯史的論文。
他還譯過一些英詩,如彭斯,雪萊,濟慈,丁尼生的詩。柳無忌、張鏡潭編的《英國浪漫派詩選》,壓卷大軸,是大詩人濟慈的長篇名作《聖安妮節的前夜》,譯者也是倪慶餼。
4
倪老師在我讀研究生一年級時,教我們英語精讀。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第一個年頭。秋天,學校開學。那天,我們見到一位老者,步履緩慢,走進教室,走上講台。他的身材中等偏矮,穿著樸素,大概就是“的卡”布的中山裝;頭髮花白;他走路慢,右腿往前邁時,會先有輕微的一頓,好像句子中不小心多了一個逗號。那步履的節奏,多少年都是那樣,慢慢的,一步一頓。
當年上課的教室裡總好像空空蕩蕩。開始那陣子,我只是覺得這位老師講課有點兒特別。他說話輕聲慢語,帶著一點兒南方口音。特別的是,一個“公外”(公共外語教學部)的老師教公共英語,卻在課上不時地提起王國維、陳寅恪。他似乎對手上的課本並不十分在意,教這些東西,在他眼裡好像只是小技,並非學習英文的大道;而且,他經常眉頭微皺,在那種些許的漫不經心之中,他的眼神和眉宇之中仿佛還有一絲憂愁與傷感。
倪老師送我的第一本書,是《英國浪漫派詩選》,時間是1992年12月8日。扉頁上他寫的是:
給曉風
友情的紀念
偶爾也會寫:“曉風同學存念”,或者:“曉風君存念”,但“友情的紀念”寫得最多。落款,有時是他的名諱,有時則是“譯者”。——這些題簽,當時就讓我感到與眾不同。
倪老師說過好幾次,說我跟他認識這麽多年,卻沒有跟他翻譯什麽東西,遺憾。這於我當然是非常大的損失和遺憾,更是令我非常慚愧。但我也並非沒有收獲。比如,因為倪譯柳無忌《中國文學新論》的緣故,我不但有幸認識了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秦桂英,還認識了她的先生章安琪,他們夫婦也都是南開出身。章先生是研究繆靈珠的專家,當年當過人大中文系系主任。也因為倪老師,我認識了柳無忌,甚至採訪了柳先生。朱維之先生是當代中國研究希伯來文學的開創者,也是八九十年代全國高校最通用的《外國文學史》教材的主編。朱維之先生當過中文系系主任。但我認識他,卻是通過倪老師的介紹。和百花結緣,和倪老師關係也很大,我是通過倪老師認識了百花出版社的謝大光先生、張愛鄉等等。還有,我也是在倪老師家裡,第一次用真正的英文打字機練習打字。還有,更重要的是,我從他那裡獲得的文學知識和英文訓練,給我打開了英美文學的一扇大門。
我為倪老師,當然多少也做了一點事情,於我來說,值得驕傲。1993年春天,我到北圖,替倪老師把《普裡斯特利散文集》借出來,花了一個下午,翻閱、選目,然後複印。出版方面,賴出版社的諸多朋友鼎力相助,東方出版社出版的《綠廈》《愛默生日記精華》,雲南人民出版社的三本書,花城的《格拉斯米爾日記》《水滴的音樂》,還有河南大學出版社的兩本書,加上這次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再版的三本書,總共12本,是我幫著聯繫的。——這裡,我要替倪老師謝謝這些朋友,感謝你們為倪老師做的一切。——我拿到譯稿原稿,第一件事,就是到街上找最近的複印店,先把稿子複製一份再說,有時為了需要,要多聯繫一家出版社,就複製兩身份。總之,給出版社的盡量都是複印件,以確保手稿安全。因為稿子都是手寫稿,複印起來比較慢,往往要等兩個小時,或者更長時間。另外,倪老師的幾篇譯後記,也是經我手在《中華讀書報》發表的。
但這些,終究抵不消我心裡的愧疚。
有的時候,他因為頭一天打電話我沒接,第二天他就寫來一封信。——這就是讓我現在想來心裡就不安、難過的一件事。豈止是現在,就是當時,我心裡就滿懷愧疚。倪老師打來電話,有的時候固然是我當時不方便接,比如正在開會,或者正在開車;但也有的時候,是我心裡發狠,故意不接。我不接,當然也有我的理由。倪老師在電話裡,他說的內容,也都是出版書稿的事,其實大多都已經和他說清楚了。他和我一說,就停不下來,半小時,一小時地說——而我又不能很生硬地打斷他。即使如此,有時因為我手頭兒確實有事情,又只好生硬地打斷他。特別是大約2006年以後,他打電話,更不能控制。——後來,我靜下心來想,明白這是因為老人寂寞,想讓我陪他說說話而已。而我呢,在心裡確實是有點兒不耐煩。同樣,我回天津,回南開也比較多,大概回去三次,中間才去看他一次,而且,往往都是臨去之前半小時打電話——因為知道他反正都在家,所以就先到其他地方辦更重要的事,有了空檔兒,才聯繫他。——我這點兒小心眼兒,他當然根本不知道,也就無從介意,只要我來了,他都高興得不得了,拉著我說個沒完。——想想,其實我可以多陪他聊幾次天的。
還有一些瑣事,點點滴滴,難以在這麽短的文章裡盡述。他經常批評我的,就是我沒有一個研究的主攻方向,他總希望我能多寫一些專業研究的文章。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安排我和幾位同事十月底去歐洲訪問,先到英國,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九月初,我去看倪老師,和他說起來要去英國,他非常高興,一臉羨慕,說他一輩子翻譯英國散文,卻沒有出過國,更沒有去過英國,真是遺憾。讓我去了,替他好好看看,回來跟他講。
倪老師愛書如命,有時也天真得像個小孩兒。他願意借書給我看,但總是記得哪本書,過一段時間會問我看了沒有,看過了就要還他。有一次,他為了讓我還一本書,專門和我一起到我宿舍找,居然就從我的書櫃裡把那本書找了出來。——他那身份得意勁兒,甭提了,一臉高興,拿著他的寶貝書,得勝還朝了。
多年以後,我回西南村看他,他把托人從加拿大買的兩本英文原版書,赫德遜的Birds and Man 和Birds in London送給了我,這就是《鳥和人》和《倫敦的鳥》。
5
去年,也就是2018年5月9日,我最後一次在天津總醫院見到倪老師。他躺在病床上,已經不大認得我了。這次我是陪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兩位同志,社長劉國輝和責編李默耘,專程到天津見倪老師,為這幾本書的出版簽合約。是他女婿代簽的,倪老師已經無法和人正常交談了。但是說到赫德遜的《鳥和人》《鳥界探奇》,他眼裡還是有了光,有點兒興奮。聽說再版的書會配插圖,他更高興,呢喃著說,赫德遜的這兩本書都是名著,一定把圖配好。
我們回到北京後,不到一個月,6月2日,倪老師就走了。
倪老師1928年生,湖南長沙人,他有兩個常用的筆名“孟修”“林荇”。倪老師沒有什麽嗜好,煙酒一概不沾,也不愛喝茶;棋牌也不摸,他覺得那些都很無聊。他工作是翻譯,愛好也是翻譯;休息就是看書,看林語堂、錢鍾書;他喜歡穆旦,推崇傅雷、馮至。他的運動就是一步一頓地去圖書館。可是後來老了,圖書館也去不了了。
幾年前,我去看他,那時他的頭腦還比較清醒,還有正常的思考能力。聊天中,自然又說到他不久前在花城出版的《格拉斯米爾日記》,我很為他高興。不料,他卻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再翻譯了。這些都沒有什麽意義。”

是啊,與生命本身相比,我們所做的這些文字工作,究竟有什麽意義呢?
倪老師一生也沒有發達過,晚年則更加潦倒。因為醉心於翻譯,他在世俗的名利方面幾乎無所得。晚近幾年,家裡又連遭變故,對他更是沉重打擊。在南開園中,他就是一名普通的英文教師,幾乎沒有人知道有這麽一個大翻譯家是自己的鄰居。2015年春節之後,大學裡假期尚未結束,我專程去南開一趟,找到校黨委副書記劉景泉。我把有關倪老師的一些材料帶給他看,說,南開真的應該認真宣傳一下倪老師,他堪稱是中國翻譯界的勞模,也是南開的門面。劉書記真不錯,很快布置給校報。這年5月15日《南開大學報》就登出一篇長篇報導,韋承金先生寫的《譯壇“隱者”的默默耕耘》。——謝謝劉先生和韋先生。
倪老師的翻譯,其實與別人無關,我甚至認為,與什麽文學理想、翻譯理想也沒有多大關係。他就是喜歡翻譯,喜歡文學,喜歡優美的文字,嚮往遼闊清靜的大自然,喜歡清新自然,喜歡趣味高雅的精神生活。他是為自己翻譯,翻譯了一輩子。他以翻譯,建立一個豐富的內心世界,也成就了自我。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後人的讚譽也好,不認同也罷,都與他無關。但是,這些作品,畢竟留在了這世上,以漢語的形式,在東方世界裡傳播,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實。這個事實,將會對一些人的思想,發生一些作用。包括對純正文學經典的欣賞,對那些作家優雅寫作的傳達,還有,告訴我們,世界上除了追逐名利權色,還有一種淡泊超脫的人生追求,那很可能是一種更美好、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而純正、優雅和淡泊、超脫,也正是倪老師的精神品質。
這個“餼”字,讀xì,和“戲”字同音,《辭海》上解釋這個字有三個意思,一是“糧食或飼料”;二是“贈送”;三是“活的牲口”。《論語》裡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倪老師翻譯了幾十種名著,收獲的是清貧。清貧就是上天給他的回報。老實說,我到現在也並不理解倪老師。我大概只能說,他在現實中受壓,卻從赫德遜、小泉八雲、史蒂文生的書裡找到慰藉,獲得力量和滿足。從這一方面說,他離開這個濁世,也未嘗不是一種解脫。我們這些人,每天瞎忙,戴著漂亮而僵硬的面具,在滾滾紅塵中耗費生命,卻找不到生命的價值。相比之下,倪老師一生做自己熱愛的文學翻譯,倒是幸福的。
今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將再版倪老師的三部譯作。這是他最喜歡的三本書。這三本,都是關於鳥兒的書,配上了精美的插圖,真的很漂亮,仿佛鳥兒張開了翅膀。——讓鳥兒帶他去天堂吧。
(《鳥界探奇》,《鳥和人》,[英]威廉·亨利·赫德遜著,《傑克·邁納爾與飛鳥》,[加]傑克·邁納爾著,三書均為倪慶餼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