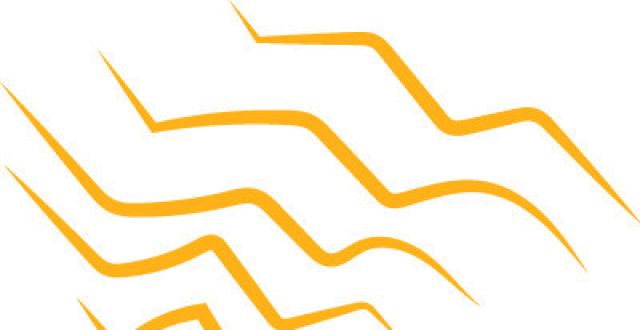面對死亡,我們能怎麽辦?荒木經惟此次在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的展覽正要給我們答案。

答案就隱藏在展覽的名稱之中——花幽。中文“幽”常常用來代指陰間,與鬼神有關。“花幽”就顯得很矛盾,一場生命力十分旺盛的展覽,卻是在探討死亡。年老的荒木經惟好像在問我們:“我們死之後,會去哪裡?”
日本真是一個充滿了“妖魔鬼怪”的民族,這一點可以從被稱為“日本民俗學之父”的柳田國男的作品中看到。他的文集已經在中國翻譯出版。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宮崎駿進入自己的創作室,都要先敲敲門,就是在表示對那些看不見的“靈”的敬意,意思在說:“不好意思打擾了。”

春天開放的花,是多麽美好啊,誰又能不愛呢。然而日本卻有一種獨特的審美存在。就像川端康成說的,“在日語裡,‘悲哀’一詞是與‘美’相通的。”因此日本民族中看似有一種矛盾性,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概括流行於全世界:菊花與劍(一個更為知名的翻譯是:菊與刀)。本尼迪克特說,這個民族平時是很溫和的,但是特定的時候,又敢於切腹,非常暴烈,兩者統一為一種民族精神。儘管本尼迪克特沒有到過日本做實地的田野調查,她的著作還是影響了世界對日本的認識。就像日本的櫻花一樣,那麽絢爛地盛放,然而轉瞬間就從枝頭飛下,落入塵泥碾作灰。

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在欣賞美麗的時候,難免會想到死亡,不是很掃興的嗎?為什麽我們就不能好好欣賞美麗的事物,為什麽一定要在美麗面前提到物是人非呢?但美麗總是會消失的啊。無論是美人的如花面龐,還是男人強健的體魄,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不再。這是事實,又怎能視而不見?

面對這樣的人生困局,我們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接受,一種是對抗。荒木經惟走的是第三條道路,他希望能夠從生的角度理解死亡。
當陽子——他一生摯愛——去世的時候,荒木經惟難免想到自己的命運也會是如此吧?而一個很不尋常的創作衝動出現了,他開始拍攝花朵。

一個人對死亡有確切的概念,是從至親離世開始的。而正是從陽子離世的那個時候,荒木經惟開始拍攝花,花是生命和死亡的統一體,但更多是生的意象。

此次展覽有一個單元名為“花靈”,是一組讓人覺得有點“邪惡”的作品。就像是一個個宗教祭禮現場,那些看起來並不好看也不完整的玩偶,和一些花結合在一起。每張照片上都題寫著中文詩詞,看展覽的人都會說,荒木的書法也是不錯的啊。荒木終究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藝術家,他總是把自己的喜好暴露在觀眾面前,“花靈”準確傳達了荒木經惟對於生活世界的超越,而進入了一種非常主觀和神秘的領域。

對於有的人來說,只要想到身處的世界的邊界,就有點瑟瑟發抖了。但是荒木經惟似乎已經直面未知,並得到了讓自己心滿意足的答案。就好像牛頓的故事一樣,一個發現了三大定律的偉大科學家,卻在生命的最後去探討什麽第一推動力的問題,終於他搬出了上帝——對唯物主義者來說,這無異於科學家牛頓的生命敗筆;但至少承認自己的局限,認識到人類的無知和渺小,並沒有阻撓科學探索的腳步。
如果沒有看到荒木經惟所說的“靈”,在展覽現場看到“美”也就夠了——花是美的,生命也是好的,趁著年華,好好享受吧。

展覽中有一組作品,荒木給枯萎的花塗上了鮮豔的顏料——多麽悲壯的舉動啊。死亡,原來也可以盛裝打扮。在萬物更生的季節,這樣一場展覽本身就是個帶有寓意的事情。它模擬了萬千花的姿態,它既生又死,所以才是永恆的。

有一幅作品中,在一朵枯萎的瓶中花後面,荒木經惟的貓奇洛“嗖”地穿了過去,在畫面中,僅僅留下它一個虛晃的身影。泰戈爾說:天空未留痕跡,鳥兒卻早已飛過。萬事都隨流水,攝影,就留下了這個痕跡。那幅畫裡的兩個活物都死了,奇洛死了,花也死了,但它們的“靈”留在了畫面中。

供圖|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
文|劉婷
本文刊載於北京青年報2019年5月24日C6版《青畫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