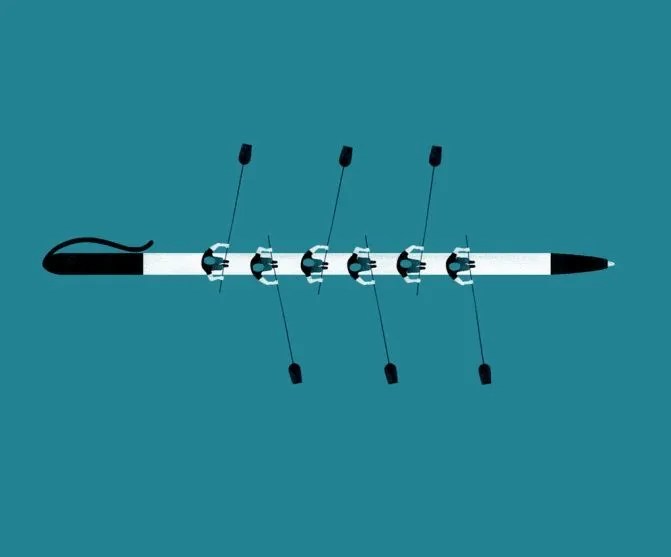教師的職業尊嚴到哪兒去了?
文|張聰
教師,是一個能獲得社會尊重的職業嗎?
起碼在唐代不是這樣的。唐代有個叫呂溫的家夥,在給族兄的一封信裡寫到,說魏晉以後,世風大壞,“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為鄙,公卿大夫,恥為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見《呂衡州集》卷三)——如果有誰在街上當眾喊人一聲“老師”,那人立時就要氣衝衝地回答:“你才老師,你全家都老師!”——教師的職業尊嚴簡直被碾壓成了碎片。“嗚呼!師道之不複可知矣!”
無獨有偶,到了17世紀一個叫蒙田的洋人,也寫了一篇文章記述當時教師職業尊嚴的淪喪——
“我小時候常常生氣,看見意大利的喜劇老是把學究或教師作為笑柄,而“夫子”這稱呼在我們當中也不見得被看重得很多。
“因為既然被交托給他們指導,我怎能不愛惜他們的榮譽呢?我曾試為解釋,以為這完全是由於一般俗人和那少數見識超卓的學者之間的自然分界,……但莫名其面的是,我發覺那些最看不起他們的,就是那些最賢智的人……”(梁宗岱譯《蒙田試筆·論教育》)”

教師的地位在今天又是怎樣的呢?是否比四百年前略好一些?
各位賢智的的讀者,如果告訴你,某人——譬如我吧——是一位小學老師,你對他會產生哪些先入為主的認識呢?你是否會下意識地認為這個人是一個高尚的人、自律的人、富有愛心的人、值得托付的人?還是會覺得,他不過僅僅是佔據“教師”這個職位的家夥罷了,完全談不到有什麽學識和專長,只是因為經常乾預兒童的成長過程所以積累了一些處理類似問題的經驗而已?或者像蒙田文章裡所說的那樣,認為雖然這些老師裝了一肚子“道理”且把這些“道理”日複一日地灌輸給孩子們,但他們自己的事業卻談不上成功。自己沒有活出名堂來,卻可以居高臨下地指點別人成功的路線,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情嗎?
如果不幸,你還能回憶起童年時被老師當眾厲聲呵斥的場景,或者關注過媒體上關於師德問題的報導,那你對教師的惡感恐怕就又增加了一分。
教師——這群以“靈魂工程師”自詡的人,這群據說可以與“天地君親”並列的人,怎麽會做倒了行市,淪落到這步田地?

我們且回到呂溫的文章中,聽聽他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吧——呂溫在他的《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裡,劈頭就說: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資道喪,八百年矣。”
這裡的“嚴”,並不是嚴格的意思,而是“尊敬”的意思(俞理初《嚴父母義》:“誤以古言嚴父為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找到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師是不容易的。
今天公立學校的孩子們更談不到有“找”的權利了,只能“遇”,或者用土話說,是“撞”,撞見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師,當然,更不容易。
接著,呂溫深情地回想起漢朝“師道尊嚴”的場景——
“夫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終身。
夫教者,豈徒博文字而已,蓋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禮義,敦之以信讓,激之以廉恥,過則匡之,失則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無瑕。”
沒有人僅僅是為了求得知識而來學習的,他們把“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的成長作為自己求學的目標。而教育者也不甘於僅僅傳授文字章句,他們自己就是虔誠的信仰者和積極的踐行者,所以他們有權利(不是有權威)敦促、教育他們的學生也成為真理的追求者,並在這個過程中教學相長,彼此成就。
而今天(唐朝)呢,由於社會風氣的熏染,教師已經失去了這種人格上的影響力,不再把育人作為自己的使命;學生也絕少高遠的人生目標,甘於做一個小時代裡的“成功者”——“至於聖賢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倫之紀律,王道之根源,則蕩然莫知所措矣。”

我們回想《進學解》裡太學學生對老師韓愈的質問——你憑什麽以真理的擁有者自居?你憑什麽告訴我應該怎麽生活?(如果是現在的學生,還可以加一句:“你僅僅是個服務者!”——我至今都不能理解,教育行業怎麽能成為服務行業。一個老師怎麽一面保持著服務的姿態一面進行教育。)你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吧,“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別巴巴地教育我了!
韓愈臉皮厚實,居然侃侃而談回答了這個學生的質問。如果我處在韓愈的位置上,會轉身就走,絕不多撂一句話——不是因為憤怒,而是因為無語。三觀差異,不是靠語言能夠解決的。
可我們的教育體制,恰恰把懷著完全不同的人生信念的人們——教師、學生、家長——強行聚攏在一起,賦予他們“師生”的名號,生不必敬師,師不必敬弟子,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升學與應試,為了那個可把握的、具體的又虛幻的幸福。
日本學者佐藤學在他的《課程與教師》裡說:
“今日教師的存在論危機,可以說,產生於從根基上支撐教職這一工作的“公共使命”的喪失。一旦喪失了教育的公共使命這一大支柱,(教師職業的)“回歸性”(即反思性實踐)特徵,會使得課堂這一公共太空封閉為教師的主觀性私人太空;(教學實踐的)“不確定性”這一的特徵將助長學校的官僚主義、管理主義、形式主義,把教職工作轉化為人人都能從事的非專業化工作;“無邊界性”這一特徵將瓦解教師職業的專業性,把教師的職業生活變換為繁瑣事務的堆積。
教師這一職業由於是以公共使命為中心,所以主張它的存在並且實踐它。但是在日本近代學校確立以來,再沒有像今日這樣,教師的公共使命處於不透明的時代。儘管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如此滲透著教育;儘管通過教育應當拯救的兒童不幸的現實如此地擴大,但在教育服務以市場原理為基礎流通、人們對於教育的意識被私事化的現在,教育的公共使命已經蛻變到比任何時代都難以彰顯的地步了。
今日的教師(看上去強勢的)權威與權力,與其說是作為過剩的公共使命的結果,不如說是公共使命衰退而派生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學校教育中也可以發現。今天的教師不是以“成為不了國家棟梁”之類的語言來威脅、壓抑兒童,當然,也不是相反的語言——“不能作為自立的、民主的主體參與社會”之類的語言來威脅、壓抑兒童。在表達這種公共使命的語言的權威和權力喪失的狀態下,“不要被殘酷的競爭所淘汰”“不要斷送了你的前途”之類的有關私人性、個人性事件的威脅語句。(為保持語義的完整,括號中的文字皆為筆者所加)”
回看我們公立學校建設的初衷——曾經就是作為國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承擔教育公民(人民)的“公共使命”而構建的。教師,是被遴選出來,作為國家體系的神經末梢傳遞國家意志的人。整個體制都是圍繞著這個目的運轉的,在這方面,我們的體制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說是高效的。
但,社會已經發生了變化。我清楚地記得自己小的時候,“教師”,在人們的觀念中是一個多麽具有權威的職業,家長、學生對老師的尊敬,不僅僅是因為她能左右一個人未來發展的路線,還因為……還因為什麽呢?還因為她的一顰一笑都那麽與眾不同。
今天還會有家長用這樣的眼神看我嗎?應該說還是有,但他們的眼神中更多的是焦慮與疑惑。每個人都是孤島,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生活奮鬥,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所以,每個人都會形成自己的教育訴求,這是必然的事情。人們無暇為整個人生做考量,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很多家長急於尋求一種可以兌現的技能。市場經濟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教育,在不少人看來不過是一種可以購買的服務而已。既然是服務,整個教育都應該是以我為中心的、為我的(卻不知教育恰恰是為了改變你而存在的)。教師,不過是掌握一種“專業技能”的人,他們出售自己的勞動,換取相應的報酬……當我們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下審視教師職業的時候,你會發現,教師,並不需要提供什麽複雜勞動,他們要傳授的知識如此簡單,他們要處理的問題如此輕忽,以至於他們的準入門檻是這樣的低,他們的收入是如此少——這和一個車間裡的計件工人到底有什麽不同呢?我們有必要給予教師額外的敬意嗎?
這不是一些家長的認識,是整個社會的誤解——今天,教育問題的層出不窮,恰恰是由於公共使命的式微,我們的社會把“教師”僅僅看作是一份職業!
教師絕不僅僅是一份“職業”,或者說,這份職業特殊到絕不能把它僅僅看作一份“職業”。能否做好一份職業,卻決於你是否具有良好的技術和相關的能力;而能否成為好老師,卻取決於(幾乎可以說隻取決於)你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謂予不信,不妨舉個例子——現行的教師職稱評定方式集中考察教師的四個方面:你做過哪些公開課?你寫過哪些論文並獲獎?你主持或參與過哪些課題?你獲得過哪些榮譽?——這四方面或許可以很好地考察出一個人所具有的“專業成就”,但我們能不能說在這四方面做得好的老師就是一個“好老師”?當然不能!內爾·諾丁斯在《學會關心》裡說:
“當我和我丈夫讀高中的時候,我知道我們的老師關心我們。實際上我們的很多老師並不精通他所教的科目,但是他們了解我們,與我們交談,鼓勵我們。我們學習負擔也不是很重。一旦暑假來臨,我就精神不振,因為我不願意離開學校那麽長時間。學校已經成為了我的第二個家了。”
這些專業技能並不夠出色的老師竟可以給孩子留下如此積極的影響,更不要說那些有信仰、有思想、有愛心,給予孩子一生深刻影響的老師了。用“職業”來定義他們的工作,用“職稱”來評價他們的工作,幾乎是一種褻瀆。

既然我們不能把“教師”僅僅看作一些“職業人”,那今天我們該用什麽標準遴選、評定他們呢?在公共使命式微的今天,我們改如何重拾教師的尊嚴呢?
恐怕要從幾方面著手——
首先,我們要給予學生“擇師”的權利,以“敬-愛”為基石,重構現代的師生關係——學生既然是教師“服務”的對象,就應該是最有權利評價教師的人。他們只有與自己真正敬仰的教師在一起,才能接受到真正有效的教育;而不合格的老師將在這一過程中被自然淘汰。
同時,我們的學校和教師要有精神上的擔當。一面要提供有差異的、多樣化的、可選擇的教育路徑,一面又在多樣化路徑的背後,給予學生的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品質,肩起“為社會立心”的作用——也就是教師所要承擔的“公共使命”。教師不僅要成為這種公共使命的宣講者,也要成為這種公共使命的信奉者與踐行者。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裡講了一個故事:
“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鹹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希望今天的師者也有孫昌胤式的勇氣,活出自己的尊嚴來!

【作者介紹】
張聰,小學教師。
特別鳴謝
書院中國文化發展基金會
敦和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