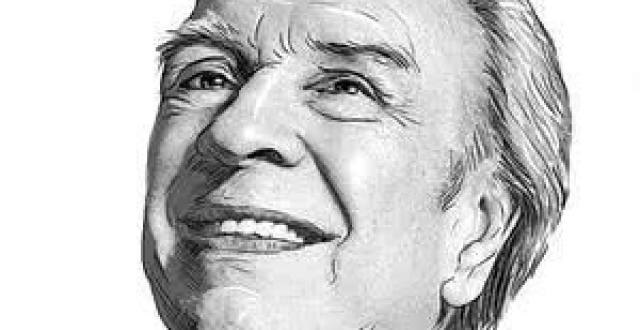寫信人:吳琦
單讀主編
我站在鋪天蓋地的塵埃中
柏琳,你好
話到紙上,頓時就客氣了起來。倒是不怕客氣,就怕許多對話最後只剩下客氣。想到和你認識以來,一直在團結緊張嚴肅認真的氣氛中交流問題,所以這種客氣也是真實的,在嬉笑怒罵的語言環境中,幫我們保持了嚴肅性。最近北京雨水連綿,情緒粘稠如同南方,紙筆之間尚存一點清爽的距離,是一樁好事情。
你是仗義執言之人,又愛強身健體,身上那股元氣常常令我汗顏。隔著電子看板,看到你對時下媒體風氣有嚴厲的批評,我叫好之前都會懷疑,自己仍然身處其中,大概沒有什麽資格附和;又是隔著螢幕,和你討論閱讀和寫作,你總是更加激動,那種厭惡和歡喜幾乎來自本能,勝過我緩慢猶豫的考慮,想來我還是不如你那般熱愛文學;回信一直拖延,鍛煉的計劃也無力趕上,等到約你寫的文章終於發表,竟然還在前言中錯把你去的聖彼得堡寫成了莫斯科……大事小事上都落後了,這恐怕是在你面前客氣的另一個原因。

近幾年我的生活趨於穩定,而朋友們依然在各辟蹊徑,其中就包括你,辭職、學法語、練拳擊、考駕照、四處旅行,每一項都被我引為參照,那感覺已經不是羨慕,而像讀到了另一個人生劇本,更直接、真實、有生命力的一個,像你說的,“用文學來愛”,或者用我的話,用文學披荊斬棘。當然這都是隔岸之言,旁人無法體會在這表面的自由中,是怎樣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的歷程。
我們專業不同,工作領域也不完全一樣。很長一段時間,可能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都認為如果文學有個圈,那麽你在裡面而我在外面。我在外面,看到許多作家陷入一種自說自話的窘境,除了獲得親近者的吹捧,不能在讀者那裡獲得共鳴,你在裡面,發現了文學的無力感,高高築起的幻覺正在塌方,和生活本身隔絕得太遠。我們裡應外合交換了意見,最終都避開了這個圈子,繞道而行。
今天我們依然在談論它,大概都是還沒死心?畢竟文學中寄托了太多美好的品質,至今也值得相信。它不該是一種標榜,不證自明的標簽,一勞永逸就能獲得的頭銜,不該是一個乾涸的系統,頑固地保守著一些空洞的誓言。如果說在這穩定的生活中我還有什麽期待,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稍微擴充文學的邊界,甚至讓渡它的價值,讓我們時代那些被宣判為業餘、草根、無關的,卻深深擊中人心的文本,也去往開闊的文學峽谷。

而你從未停止的閱讀和寫作,常帶著一種深刻的逼問,逼得那些沉默的書和作者交出他們的沉默,說出他們未能全部寫出但諳熟於心的話,那是文學的腹地,是最必要的袒露,也是捍衛。
我當然同意你說的“強壯的悲觀”,不過我猜一定有人又會嫌棄這個詞不夠文學,那麽讓我換到你提到的“愛”,我喜歡的批評家張定浩也最常談論這個概念——哈哈,這總十分文學了吧?
在新書裡,張定浩說“文學能力”是一種“類似於愛的積極關係”,這就是一個非常強壯的比喻,正是這種能力帶領文學——或者文學帶領我們,衝進世界裡去。衝進去然後怎麽辦呢?他又援引濟慈一個看似悲觀的詞“消極感受力”,意思是在審美中,不僅要面對確鑿的事,還要“有能力經歷不安、迷惘和疑惑”,這些脆弱的時刻我們仍然可以依靠著文學。在這之中我能看見一個好大的世界,具體的字句鋪成了路,而大路朝天,路上多少古往今來的同道中人,如此文學才能向前,去處理歷史、道德、共同的人類經驗。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分享對同一類作家的喜愛,紀德、加繆、特裡林、漢德克、伯林……包括你在南斯拉夫行記中提到的物理天才特斯拉,我抄下你抄下的他的句子,“在這樣一個時代,超乎想象的科技發展,並不會導向真正的文化新生和新啟蒙。恰恰相反,如今國家衰落的真正原因,在於人類對社會、道德和精神危機的無能為力。”

“寫作也是為了被愛,被遙遠的人所愛。”這也是張定浩抄下的羅蘭·巴特的句子。怎麽去形容這些閱讀的經驗呢,只能說那就是相愛的感覺。
在“愛”的過程裡,最有迷惑性的概念也許就是“我”。我當然理解,文學發展到今天,自我已經成了最基本的敘事單元,最合法的動機,甚至在整個文化的領域,自我都是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時代精神的載體。但就如同“文學”一樣,“自我”也不是一個先驗的概念,如果僅僅通過它來抒發、宣泄,那麽顯然低估了它之於文學的意義。“自我”更應該是考驗,關於一個人的得到與失去,以及那些得到與失去在世界當中的位置。未經召喚、未經拷問的自我,根本不值得寫。
更何況,談論自我不是通向自我的唯一方式,而只是其中更方便、更流行的那一種,因為這種方法也被這個時代如陰謀一般地鼓勵著。
就像我們寫“公開信”,並不是為了展示自己,而是借由這種自我分析,尋找寫作的對象感,試驗溝通的有效性,更樂觀一點,為可能的共同體做準備。正好在這裡懇請其他對這個計劃有興趣的朋友,不要再專門給我個人寫信,而應該給你們的朋友,給單讀的作者們,給那些與你們遙遠地對視的人寫——他們那裡說不定幫你保存著更珍貴的自己。

近來的感受是,古典時代就形成的許多美德、藝術、學問和身體,經過現代後現代的洗禮,到今天反而分崩離析。而如果我們還要踏上尋找自我的旅程,不如就讓愛、勞動、語言、實踐這些從我們身上被拆解被分離的部分,重新匯合,組成我們的身體和靈魂,與所有人不同又與他們一樣。
看到你提到赫拉巴爾,我又一驚,因為這位作家時不時也會跑進我的腦子裡。我們如今不就像他一樣,守著一座巨大的廢紙回收站,眼睜睜地看著那些冰冷、堅硬、機械的成見、系統、權力,把所有反抗和變化碾碎?
真不幸,你從貝爾格萊德特意挑選的明信片果然還是寄丟了,但新寫的塞爾維亞的文章如期收到。大概這就是和文學相愛的人必經的命運。我們隨時準備失去那些即將失去的東西,同時總會得到意料之中的驚喜。
“我站在鋪天蓋地的塵埃中,傾聽著爆炸的樂曲,心裡想著我在深深的地下室裡的工作,那裡有一台壓力機,我在它的旁邊,在幾盞電燈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聽得見上面院子裡來往行人的腳步聲……”你看,這是赫拉巴爾寄給我們的信。
此致
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