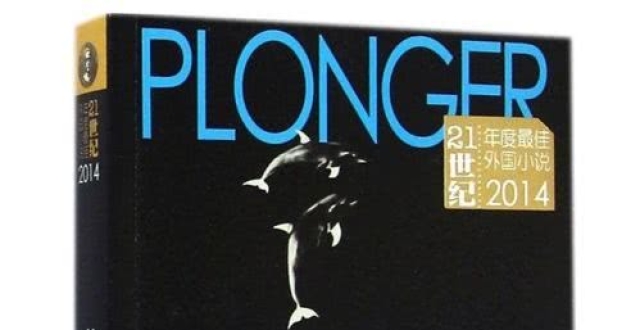1922年12月3日,魯迅在為自己的首部小說集《呐喊》所作的序言中講述了他進行文學創作的緣由,也就是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的一次眾所周知的經歷,他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一年後,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作了《娜拉走後怎樣》的著名演講,指出“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看客”可以說是魯迅作品中最為經典的形象塑造。錢理群曾說,凡讀過魯迅小說的人,大概都很難忘記那篇獨一無二的《示眾》,“沒有情節故事,沒有人物性格,沒有風光描寫,沒有主觀抒情,沒有推理論證,只有一個場面”,那就是“看與被看”,但它卻凝聚著魯迅對中國“人”的生存方式、人際關係及人生價值等方面“最深刻的觀察與把握”。在錢理群看來,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與《故事新編》中的許多小說都看作是《示眾》的“生發與展開”。(錢理群、王得後:《近年來魯迅小說研究的新趨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1年第3期)
作為經典文學形象的“看客”已然深入人心,並對魯迅同時代及其以後的許多中國作家的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有關“看客”形象的文學分析及其研究也數不勝數,但“看客”們在現實世界中究竟呈現為何種形象,何以令魯迅如此深惡痛絕,卻少有論述。這恐怕是因為現實世界中“看客”們的“看”無處不在,以至於很少有人會意識到“看”也是一個問題。不過,有一種現象例外,那就是“大出喪”,因為它似乎天生就是為了讓人“看”的。喪家一方面為了表現自己作為孝子賢孫的一片孝心,另一方面為了彰顯家族的權勢地位,各種儀仗花樣百出,從而成就了“看客”們的一場場盛宴。尤為關鍵的是,當時的新聞報刊對於“大出喪”也頗感興趣,常常事無巨細地進行報導,因而留下了大量此類“看與被看”的資料,使得我們能夠在魯迅的文學文本之外,一睹民國“看客”們的歷史形象。

魯迅及《呐喊》書封
“大出喪”中的“看客”
出喪,又稱出殯,在整個殯葬儀式中,以其活動空間的公共性而備受矚目,是喪禮中場面最壯觀、耗資也最大的環節。民國時期的報刊媒體上常常使用“大出喪”一詞,來突顯當時出喪儀式的規模宏大和引人關注。提起民國時期的大出喪,不能不首先提到上海,而提到上海的大出喪,盛宣懷大出喪又不能不提。在當時的報刊媒體中,“滬人所最喜觀者,莫如大出喪”(自由談,《申報》1919年2月17日),在整個民國時期一直被上海人津津樂道,並不斷拿來與此後的大出喪進行比較的,也正是盛宣懷大出喪。
盛宣懷的出喪日期是1917年11月18日,早在10月25日便由上海總商會總董朱葆三、副董沈聯芳聯名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請求發給出殯路由執照。所謂路由,是指出殯時的經行路線。如果出殯從租界經過,那麽路由就須得到租界當局的批準,發給執照。這種做法在清末已經實施,違者要受到處罰。久而久之,成為慣例。一些富貴人家還會預先將出殯路由,同訃告一起登報廣告,俾眾周知。因為工部局“向不允許”出殯行經南京路與黃埔灘,所以出殯時若能經過南京路和黃埔灘,就成為一種特殊的榮耀,能夠彰顯死者與眾不同的地位。按《申報》的說法,盛宣懷之父盛康在1902年出殯時,“費五萬元,以曾經過英大馬路為特殊之榮”。(《申報》1922年4月23日)盛宣懷的出殯路由於1917年11月8日在《申報》上刊登,相當於提前通知“看客”們到指定位置靜待“好戲開場”。
“看客”們的熱情被充分調動起來了。據《申報》報導,“四馬路一帶各大菜館、酒樓洋台座位已預定一空,各茶肆更特別買票,每位取洋一元或五角不等”。對於大出喪的盛況,《申報》也有詳盡報導:
昨為盛杏孫出殯之期,所有經過各馬路,無不人山人海。四馬路一帶更無容足之地,兩旁店鋪大都暫停營業,布置坐位,或則供給親友,或則收費賣座。且有人在馬路兩邊搭台設椅,收取看資,每位亦取洋六角。是以繡雲天、升平樓、長樂等處,擁擠不堪,鹹無隙地。而在馬路中觀看者,更如潮湧。外灘各洋房,屋脊之上,亦只見人頭亂擠,實為從來所未有。(《盛杏孫出殯之盛況:應有無不有,不應有亦有》,《申報》1917年11月19日)
盛宣懷大出喪也並非上海一地的盛事,其影響異塵餘生到了上海周邊眾多市鎮。早在出殯前,《申報》便報導:“外方來滬觀看者亦甚多,連日火車、輪船均極擁擠,各旅館生涯頗盛。”(《哄動遠近之大出喪》,《申報》1917年11月18日);出殯後,又報導:“昨日午前後,該兩路火車搭客亦甚多,大半為觀看出殯而返者。如滬寧路之蘇錫昆山南翔等處,及滬杭路之嘉興、警善、楓涇、松江等處搭客,每次開車均擠軋不堪,甚至有人搭於獸車之內,亦所不惜。而開往各埠之小輪船,亦無不利市三倍。”(《盛杏孫出喪之勞民傷財》,《申報》1917年11月20日)大量外埠人士湧進上海,對於上海商家而言,是個巨大商機,而借著盛宣懷大出喪大作廣告的商家亦不乏其人,如戲院的廣告:
今日大馬路、四馬路擁擠不堪,外埠的人趁著輪船火車趕到上海來,無非是看盛公館出喪。諸君日間看了出喪,夜間用何法消遣咧?當以到笑舞台看好戲為第一。看出喪是悲的,看戲是喜的;看出喪是動的,看戲是靜的。有悲有喜,有動有靜,才與精神有益,身體有益,所以今夜到笑舞台看戲,不獨娛樂,且很合衛生之道。(《日裡看盛公館出喪,夜裡看笑舞台好戲》,《申報》1917年11月18日)
廣告刊登在大出喪當日的《申報》上,目標客戶相當清楚,就是前來上海觀看大出喪的外埠人士。
由於觀者甚眾,以致事故頻發:
惟聞當擁擠之時,四馬路望平街口有年二十餘歲之懷孕少婦,被擠倒地,不省人事,由其夫大聲呼救後,見數人扛起向東而去。匯芳門首有一五六歲之小孩,竟被眾擠死。新世界左近軋倒浦東鄉老二人、小孩一人,後經旁人呼救始得出險。至於呼妻覓子、尋哥叫弟,以及失落鞋帽者,不可計數。法界新開河太古碼頭上有衣服華麗之中年婦兩人,被眾擠落碼頭底下,後經旁人救起,滿身泥汙。在三點數分,時哭聲大起於江邊者即此地。(《盛杏孫出殯之盛況:應有無不有,不應有亦有》,《申報》1917年11月19日)
除了大出喪當日的報導外,《申報》等此後又連續報導了盛宣懷大出喪時的各種事故:
住居滬城唐家弄之某甲,向在北市某保險行執業,家有二女,年均及笄。舊歷十月初四日下午,由女傭伴同出外,至金利源碼頭觀看盛杏孫出喪,因人多擠軋,致將兩女及女傭擠落浦中,當時由各杉板船將甲之長女及女傭立時救起,其次女則迄未撈獲。前昨等日,甲已自懸重賞,分投知照各幫船戶,留心打撈,不知屍身將於何日出現己也。(《盛杏孫出喪之害人》,《申報》1917年11月23日)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眾多的事故還都是在租界巡捕全班人馬都出動維持秩序的情況下發生的,於此可見盛宣懷大出喪所造成的上海全城如癡如醉觀出喪的景象究竟有多瘋狂!
這一盛況並非盛宣懷大出喪特有,而是大出喪的普遍現象。1922年4月,當時報刊上被稱為“江西首富”的周扶九父子大出喪轟動一時,也是“經過之處,人山人海,各店鋪洋台無不滿坐來賓,茶樓酒館亦臨時賣座”。章太炎當日前赴職工教育館講學,中途為行人阻塞以致遲到半小時,記錄者稱“大約為周扶九父子之大出喪所阻,可見無謂之大出喪不但勞民傷財且妨講學”。(《申報》1922年4月23日)
熱衷於觀看“大出喪”者也並非上海一地的民眾。1919年9月6日,浙江督軍楊善德大出喪,“前昨兩日遠近吊客及來觀大出喪者,火車站擁擠不開,省城驟增二萬餘人,旅館漲價數倍”。(《楊故督出殯紀》,《申報》1919年9月7日)一年後,江蘇督軍李純在南京的大出喪亦不遑多讓。“李故督出殯,由督署出發,至下關碼頭下船渡江。沿途路祭者,如總商會、警察廳、中交二銀行,及其他各機關,計有四十餘處之多。儀仗中有僧道一百餘人,陸軍一旅,美國海軍四十名,金陵各學校學生一千餘人,勳亭、命令亭等有十餘座。一路由警務處王桂林每離五丈派雙崗四名,並有陸軍隨處保護。一時觀者人山人海,幾無立足地。滬寧路因見鎮江各地往寧觀者乘客甚為擁擠,故特開專車一次,以便觀客即日回家。”(《李故督出殯盛況》,《申報》1920年11月1日)事實上,一些普通富貴人家的大出喪也能夠引來大量觀眾,如無錫某紡織廠主人的母親去世,“一切儀仗頗極繁盛,如軍樂、旗傘各種喪禮應用之物,均向蘇滬等處賃來。行喪之際,交通斷絕,足有裡許之長。鄉城男女之特來瞻仰者,滿坑滿谷,萬人空巷”。
直至20世紀40年代,大出喪仍能在北方社會造成轟動效應。1940年1月24日的吳佩孚大出喪,給老北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幾乎所有居民都自動跑到街上觀禮,形成萬人空巷之勢。甚至有從天津、保定、石家莊,以及京郊四鄉八鎮敢來看熱鬧的。大殯所經過的各街道,兩旁的茶樓酒肆、飯館,樓上樓下臨街的客座事先都被顧客以重金(比平日高數倍價錢)包了下來,以作為臨時觀禮台。”(《吳佩孚的葬禮》,秦虹編著:《名人喪葬逸事多》,第145—155頁)由此可知,民國時期無論南北,大出喪都能吸引眾多看客,包括從周邊地區遠道而來的看客。
事實上,當時的報刊輿論對於大出喪“看客”的批評和諷刺也比比皆是。“亦不是五九,亦不是五卅,亦不是雙十,街市上卻呈出一種不安寧的景狀,像有一件重大事情立刻即將發生似的。各條街道上都擠滿了人群,街的兩旁,店肆的門窗,樓上幾層樓上屋頂上,都立滿了我們的貴同胞。真奇怪,特從來沒有看見這般的群眾,而又這般的整齊。”“在平日嬌貴的我們,這時全都不覺得只是墊起了腳跟,伸長了頸子,遠遠的全神貫注的忘了一切的望著。”(楊小仲:《大出喪》(上),《申報》1926年11月13日)“男的還好,女的卻擠來擠去,走投無路,可是沒有法子擠出人叢,也只得珠汗淋淋的在等候。”“得不到好地位的幾位少女,站在水泥上,穿的是輕而薄的紗衫,給大雨點光顧開得不成模樣,伊們嬌羞的神情,實在難以形容啊。”“還有一班人,都站在先施公司門口石路、拋球場的等電車處,以為是萬穩萬妥,飽覽無余。那無情的西捕,卻拿了棍子來驅逐,可憐那般人,真弄得走頭無路了。”有人吃了兩棍,論者嘲諷道:“我想因看出喪而吃痛,太不值得了吧!”(《出喪趣屑》,《申報》1928年7月13日)看出喪的人們,“雖飽了眼福,卻未免要吃些苦頭,丟鞋落帽和扒去皮包,都還是小事;若不幸而發生踏傷孕婦或迷失小孩等慘劇,也只能‘打落門牙向肚裏咽’罷了”。於是有人說:“最好沒有看出喪的閑人,就不致於有慘劇”,論者因而評論道:“話雖不錯,但既無人看,也就沒有大出喪了。”(姚克:《論大出喪》,《申報》1933年12月21日)“大出喪”與“看客”就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互相成就,構成了民國社會的一道奇觀。

盛宣懷
魯迅、邵洵美與盛宣懷大出喪
對於“大出喪”這道民國奇觀,魯迅當然耳熟能詳,在其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現。在《準風月談·後記》中,魯迅寫過這樣一段話: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
這段文字涉及到1933年上海文壇著名的“女婿”風波。當時,邵洵美在《十日談》上撰文說,人們之所以做文人,“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一支筆,一些墨,幾張稿紙”,“無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邵還列舉了五類“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類型,其中有這樣兩類:“(三)學問有限,無處投奔,但是外國文字,倒識得一些。於是硬譯各種文章,自認為時代前進的批評家。”“(五)大學教授,下職官員,當局欠薪,家有兒女老小,於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時藉以消遣的外國小說,譯一兩篇來換些稿費。”“硬譯”曾是魯迅的“自謙”,後被梁實秋撰文批評,魯迅隨即反擊,以至於圍繞“硬譯”展開了“魯梁論戰”,“硬譯”由此成了魯迅的“標簽”。“大學教授”、“下職官員”也符合魯迅的經歷,因此魯迅專門撰文《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予以回擊。(費冬梅:《1933年海上文壇的“女婿”風波》,《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3期)
在《各種捐班》一文中,魯迅指邵洵美步入文壇完全是靠錢鋪路,是“捐班”文人。在《登龍術拾遺》一文中,魯迅直接針對邵洵美的盛宣懷“孫婿”身份大做文章:
術曰:要登文壇,須闊太太,遺產必需,官司莫怕。窮小子想爬上文壇去,有時雖然會僥幸,終究是很費力氣的;做些隨筆或茶話之類,或者也能夠撈幾文錢,但究竟隨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陪嫁錢,作文學資本,笑罵隨他笑罵,惡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頭銜自來,贅婿雖能被婦家所輕,但一登文壇,即聲價十倍,太太也就高興,不至於自打麻將,連眼梢也一動不動了,這就是“交相為用”。
“闊太太”指邵洵美之妻盛佩玉,為盛宣懷的孫女。正如前文所言,盛宣懷大出喪是近代上海最為著名的一次喪禮,出殯儀仗“應有無不有,不應有亦有”,而支撐這一切的當然是盛家雄厚的家財,據傳僅盛宣懷大出喪便“耗費三十餘萬”大洋。據學者研究,在盛宣懷去世後的第二年(1917年),盛氏家族專門設立“清理處”對盛宣懷的遺產進行清理。經過兩年半的清理,盛氏財產清理處於1920年初公布盛宣懷家產共計13311396.495規元兩。(雲妍:《盛宣懷家產及其結構——基於1920年盛氏遺產清理結果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盛宣懷大出喪
在《準風月談·後記》中,魯迅將邵洵美的“作文人”與“大出喪”進行比較,因為在其看來,兩者都要“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不同的是,邵洵美的“作文人”在熱鬧一陣後就“仍是一條空街”,而盛宣懷的“大出喪”在數十年後“還有幾個市儈傳頌”,因此邵洵美的“作文人”還不如盛宣懷的“大出喪”。
“大出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看來,本已極為不堪,姚克曾撰文諷刺“大出喪”,稱大出喪時“棺材中的死人雖出足風頭”,但其實只是一個幌子,功布中“禍延顯考”的孝子們才是大出喪的主角,“雄赳赳的保鏢是隻保孝子不保死人的,便是全副儀仗也不過是壯孝子的威風,何嘗為死人的體面”!鄒韜奮也曾寫道:“我每在馬路上經過,看見出喪,尤其是大出喪,便發生‘靠叫花子鬧鬧’的毫無意思!”“聚了一大堆叫花子,鑼鼓喧天,絲竹並奏,簡直像‘歡送會’與‘慶祝早死’的氣概!不但是極無謂的耗費,而且也是極討厭的事情,極可笑的事情。”(韜奮:《靠叫花子鬧鬧》,《生活》周刊第3卷第5期,1927年12月4日)“大出喪”在當時知識人的眼中已然如此不堪,魯迅還要嘲諷邵洵美的“作文人”還不如“大出喪”,可見魯迅對邵洵美輕蔑至極。
邵洵美以富家公子的高姿態撰文,奚落當時文人的貧窮和落魄,可謂以富欺貧,而“大出喪”是富人的遊戲,盛宣懷的“大出喪”又最為典型,恰好邵洵美又是盛宣懷的“孫婿”,魯迅將這些聯繫起來,才有了將邵洵美“作文人”與盛宣懷“大出喪”進行比較的辛辣嘲諷,邵洵美真可謂自作自受。
稍可補充的是,魯迅所謂“大出喪”在數十年後“還有幾個市儈傳頌”,也並非虛言。盛宣懷大出喪後,滬上每當有新的大出喪,看客們總是要將其與盛宣懷大出喪進行一番比較。例如1931年底,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的大出喪便引起了這樣一番議論:
“郭標蓋過黃楚九了。”“遠不及盛宣懷!盛宣懷那次出喪,哄動了幾百萬人,在上海總算是空前絶後。”街上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在那兒閑談。(《從南京路說到南京城(上)》,《申報》1932年1月18日)
聽說從前盛宣懷死後大出喪,鬧動了好幾十萬人都趕來上海看熱鬧。不久以前永安公司總經理郭標出喪,我雖沒曾親眼看見,但據一般輿論批評,似乎也還“嘸啥”。(《借死人出風頭》,《申報》1932年1月28日)
盛宣懷大出喪幾乎成為一個標杆,成為衡量其他大出喪顯赫程度的標準。魯迅身在“大出喪”最為頻繁的上海,應該不僅目睹了許多的大出喪,也耳聞了許多有關大出喪的議論,因而在文章中運用“大出喪”作為材料時才如此得心應手。
毋庸置疑,魯迅筆下最經典的“看客”形象,還是他留學日本期間在“電影”上看到的圍觀砍頭示眾的那些體格健壯但又神情麻木的中國人。這也是對魯迅刺激最大的“看客”形象,以至於他在《呐喊·序言》和《藤野先生》中不厭其煩地一再提起。但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魯迅首次明確提出改造“看客”式的國民性,是在1922年底。從1906年在日本觀看“日俄戰爭教育片”,到1922年底撰寫《呐喊》序言,在這十六年間,魯迅心目中有關“看客”的印象一定發生了不少變化。也許日本的經歷只是埋下了種子而已,日後在國內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國人“看客”式的生存方式,尤其作為“看客”盛宴的“大出喪”,想必是魯迅經常看到的,也是刺激魯迅不斷深入思考的最為奇葩的社會怪相。或許,正是在這類現象長時間的刺激下,思考下,魯迅逐漸形成了觀察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看客”視角,並在作品中塑造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經典形象——“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