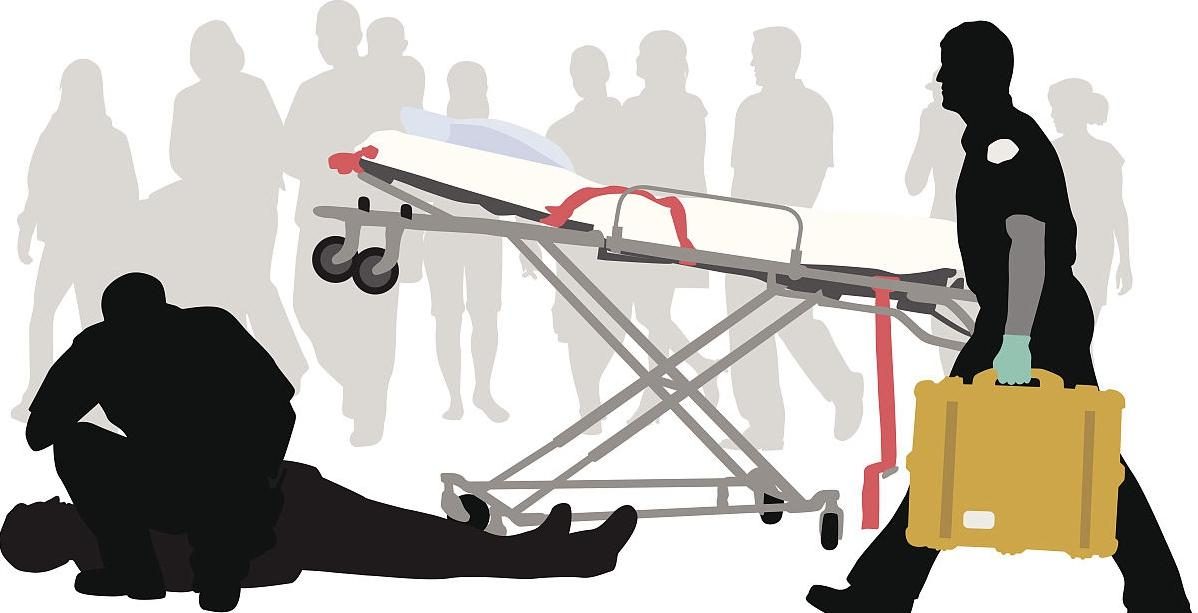一生都在與病魔作戰的人,在面對自己的死神召喚時往往更為平靜。他們很清楚即將發生的過程,也了解可能面臨的選擇,其中大多數已經對治療涉及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來自一位目睹無數生死醫生的坦率告白,2011年發表於《紐約時報》,曾引起巨大反響。
可能會因為無法接受Murray醫生的直言不諱而中途掩卷,也可能想到一點不那麼願意麵對的過去或未來......一聲嘆息。
本期配圖為大自然中隱藏的神聖幾何圖形,在本應完美具足的世界裡,人們最終想說的總是:
逝 者 安 息
生 者 平 靜

 播放GIF
播放GIF
一個醫生對死亡的告白
文 Ken Murray / 譯 研墨丫頭
美樹嘉文藝志
-


幾年前,我敬重的整形外科醫生和我的精神導師查理在腹部發現了腫瘤,醫生做了進一步檢查後確診為胰腺癌。
他的主治醫生是全美最優秀的專家,其開創的獨特療程能把重度胰腺癌病人生存5年的幾率從5%提高到15%——這可是原來的三倍!當然,與此同時病人必須應對艱難的治療和堪憂的生活品質。
查理斷然拒絕繼續治療,第二天就回到家裡,停下一切工作,再沒踏入過醫院一步。他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與家人們在一起,也儘可能讓自己感覺舒服些。幾個月後,查理在家中去世。
他沒有使用任何化療、放療或手術,醫療保險也沒為他花費多少錢。


雖然沒人經常提起這樣的話題,但真的,醫生也同樣面臨死亡,而且他們選擇的方式和普通人並不相同。耐人尋味的是,他們往往不會追求更多救治,反而是越少越好。
這些一生都在與病魔作戰的人,在面對自己的死神召喚時更為平靜。他們很清楚即將發生的過程,也了解可能面臨的選擇,其中大多數已經對治療涉及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但是,他們還是更願意輕鬆地離開。
醫生當然也不想死,每個人都想活下去。然而對醫學的了解也讓醫生足夠明白醫學的局限,足夠明白人最害怕的東西:痛苦而死,孤獨而死。他們會告訴家人,當最後的時刻到來,務必不要再來什麼英雄逆襲般的拯救——在生命的最後,他們絕不想被心肺復甦的機器擊碎肋骨(是的,正確的心肺復甦必然導致如此)。


幾乎所有的專業醫護者都見過所謂的「無效救助」,這種事天天都在發生。那是醫生們竭力用所謂最先進的科技把一個劇痛的病人「命懸一線」的時候——身體被切開,插滿管子,連接在各種儀器上再灌入大劑量的藥物。
在每天費用高達幾千美金的ICU(重症監護室)裡,這就是常態。
我已經記不清多少次聽到同事對我說過差不多的話:「你要保證,如果發現我成了這樣一定要記得殺了我。」他們是認真的:有些同行隨身佩戴著NO CODE的徽章以告知醫護人員不要在自己陷入垂危時嘗試心肺復甦搶救,還有人甚至把字樣紋在身上。
在醫生眼裡,看著病人飽受折磨是最痛苦的事。我們被訓練成不可以輕易在工作中表露自己的感受,但是私下裡大家還是會有發泄:「天吶,怎麼能忍心對自己的親人這樣?!」
我常懷疑這是醫生比其他職業人更容易陷入抑鬱和酒精依賴的一個原因;而我很清楚知道,這是自己後最後十年職業生涯離開醫院的重要原因之一。


究竟是什麼使得醫生每天在做這些換成自己也不想要的「救助」呢?這個既簡單也不簡單的答案裡隻包含三個詞:病患、醫生、系統。
首先是病患一方。要理解這個角色,不妨設想這樣一個場景:某人已經失去意識,被送進急救室。在這始料未及的情況下,病患的家屬們很快會發現自己陷入了應接不暇的選擇題模式,讓人不知所措。這時候醫生如果問你:「要儘力搶救嗎?」回答都會是:「當然!」然後……噩夢自此開始。
其實有時病患家屬想說的「儘力」只是「合理地儘力」,但麻煩的是他們很難知道什麼是「合理」的界線;在慌亂和悲傷之中,也無法想到怎樣詢問醫生和分析醫生的回答。站在病患的立場,醫生的「儘力」只能是用盡所手段,不論是否「合理」。
在這樣場景中,病患家屬對醫生(醫療手段)不切實際的期待值也是深層的原因。
很多人以為心肺復甦術是個可靠的救命法寶,但實際上結果常常很差。我自己接納過幾百個心肺復甦後的急診室病人,坦率地說我只見過一個人活著走出醫院——這是一個本來就沒有心臟問題的人(他的情況準確說是「張力性氣胸」)。
如果換成是嚴重晚期病患、老人或是致命疾病的患者,那麼心肺復甦的成活率幾乎接近於零,而要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卻非常巨大。
一直以來,缺乏知識和被誤導而產生的期待值最終引發了許許多多錯誤的決定。


當然病患一方並不是唯一的原因,醫護方也同樣在推動劇情。但這確實是很棘手的事,即使某個醫生對「無效救助」深惡痛絕,卻未必找得出合適的方法說通病患和家屬。
我們再來想像先前的場景:急救室外站著極度悲傷甚至已經開始歇斯底裡的家屬,他們和醫生素不相識——要在這樣的情境中建立信任感和信心是件何等微妙而艱難的事!
人們很容易對醫生帶著某種預判:醫生這是想省時間?省錢?省事……?尤其是當聽到醫生居然建議放棄進一步搶救,家屬的情緒可想而知。
有的醫生非常擅長溝通,有的醫生更有權威感,但無論哪種他們面臨同樣的壓力。每次面對涉及瀕死境地的情況時,我會用這樣的方式:
儘可能提前商討,
羅列我認為「合理」的方案,
盡量用外行人聽得懂的「俗話」 解釋可能發生的負面結果。
經過這樣的溝通後,如果患者或家屬仍然堅持我認為毫無意義並有害的救助,我會建議他們轉投別的醫生或醫院。


我曾不止一次問自己:有時候是不是該用更強硬的態度?因為我知道即使是轉給其他人,結果也難免讓人心有餘悸……
記得有一個我挺喜歡的病人,她來自著名的政治世家,得了很嚴重的糖尿病,血管阻塞導致雙腳疼痛難忍。基於對病情的了解,我盡自己所能的一切療法來幫助她免受手術之苦。
然而他們後來還是尋求了其他醫生(我並不認識),接手的醫生也許並不像我那麼了解病人的整體情況吧,最終決定為她的雙腿做血管繞道手術。
然而不幸的是,手術不但沒有恢復腿部的血液循環,手術傷口反而根本無法癒合。她的雙腳開始腐爛,必須接受雙腿截肢。就在這一切發生的兩周後,她死在那間赫赫有名的醫院裡......
以上兩方面發生的失誤都是顯而易見的,但更多時候醫患雙方都只是這個鼓勵過度治療的龐大系統的受害者。


不能否認有的醫生會為了增加收入而去做一些毫無意義的救治,但更多時候,是出於不得已——由於害怕面臨無休止的投訴和起訴,醫生們不得不按病患的要求做「一切努力」。有時就算是已經做了最充足的準備,還是可能被這個運作系統吞噬。
傑克是我曾經的病人,已經78歲,在漫長的治病過程中經歷了至少15次手術。他告訴我再也不想被綁在那些維持生命的儀器上。
之後的一個周六,傑克出現嚴重中風,在失去知覺、也沒有太太陪伴的情況下被送進了急救室。醫護人員竭盡全力讓他活下來,在ICU裡為他連接上管線和儀器。
我知道這是傑克最擔心的噩夢,趕到醫院後就和他太太以及醫院同事討論了處理方案,並拿出傑克早先留下的關於拒絕急救的囑託,然後我親手關掉了維持機,坐在那裡陪著他。
兩小時以後,一切結束了。
雖然傑克留下了明確的願望,他仍沒能按自己期待的那樣安靜離去——因為整個系統會進來乾預。我後來才知道,當時有個護士甚至舉報了我切斷傑克的生命維持機的行為,認為有蓄意謀殺的可能性......
當然,因為傑克的囑託黑紙白字非常明確,最後我沒有承擔什麼責任。可是想到要面臨警察的盤問和偵察已經足以讓每一個醫生望而生畏!
我當時完全可以讓傑克繼續待在ICU裡苟延殘喘,看他活著,看他飽受痛苦——對於我,這樣的決定實在容易得多。更不必說這麼做我還能多掙一點錢,而醫療保險公司的帳單金額最終也會高達50萬美金。
這些難言之隱都讓「過度治療」成為理所當然的事。


拋開這一切,回到個人的立場,恐怕沒有一個醫生會願意「過度治療」自己。
我們見太多了,到了最後幾乎每一個同行都會想個辦法控制疼痛,讓自己盡量死在家裡。「臨終醫院」也能為更多絕症病人提供更舒適更有尊嚴的離世,讓最後的時光免受過度治療之苦,再過幾天平靜的好日子。
當我在廣播裡聽到《紐約時報》著名記者Tom Wicker選擇在家中安然辭世的消息,這讓我震動不已。這樣的故事如今越來越多,我能感受到其中的善意。


幾年前,我的表兄托奇(Torch意為「火炬」,他是在家裡接生的,大家用手電筒火炬照著亮帶他來到這世界)被發現肺癌已經轉移到腦。我帶著他找了好幾個專家,在得知生命最多只能維持4個月左右後(還是在必須每周3-5次來醫院化療的情況下),托奇選擇放棄治療,他搬來我家,僅僅吃一些防止腦積水的藥片。
結果我們在一起度過了整整8個月。他做了許多自己喜歡的事,我們就像他沒病的時候一樣到處找樂子:一起去迪士尼——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或者在家裡閑呆著,托奇本來就是個運動方面的呆瓜,但他特喜歡一邊吃我做的東西一邊看體育台,沒有醫院的營養餐,天天吃可口食物竟然還讓他長胖了點。
托奇沒有經受特別疼痛的折磨,精神也一直很好——直到有一天,他睡著後沒有再醒來,又昏睡了三天后,他走了。
這八個月來,他治療所費的僅僅是那一點點藥片錢,大概20美金。


Torch並不是醫生,但他知道生活的品質比數量更寶貴。難道這不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的願望麽?
如果真有一個用來衡量死亡的標準,那麼「尊嚴離世」是我的答案,我也會告知我的醫生這最後的選擇。
對於一個職業醫生,這樣的決定並不難做,大多數的我們都會如此。
無需什麼豪言壯語,只是輕輕走進那屬於自己的黑色良宵——就像我的導師查理,我的表兄托奇,以及許許多多的醫生們選擇的那樣。
來源:美樹嘉文藝志
T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