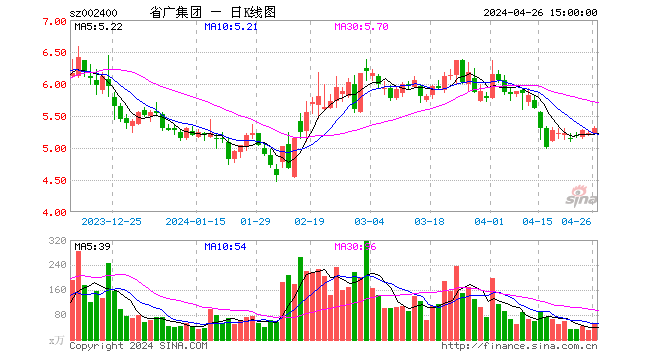紅刊財經 周月明
編輯/承承
華錄百納2018年業績巨虧看似由外界環境所導致,可實則是公司為了未來業績持續向好表現有刻意業績洗大澡之嫌疑。對交易所問詢函提到的問題,公司在關鍵問題上進行了回避,其背後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一直備受關注的影視上市公司巨頭華錄百納2018年業績突遭滑鐵盧,6.3億元營收同比大幅下滑72%,歸母淨利潤巨虧34.17億元,同比負增長3201%。5月16日,就其業績的大幅變臉,深交所下發了年報問詢函,而上市公司也神速地於當日就給予了回復,回復內容雖然看似很誠懇,但《紅周刊》記者在深入研究其近幾年財報和問詢函回復內容後發現,華錄百納2018年業績大幅虧損背後難免有業績洗澡之嫌,而其在關鍵問題上答覆的模棱兩可,可謂誠意不足。

巨虧引發業績洗大澡嫌疑
財報數據顯示,華錄百納2016年至2019年一季度的營收分別為25.7億元、22.5億元、6.3億元和4108.81萬元,同期歸母淨利潤分別為3.8億元、1.1億元、-34億元和976萬元,雖然2017年在營收變動不大下,歸母淨利潤大幅下滑71%已經讓人吃驚,可2018年的34億元巨虧則讓市場在震驚的同時,更是一片嘩然,原因在於該公司有明顯的業績洗大澡嫌疑。
華錄百納2018年年報顯示,因出售2014年高溢價並購的藍色火焰核心資產——喀什藍火和北京藍火,公司這一年計提商譽減值20億元(其中喀什藍火和北京藍火商譽減值15.56億元,剩餘藍色火焰資產商譽計提減值4.42億元),計提應收款項壞账損失由2017年的9298萬元大增至2018年的9.7億元,再加上無形資產、固定資產、存貨跌價等各種各樣的資產減值,凡是能做減值計提的科目全都未能幸免。總體上,華錄百納2018年的資產減值金額由2017年的2.12億元躥升至2018年的近15億元。
一次性對藍色火焰核心資產計提20億的商譽減值不可謂不是大手筆了,然而如此一次性計提的做法是否合理是存在疑問的。
2014年,華錄百納以發行股份和支付現金的方式斥資25億元收購了同為影視製作行銷公司的藍色火焰,收購價相較標的公司淨資產溢價650%,增值金額21.7億元。正是通過那次收購,上市剛兩年的華錄百納營收在並表後出現了大增,由2013年的3.78億元上升至2014年的7.6億元,一度與華誼兄弟等影視公司相比肩。當時,藍色火焰也確實風頭正勁,行銷了《爸爸去哪兒》、《非誠勿擾》等現象級綜藝,還推出了《快樂大本營》《爸爸去哪兒》同名大電影。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隨著時間推移,在近兩年經營中,藍色火焰基本上將影視行業能遇見的“雷”都不幸一一踩中。
在藍色火焰完成業績承諾的第二年,即2017年開始,藍色火焰趕上了各種政策的限制,“限娛令”、“限童令”、“限真令”等政策相繼頒布,使得電視綜藝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管控,這不僅使黃金時段對綜藝的播放越來越少,讓藍色火焰大為受益的《爸爸去哪兒》也因“限童令”而遲遲未再繼續。與此同時,公司在2017年有很多計劃項目也因政策原因而未能上馬。而這點從上市公司回復函中也予以說明:“由於企業所處行業環境及自身經營環境的狀況惡化,綜藝節目收視率下降、廣告招商不及預期,導致綜藝項目數量大幅遞減,收入下滑,而藝人成本及製作費用維持高位,項目大幅虧損”。
話雖如此,可有一點還是讓人奇怪的,為何在上市公司2017年淨利潤出現大幅下滑70%的情況下,華錄百納在2017年卻隻對因並購藍色火焰所產生的商譽做了3000萬元左右的減值準備計提,如此做法是否存在少計,是否有刻意美化2017年業績的動機?
除了2017年對藍色火焰並購所帶來的商譽有少計之嫌,華錄百納對2018年應收账款計提壞账損失9.7億元,相比2017年翻了十倍的情況也是讓人奇怪的。對此問題,交易所明確要求上市公司“逐項說明單獨計提壞账準備的應收账款的客戶名稱、產生原因等”,可對於交易所的問詢,華錄百納卻仍以客戶A、客戶B、客戶C等名稱披露,遲遲不願意披露具體有哪些公司,如此做法難免讓人感覺其背後可能存在一定貓膩,因為2018年暴露的娛樂行業明星偷稅一事若不是有證據證實,誰會知道這其中會有那麽大貓膩!而華錄百納此次不願公布客戶名單是否也是出於保護客戶的目的?防止出現類似2018年稅收事件。但不管出於何種目的,其不願公布名單的做法是否合規是值得推敲的,因為若每家上市公司都選擇客戶A、客戶B的做法,那監管層提出的財報數據公開準確、信披合規等的規定又有何用?這不明擺著要讓上市公司去刻意規避媒體或投資人的審核嗎?
在藍色火焰的並購方案中,可以看到在收購的當初,藍色火焰大部分應收账款均在一年以內,“截至2013年底,一年以內的應收账款佔比98.96%”,而查看上市公司2018年年報時,則可發現公司的應收账款账齡出現明顯變化,5.56億元應收账款,账齡在一年以內的應收账款僅有1900萬元左右,應收账款佔比最大的已經變為3年以上,顯然,這幾年有很多欠款是持續多年未收回的。從風險角度講,這些逾期的應收账款早就需要充分計提壞账準備的,可事實上從往年的壞账計提來看很可能是不充分的,進而導致了2018年的集中計提,這種做法是否合規本身是值得商榷的。要知道,此前原該計提的壞账準備而不計提,對當年的業績表現是起到一定裝飾美化作用的,如若充分計提,則很可能對當期業績帶來明顯負面影響。而集中一次計提,雖然對一年的業績帶來明顯負面影響,但對來年或後幾年的業績同比表現卻有明顯利好,這是屬於非常典型的業績洗大澡的手法。
其實,除了華錄百納有業績洗大澡的嫌疑外,其子公司藍色火焰還出現了“人”的問題。從上市公司披露的問詢函內容來看,“進入2018年以後,藍火文化核心經營管理團隊變化較大,導致原預定項目規劃無法正常進行,短期內公司相關業務無法有效延續。”這意味著,藍色火焰團隊目前並不穩定,這對於依靠“人”的影視公司來說是很大打擊的。
資料顯示,藍色火焰在被華錄百納收購之後,其創始人志向好像也越來越不在公司經營上,反而在套現減持上大展拳腳。在2016年藍色火焰三年的業績承諾的順利完成之後,創始人胡剛及其親屬就開始逐步減持套現。據統計,胡剛在2016年完成了兩次減持,累計減持1444.72萬股,套現金額約2.8億元;2018年下半年,胡剛又減持500萬股,套現3000萬。股權解禁以來,胡剛已經累計套現3.1億元。而相較胡剛的大力減持,其親屬李慧珍也毫不手軟,累計減持6次,套現1.54億元。光套現似乎還嫌不夠,在限售的股份中,胡剛質押率高達99%,而李慧珍質押率則達100%。
實控權變更後,華錄百納漸被“殼”化
在核心資產被低價拋售之後,藍色火焰剩餘的資產所涉及的商譽也在2018年早早做了減值,這意味著華錄百納對其剩餘資產未來的業績表現是不抱有信心的,與此同時,就華錄百納自己的存貨和目前的項目計劃來看,公司對未來的發展似乎信心不足。
資料顯示,華錄百納目前存貨共有3.66億元,80%金額是五部影視作品所留存,其中只有電視劇《東宮》和綜藝《神奇夥伴在哪裡》已播出,但尚未結算。其余三部還在發行中,在影視行業政策越來越嚴的情況下,余下作品能否成功放映還是未知數,一旦“流產”顯然會給華錄百納造成很大的資金負擔。
從華錄百納2018年年報披露的情況看,其2018年的營收主要來源於劇目的海外以及二輪發行、各大衛視的內容行銷、硬廣項目等。報告期內,只有《讀心》、《不負時光》兩部作品取得了發行許可證,三部綜藝在不同渠道放映,其他作品或是處於後期製作,或是僅在拍攝階段和籌備階段。
需要注意的是,華錄百納的實控權在2018年曾出現過大變動,美的集團的何享健、何劍鋒父子在2018年4月聯手斥資18億元獲得18.16%股權,成為華錄百納新的控股股東。然而在何享健、何劍鋒父子控股後,其卻大手筆進行資產剝離,首先剝離了核心資產藍色火焰,其後又在播放、籌備項目上進行了一系列資產剝離操作,如此做法,實在令人擔心華錄百納會不會最終淪落為一家殼公司,最終存在被打包出售的可能?
營收差異巨大
除了上述問題,《紅周刊》記者在查看華錄百納近幾年財務報表過程中發現,其營收數據在財務勾稽關係處理上也是存在較大異常的,進而讓人懷疑其2018年大幅虧損很可能為了對衝往年數據上的造假。
財報披露,華錄百納2016年至2018年營業收入分別為257486.4萬元、224762.37萬元和62952.12萬元(見表1),其中有257274.47萬元、218341.29萬元和61741.67萬元為國內營收,考慮到影視行業國內營收有6%增值稅率影響,因此可推算其含稅總營收大約為272922.87萬元、237862.85萬元和66656.62萬元。

同期的合並現金流量表數據顯示,公司這三年的“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分別為182707.65萬元、181365.77萬元和144331.33萬元,此外,2016年至2018年新增預收款分別為4138.64萬元、-2738.95萬元和-2321.16萬元,在對衝同期與現金收入相關的預收款項影響後,與這三年營收相關的現金流入了178569.01萬元、184104.72萬元和146652.49萬元。將這三年含稅營收與現金流數據勾稽,則含稅營收分別比收到的現金多出94353.86萬元、53758.13萬元和-79995.87萬元。理論上,這將體現在當年債權的增減上,即理論上2016年至2018年的應收款項應新增94353.86萬元、53758.13萬元和減少79995.87萬元。
然而,在資產負債表中,華錄百納2016年至2018年的應收账款(包含壞账準備)、應收票據合計分別為250225.68萬元、273940.55萬元和100908.65萬元,分別相比上一年年末相同項數據新增119502.65萬元、23714.87萬元和-173031.9萬元。顯然,這一結果與理論應該增加的94353.86萬元、53758.13萬元和-79995.87萬元差異明顯,分別相差了-2.51億元、3億元和9.3億元。
即使考慮到報告期內華錄百納公布的2016年至2018年的應收票據背書金額(約為5913.16萬元、5124.26萬元和8883.76萬元)影響,仍無法解釋上述巨大的數據差異問題,顯然這是需要上市公司給出更多詳細解釋的。
採購數據不匹配
除了營收存在較大異常外,《紅周刊》記者發現華錄百納2017年、2018年的採購數據同樣存在較大金額異常。
財報披露了2017年和2018年向前五大供應商的採購金額及佔總採購金額的比例,2017年為79817.04萬元和43.35%(見表2),2018年為42063.75萬元和40.75%,由此推算出這兩年的採購總額分別為184122.35萬元和103223.93萬元,考慮影視廣告行業6%增值稅率的影響,則其含稅採購總額分別達到了195169.69萬元和109417.36萬元。

在2017年、2018年的現金流量表中,公司“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分別為204046.46萬元和103213.65萬元,剔除當年預付款項新增的948.01萬元和1439.47萬元影響之後,則與採購相關的現金支出分別達到203098.45萬元和101774.18萬元。將含稅採購總額與現金支出勾稽,則2017年現金支出比採購總額多出了7928.76萬元,2018年含稅採購總額比現金支出多出了7643.18萬元,理論上,這將會導致2017年和2018年應付款項相應的變動。
可事實上,這兩年的應付款項分別為23835.89萬元、9620.67萬元,2017年未減反增了8135.79萬元,2018年未增反減了14215.22萬元,這一結果顯然與理論上的情況是相左的,分別存在-1.6億元和2.19億元的差額。
雖然2017年、2018年還有固定資產原值、在建工程、無形資產原值的增減情況影響,即這兩年幾項之和分別為11195.76萬元、1503.27萬元,較上期分別減少了324.91萬元、9692.49萬元,同期構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現金分別為8868.9萬元、8743.12萬元。兩者勾稽後,理論上2017年和2018年應付款項應該相應減少9193.81萬元和18435.61萬元。可即使我們考慮到這部分金額的影響,實際的應付款項與理論金額的差額反而變得更大。
(本文已刊發於2019年6月15日出版的《紅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