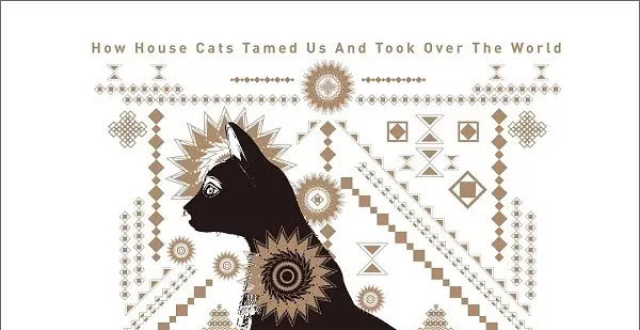@ Jian
赫拉利的訪談中有幾點還是挺讚同的。首先就是對權威尊重的問題。現在能質疑權威的人能有多少呢?每個人在群體中都不那麽理性,而且市面上的權威又多如牛毛,各種事情都有專家來各種解讀,甚至已經到了別人不信我自己信了的地步。媒體也追逐各種熱點,搶佔頭條,加速了各種專家觀點的推銷。所以個體在其中如何識別,如何立足,需要思考的方式和視角。
第二個就是你可以用鳥的視角來看人類。以色列本來就是一個奇怪的國家,他們為了生存需要回到應許之地建立新的國家,恢復希伯來語,取得了經濟、科學、藝術等領域的飛速發展。除了在美國的猶太人,其他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被嫌棄,被迫害,被驅逐。而在巴勒斯坦建國也更怪異,因為他們與阿拉伯人互相仇視。這大部分來自於宗教,而宗教就是人虛擬的一個世界,而人在這個世界裡是仇視和屠殺。我們局外人看就有點像鳥從空中看世界一樣,抽離出來看,根本理解宗教的威力如此巨大,而又沒辦法證實宗教的存在的真實性。對猶太人的仇視可能僅僅是因為他們能快速發展,並佔領財富。人類有無數的解釋可以讓其他人去相信,很多是靠說,靠解釋,是口號,是理論,總能產出新的說法來替代舊有的。所以抽離出來看,似乎是可以看到那張虛擬的大網把人聚攏在一起。所以他說不要把虛擬的故事誤認為成終極真理,他只是工具,要拋開虛構的故事,去真正理解關於自己的真相。
第三就是對於未來。大多數歷史的觀點是通過觀察過去事物的變化而得來的,觀察過去的變化中發生了什麽事,存在哪些問題,當我們關注未來時,應該警惕什麽是危險的。對於未來只能是預警,而預警的經驗來自於對歷史的觀察和思考。

@ one
對於聚焦在赫拉利身上的歷史、未來、宗教、AI,甚至金融、科幻、性取向等等,我都沒有知識背景去討論,唯獨對於現實和故事有興趣,但也只能按下不表了,因為流浪漢沈巍出現了。
之前就看過沈巍的視頻,是一個輟學的零零後推薦給我看的,當時我看過之後覺得這個人有著幾乎無懈可擊的價值觀,還很好奇為什麽他一個零零後會持續關注這樣類型的人?直到前兩天沈巍在街頭被人群圍追堵截,我突然意識到他與赫拉利之間有著一種呼應關係,他們一個在馬路邊的綠化帶裡被追捧,一個在被聚光燈照亮的舞台上被追捧,他兩人代表了兩個階級的人群,他兩人折射出的就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神狀態。
“只有在中國,思想者才會被像搖滾明星一樣對待”,看完這篇採訪,只有這句話一直在我腦際,盤旋了好久我明白,這不是一句好話。我還想到了另外一種情況,也只有在中國,政治領導人才會被像耶穌一樣對待,這一樣不是一句什麽好話。
乍聽上去好像中國的青年對於知識,對於思想無比的尊重與推崇,仿佛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圍又再一次降臨,可現實是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比如今更急功近利,更藐視文化,背後反映出的是這個社會對於知識的異化,對這個時代缺乏安全感以及對歷史和未來的無知。像這樣類似知識回光返照的場景只是他們在說服投資人時的談資,甚至只是朋友圈的一次炫耀。這更像一場秀,和對知識本身的態度並無多大關係,唯一慶幸的是,知識被選擇成為了這個秀的媒介。

其實在中國也不乏赫拉利,羅振宇,高曉松,梁文道等,他們所到之處,無數青年便擁躉至此,赫拉利自己說“在後來的幾年中,我與公眾互動,與媒體互動,在廣播和電視中發表講話,在這些情況中,清晰就是一切”,也就是說普通大眾對於知識的態度是像奶奶喂孫子吃東西一樣的,用當下的話說就是“直給”,也就是強調直接的作用於現實生活,不經過自身的經歷和體悟的知識經驗。好像存在這樣一種情況,當我們面對成名的文化偶像時,作為閱聽人時的我們會存在一種類似“受虐心理”的心理動機,就好像我們跪在地上祈求他狠狠扇我一個耳光,然後以確認無疑的態度告訴我們“我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你隻管聽就是了”,哪怕他自己覺得這不一定是對的。對於聽眾來說我們好像習慣了在這樣的場景下進行自我催眠,因為你是文化偶像,所以我選擇相信你所說的一切,不願也不試圖去發現這些言論背後的漏洞,其實是在時間和腦力上的偷懶和自我麻醉,以便自己不帶懷疑地在這個世間行走,因為產生懷疑意味著巨大的思想壓力和選擇的壓力,這也是赫拉利一再解釋自己不是預言家,而人們並不總是想聽的原因。
但話說回來人類好像從來如此,就像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我們不是都選擇相信了嗎,如果我們選擇不信或者懷疑,那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要重溯人類起源。
回頭說沈巍,他引發的現象相較赫拉利就會更加赤裸,他是被“抖音”的使用者們捧的,之所以捧他是因為他身上產生了流量,或者說身邊的人都在拍他。如果赫拉利身上的文化因素是知識,那沈巍身上的文化因素就是道理,在文化反思或者文化叛逆的年代我們是最排斥道理的,而我們所處的現實是大家開始津津樂道的,樂此不疲的聽別人來給我們講道理,包括零零後們,這和前邊談到的智識上的“受虐心理”是一樣的。
這又讓我想到了韓寒,那時候他作為文化偶像,還會調侃“少跟我說你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飯都多”,許老師曾把“韓寒現象”總結為庸眾的勝利,那今天呢?

@ 鏡中行深
採訪者手記清晰地表達著對如今這種濃縮的、速成的知識潮流的不滿。這也常常被人們所討論,討論在由技術所促動的這股知識潮流,讓更多人更加浮躁、喧囂,急切地追逐簡明、濃縮、確定而且能帶來即時閱讀快感的實用性書籍。成功學之類的書當然是這其中之翹楚。而,暢銷的如赫拉利的幾部曲亦是能夠滿足不少國人的需求。在充滿焦慮的當下,書中知識讓人們得到安撫,通曉人類歷史之餘還輕鬆地進入新的思考維度,看似掌握了面對未來的秘鑰。和文學作品有陽春白雪和下裡巴人之分一樣,有學者也認為知識也是有高低層級之分的,在某種意義,這類書籍讓人們更容易陷入低度知識的泡沫之中。正因如此,才會有更多人憂慮,這是技術快速變革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讓人人都陷於信息泥淖之中無法自清,因此才在焦躁中選擇最簡單有效的方式脫身。在此不去談所謂的技術道德論的問題。而想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談談。赫拉利說“只有在中國,思想者才會像搖滾明星一樣被對待。”這是自嘲,也在說明,國人對於這樣所謂的實用暢銷書籍的追捧力度是無與倫比的。這裡就涉及到我們文化中潛在的功利與實用的基因。不追訴多遠,就說說新中國建立之後。事實上,不管對科學、技術等等一直整體都表現出長期的功利主義的興趣。“理論聯繫實際”的提出得到了狂熱推崇就是歷史的佐證。在當時的必須結合生產的需要和為生產服務是對這句話簡單化、庸俗化的解釋。慢慢地,大家都熟知的運動就是在這樣方針指導下為了經濟、為了國防、為了文化改造而服務。從科技層面來看,當時所有的一切都背離了科研工作的常規程序和評價標準,迎合著當時的口號和狂潮。而功利的價值取向也就這樣深深地遺傳至今,實用主義的理念深入人心。

最後再來談點技術,當回答關於數據恐怖主義的問題時。赫拉利認為唯一對抗的手段仍舊是創新技術。現在很多人認為技術在逐漸毀滅人類。有反對者,用麥克盧漢的“後視鏡”理論來駁斥——“我們盯著後視鏡看現在,我們倒退著走向未來”——人們總是站在後視鏡中看待新技術,看不到前面的新環境。也許,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總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 bug,需要靠新的技術才能修複。任何技術都是人的選擇,在未來的日子,技術的發展越來越符合人的需求,也希望能不斷的解決這諸多令人不安的問題。我想赫拉利在技術方面和麥克盧漢一樣,都是樂觀派。
@ 藍莓
我不預測未來,我只想讓人們有能力討論人類的未來。在新技術革命的現代,一切都在加速,如果不抓住新潮流就會被迅速拋棄,但像 TED 式的知識潮流,只會讓聽眾迷失自己,營造了一種假象,這種新技術革命似乎也有一點裝模作樣。赫拉利帶著工程技術的眼光,將人類社會重組,優化,而且還帶著一點狂熱的情緒。
赫拉利寫書的動力來自於他想給讀者提供清晰的視野,讓人們明白如今真正重要的事情,使他們知道什麽是致其無法看清這個世界的幻想和騷擾。寫作是一種交流,閱讀也是一種交流,所有這些的目的我想也都大概如此吧。同樣他也提醒我們,不要把虛構的故事誤認為終極真理,真的答案是將所有的故事放在一邊,而故事的工具價值是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功能作用,歷史學家等應該考慮工業革命帶來的各方面的影響,用故事來阻止人們,並不混淆人們。而讀者就是學會區分他們,不被迷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人類目前的壓力感和疏離感正在加強,正在失去與自身的聯繫。我還是挺認可他的話,人們必須切合現實,而不是做社會告訴你應該做的事。我們確實已經迷失太久了,不是麽。
對赫拉利的預見力,他認為他不會去預測未來,他隻提供可能性,而且他想從一個作家角度,提供一種有趣並非無聊的預見。創作的過程也是一種有趣的過程,不是麽。還是希望未來能夠多一點樂趣吧。

@ 流徽照影
看完這篇採訪文本,思緒頗多,就著採訪本身而非赫拉利,從以下幾個角度來說說我的想法:一是很佩服赫拉利,能在採訪溝通中、或是幾本暢銷作裡把觀點說得平靜、清晰而易懂,極為寶貴。在我看來,深入淺出與“說人話”是一項難得的本領,進一步說,轉化學科前沿的知識,與推進知識前進同樣重要。
過於分工明確、不斷追求細化、學科壁壘森嚴的學術環境,也已經引發了很多學者的不安。或許再無百科全書,但如果不考慮知識溝通的必要,而是各說各話、孤立向前,那麽也很可怕。《人類簡史》等幾本書,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各學科狂飆突進的知識膨脹、與相對而言非常滯後的大眾認識之間的空白。在當前時代,誰也無法親自投入各個領域;在自己專業之外,誰都需要懂行者拉一把。也正因如此,溝通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高,而這個過程中,簡化與清晰是必要的。
赫拉利暢銷作所呈現的面貌,讓我想到了優秀的大學教科書與普及性讀物。這類書籍,不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也不要求接受者單純感受知識密集與過量的痛苦,而是給予一種可能的思路,讓剛接觸這個領域的、有學習訴求的“普通讀者”也能大致了解知識之樹的一路枝乾,從中獲得興趣與啟示。這類書籍應當得到慎重的正視,它們的對象是所有人而非領域專家,伴隨著可讀性必然喪失一定的專業性,只能指路而不能進一步鋪路,尤要警惕過度捧高。二是也佩服採訪者,開篇的一句話就讓我倆同步了:“對於所有過分流行的人與物,我總抱著某種懷疑”。採訪者非常敏銳地抓住“赫拉利在中國”的特殊之處,指出中國受製於歷史語境的影響,更明顯地、不自覺地沉浸於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尤為具有速成的渴望。但教材或普及讀物,只是教材或普及讀物而已,哪怕是優秀的方法論指導,也無法未經實踐憑空生效。知識本身不能具有直接的實用性,更不存在顛撲不破的真理。

而在這股狂熱的“求知”衝動中,這本書反而被誤用成為“興奮劑”,而不是合乎赫拉利意願的彌合認知差距的“安定劑”。赫拉利說“我只是個歷史學家”,他至少是相對清醒而有分寸的;而他的好些觀眾(注意,是觀眾)則進一步高聲喊叫“赫拉利是預言家”或者“赫拉利是騙子”,並不在乎他的書的內容,卻試圖通過這場狂歡分得幾杯羹。這種事情也不少見,三十年前學術圈內的“索卡爾事件”就引發了所謂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間的“對立”,而在互聯網時代,這樣的相互不理解、各自站隊的情況更會頻發,而且更加情緒化、粗鄙化。內容簡化不同於口號化,表意清晰也不指向觀點絕對;但缺乏細讀,再加上狂妄,大概率將引向後者。
可怕的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現象,而是背後共通的不審慎與好面子、短見與誤用。魚龍混雜的呐喊聲下,“誤解”前所未有地高發,擠壓理性與審慎話語的地盤。這種環境推演到極端,不同領域的學者可能無力分辨自身領域以外的狀況,要麽更大概率產生誤解與對立,要麽紛紛甘做埋頭的鴕鳥。這種野蠻的環境大大增加了溝通的成本,更容易誕生非理性權威與盲從的信徒。
編輯丨田也
圖片來自電影《方形》
更多共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