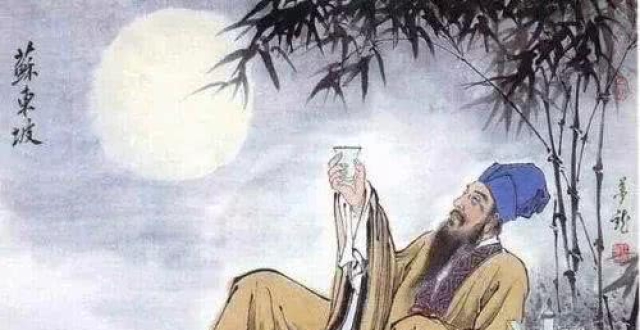今人常將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的詩“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作為蘇軾乃至中國古代士大夫鄙薄法律的證據,這一理解稍顯簡單化。實際上,蘇軾的本意並非如此,而且中國古代大部分士大夫也認為,無論是從政為官,還是治學修身,都需要學習一些法律知識,有的還有較深的法學素養。但受製於大環境,律學是不大受重視的學問,官員們也不大尊重法制,甚至公然法外用刑而不以為非。

實際上,讀書亦讀律是中國古代許多有識之士
(不限於官場人士)
的共同主張。從一些間接記載看,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律學修養不錯。但另一方面,律學始終是不大被看重的學問,蘇軾詩中反映出的不以為然和牢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部分真實。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相對於對律學的淡漠,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多較為自覺,即使是刑名官員也多具有較深的儒學功底。
此外,一方面是因為“無訟”的傳統,律學沒有活動空間,發揮不了什麽作用。一般讀書人出於功利目的,沒有學習法律的動力和興趣。另一方面與中國古代傳統價值觀有關。傳統士大夫和官僚階層大都認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學的地位是有高下貴賤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術;文章和儒學則仁慈深遠,是先王之道。
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後,社會上才逐漸重視法律,法學才逐漸成為熱門專業。至於真正把法律當一回事,尊重法制和人權,那更是後來的事情了。但中國古代士大夫關於讀律的重要性,以及讀律和讀書關係的論述,頗有獨到之處,對今天也有啟發。
北京大學近代法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法學博士張群,由蘇軾的這句戲言開始談起,重新梳理了中國各個朝代和士大夫們對於法律的觀念和態度,為我們講述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以及中國古代法律觀念的演變史。文章選自《法史學刊·2019年卷·總第14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讀書萬卷不讀律”?
撰文丨張群
整合 | 吳鑫
北宋著名文學家、詩人蘇軾曾有一句“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
(一作終)
無術”的詩,流傳甚廣,常被作為蘇軾乃至中國古代讀書人鄙薄法律的證據。
清末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認為此詩乃“蘇氏於
(王)
安石之新法,概以為非,故並此譏之,而究非通論也”。近代著名法學家楊鴻烈先生也以這句話為據,斷言蘇軾“對於此道
(指法律)
全是外行”。
這些意見從字面上看不無道理,但稍顯簡單化,蘇軾的本意並非如此,中國古代讀書人對法律的態度也遠比這一句話複雜。

《法史學刊·2019年卷·總第14卷》,中國法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張生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蘇軾的本意和實際
根據《烏台詩話》記載,該詩背景大略如下:“是時朝廷新興律學,
(蘇)
軾意非之。以為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忘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 蘇軾還因此遭到禦史舒亶的彈劾:“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
(蘇軾)
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不難發現,這很大程度上只是蘇軾在詩歌中的文學表達,反映了他對朝廷過於強調法律的選人用人政策的不滿,並不表示他認為法律不重要。
事實上,蘇軾本人重視法律在施政中的作用,個人也勤於學習並熟悉法律。例如在討論商旅出境問題上,蘇軾熟練征引《慶歷編敕》、《嘉祐編敕》、《熙寧編敕》、《元祐編敕》等有關規定,主張加強商旅出境貿易管制。在高麗使者買書問題上,蘇軾持反對態度,他不僅熟練征引有關編敕為自己背書,還針對支持派援引《國朝會要》為據
(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均曾賜高麗《史記》等書)
指出,“事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有其害,雖例不可用也”,並從法理角度指出,“《會要》之為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在討論五穀力勝稅錢問題上,蘇軾更廣引《天聖附令》、《元豐令》、《元祐敕》等法規文件為自己辯護。

蘇軾
有法律史學者曾引用蘇軾關於五穀力勝稅錢問題的這篇劄子,高度肯定蘇軾提出的“以法活人”主張
(即依據法律、法令減輕民間疾苦)
,並評論說:“熟悉法典敕令,本是宋代地方官員為政的一項基本要求。值得玩味的是,蘇軾從憂國憂民的悲憤意識出發,把法令的貫徹落實到減輕民間疾苦上,這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素養及人文情懷,也同時說明了憂患意識、法律觀念與立法從政的密切關係。”認為蘇軾在這方面,算“一個典型的代表人物”。這一評論是比較準確的。這也應是蘇軾政績比較突出、受到廣泛肯定的重要原因。
概言之,蘇軾對法律的實際態度遠非詩句看起來的那麽反感,反而是積極學習的。但後人對此的解讀卻多流於形式,未能認真探究其真意,有的則根本不在乎蘇軾本意何在。當然,根源還是在對讀律和讀書關係的認識上存在分歧。
元代:讀書亦讀律
大概因為同代人熟悉蘇軾寫詩的背景,理解其意圖,不致產生重大誤會,宋人似乎沒有專門評論此詩用意的。下面主要看一下元、明、清時期諸人對此詩的解讀,以及對讀書讀律的看法,從中管窺中國古人對法律的態度。
元人大多認為,國家治理和個人治學應當既讀詩書又讀律,二者都很重要。表現在言論上,就是讀律與讀書相提並論。元代楊維楨引用該詩說:“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我哉!”並聲稱元朝就是這樣做的:“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由科第入官,凡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製相參,未有吏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揭傒斯提出:“夫文以製治,武以定亂,法律以輔治,財用以立國,皆君子之事所當學者。”朱德潤提出:“讀書所以知天下之有道,讀律所以識朝廷之有法。士之出處窮達,夫古今事勢,非道無以統體,非法無以輔治,於斯鹹依焉。”甚至官方科舉考試還以此為題:“或言讀書不讀律者,蓋有所譏。及其釋經輒引律文,豈文章之士於律亦不廢歟?”
元人詩歌中也多類似表達。例如:“俗吏固不可,腐儒良足嗤。明經先植本,讀律貴知時。”“近曾讀律知名例,早事通經識孝慈。”“讀經還讀律,為吏本為儒。”“讀書複讀律,才比百煉鋼。”“君家有子為時出,且喜讀書進修律。”早年讀律如五經,案頭夜照練囊螢。”“高人讀律仍讀書,白頭在堂辭我歸。”“讀書讀律已稱賢,孝友尤聞遠邇傳。”“讀書萬卷更讀律,掉頭不肯為蕭曹。”
元人的這種看法,雖然也強調讀書,但和唐宋更為重視讀書的觀念明顯有一定距離。這可能和元代國家治理思想和價值導向有關。元代鑒於宋代尚文“迂而固”之弊,改行“左儒而右吏”政策,強調“以法律治天下”,不重視儒學,甚至一度廢除科舉,因而起用了較多刀筆吏出身的官員,“所與共治出刀筆吏十九”。元朝政府還明確提出,“吾儒事詩書,安用法律”者,“有司所不取”。故,普通人對讀律的看法較為正面。
明清:居官不可不讀律
明清時期,多視此詩為蘇軾譏諷之言,不可當真,認為蘇軾本意還是讚成讀律
(但似乎也無人認真去考察蘇軾本人是否重視和學習法律)
,而且多借機正面提出和論證讀律如何重要,特別是對居官從政之人。有些人雖然沒有引用蘇軾這句詩,提出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強調讀律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下面一並介紹,不再一一區分。
明初名臣、曾任監察禦史的著名儒學人物薛瑄認為,熟讀律令不僅有助於從政,還有助於律己:“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讀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明代中期名臣陸容曾任南京主事、兵部職方郎中、浙江參政等官,他根據親身經歷,得出與薛瑄相近的結論。其所著《菽園雜記》卷六引用蘇軾詩後評論說:
此雖譏切時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學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讀也。書言議事以製,而必曰典常作師。其不可偏廢明矣。嘗見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為俗流,而於時製漫不之省。及其臨事,誤犯吏議,則無可釋,而溺於親愛者,顧以法司為刻,良可笑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六,中華書局,1985,第70頁。)
陸容還在《菽園雜記》卷三記載某年輕官員因不讀《皇明祖訓》差點闖下殺頭大禍的故事,認為不熟悉律例後果很嚴重,“非但詒笑於人而已”,主張“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遍觀而博識”。
後生新進,議論政事,最宜慎重。蓋經籍中所得者義理耳,祖宗舊章,朝廷新例,使或見之未真,知之未悉,萬一所言乖謬,非但詒笑於人而已。嘗記初登第後,聞數同年談論都禦史李公侃禁約娼婦事。或問:“何以使之改業不犯?”同年李釗雲:“必黥刺其面,使無可欲,則自不為此矣。”眾皆稱善,予亦竊識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訓》觀之,首章有雲:“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為之毛骨竦然。此議事以製,聖人不能不為學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諸書,不可不遍觀而博識也。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三,中華書局,1985,第33頁。)
明代中期,正德辛巳年進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敖英不僅主張讀律,還曾探討“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的問題,認為“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凌辱軍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陸世儀引用薛瑄的話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
評論說,孔子“動稱周家法度”,說明其熟悉和重視制度,而後世學者只知道形式主義地追隨孔子談論周代制度,卻忽視現實法制的學習,可謂“不善學孔子者矣”
(“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製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製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還引用陸容的有關言論
(但似引用有誤,參見上文)
,認為“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學者不可以忽視律令之學:
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死”,不覺失色。因歎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之學者,奈何忽諸?
([清]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嶽麓書社,2004,第118頁。)
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李顒也認為:“律令,最為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夫豈無謂而雲然乎!”明末清初另外一位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沒有明確提出應當讀律,但從其批評科舉考試擬判作弊的激烈態度看,他應該也是讚成的。
清代康熙年間刑部尚書姚文然公開表達“律學之不可不講”的觀點,寫了許多法律文章,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刑政類選錄其文七篇,是比較多的人之一。他還撰寫有大批律學筆記,匯總題為《白雲語錄》。
乾隆年間狀元出身的刑部侍郎錢維城明確反對讀律無用論,尤其是因果之說。他說:“夫刑之關於治亂,大矣。”“自煦煦為仁者惑於果報之說,動言庭堅不祀,由於作士,絕口不敢談,至以讀書不讀律,用為訾謷,豈不謬哉!”“律之為書,別嫌疑,明是非,其義同春秋,而三百三千,與禮教相出入。”“儒者平時鄙為不足道,一旦臨民,其不以人命為草菅,也幾希矣。”
清代後期著名官僚、學者梁章钜曾任軍機章京、員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撫並兼署總督等官,行政經驗相當豐富,還撰寫多種著作傳世。他不僅主張讀律,還認為律、例都要讀:“服官不能不讀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八字,則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之義,不可不先講求也。”
清代後期著名文臣周壽昌曾任翰林編修、起居注官、實錄館纂修、侍讀學士、戶部左侍郎、內閣學士等官,多次扈從隨侍皇帝。他認為,蘇軾的詩是譏諷之言,“此因當日安石用商鞅之術,作新法以禍蒼生,士大夫承其風旨,專習申、韓家言以乾進。故東坡詠此譏之”,“其實律何可不讀也?”接著引用上述陸世儀的話,批評其時學者輕視律學,視會典、律例為俗學的陳舊觀念:“昔何休注春秋,率舉漢律。鄭君注三禮,亦舉律說。此窮禮好古之則也。……今人於會典、通禮、律例等書視為俗學,不知所謂不俗者何學也。”
清末著名學者朱一新曾任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禦史,他認為“儒者不可不讀律,律意精深,俗吏烏乎知之?”
上述主張讀律的明清諸人中,有當過中央和地方大員的資深官僚,也有只是作文字工作的皇帝身邊的侍臣,還有講學一輩子、沒有怎麽當過官的思想家,應該可以代表明清時期大部分士大夫的意見。
一般社會觀念上,也多將讀書與讀律相提並論,特別是官場上,如清代江蘇臬署大堂楹聯:“讀律即讀書,願凡事從天理講求,勿以聰明矜獨見;在官如在客,念平日所私心嚮往,肯將溫飽負初衷。”某衙署楹聯:“吏民莫作官長看,法律要與詩書通。”
在文學作品裡,蘇軾這句詩也已然成為一個符號,用來批評那些不通世事、不重實際、沒有行政才乾的官員和士子。如清末才女汪藕裳撰寫的彈詞《子虛記》中,牛撫台說:“好一個不通的宰相,真乃是讀書萬卷不讀律了。”
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根源及局限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蘇軾這句詩只是“一時戲言”,讀書亦讀律是中國古代許多有識之士
(不限於官場人士)
的共同主張。對官吏來說,熟悉律令是履職盡責的需要。對一般士大夫而言,律令也是其知識修養的一部分。前文已經梳理元明清時期的一些史料,這裡再補充一些唐宋資料。例如唐人雲:“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就是針對武則天時封官過濫,許多司法官員不具備相應法律知識所發。北宋歐陽修與士大夫接觸,隻談吏事,不及文章,認為“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所謂吏事應該也包括法律。宋劉克莊自稱:“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缺事。”
從一些間接記載看,中國古代士大夫的律學修養不錯。如宋代周密《齊東野語》卷八《義絕合離》記載,陳振孫曾就一個義絕案例發表了很有見地的意見,而陳振孫是著名目錄學著作《直齋書錄解題》的作者,一位典型的信奉儒學的讀書人。清代史學家錢大昕所撰《十駕齋養新錄》,有多處涉及法律問題
(卷六《古律有蔭減蔭贖》、《加役流》、《斷屠月禁殺日》、《碑碣石獸》、《居官避家諱》,卷七《折杖起於宋初》、《凌遲》,卷十三《唐律疏議》,卷十四《洗冤錄》)
,資料援引廣泛,遍及唐律、刑法志等,其中《凌遲》較之沈家本所述,不乏更為詳盡之處。
但另一方面,律學始終是不大被看重的學問,蘇軾詩中反映出的不以為然和牢騷,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部分真實。元代有明顯的鼓勵讀律政策,仍然“士之讀律者亦鮮”,北京周邊“郡縣官吏貪汙苟且,通知法律者少”,乃至有人自稱“予一生讀書不讀律”。明末“士不讀律”,科舉考試擬判一場,公開作弊造假。薛瑄、陸世儀最主讀律,但二人主要精力還是在儒學,前者“學一本程、朱”,後者“學篤守程朱”。直到清末,薛允升還感慨說:“士大夫輒高論義理,以法律為申韓之學,殘忍刻薄,絕不寓目,豈知法律亦有出於義理者乎?此之不知,則其所談之義理,亦可以想見矣。”
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相對於對律學的淡漠,士大夫對儒家經典的學習多較為自覺,即使是刑名官員也多具有較深的儒學功底,例如薛允升撰寫的《唐明律合編》,頻繁征引洪邁、顧炎武、錢大昕等的觀點,顯見對四部典籍之熟悉。有的刑名官員還有文史著作傳世。清代著名紹興師爺汪輝祖所著《元史本證》是考史作品,頗受讚譽,中華書局點校《元史》時還將其作為參考。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著有《諸史瑣言》、《日南隨筆》等“非刑律者又二十餘種”,其經史造詣獲著名文史學家張舜徽先生高度評價。
有些官吏因各種原因,年輕時以讀律為主,但等生活安定或者晉升到一定職位後,都會再去研讀儒家詩書,而且大多出於主動和自覺,輿論也對此予以好評。例如元代撰寫《刑統賦釋義》的梁彥舉,“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故是書“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
還有多位官員有著類似經歷,例如:“……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跡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跡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複從人授《春秋》。”這些都生動顯示了儒學和律學的不同地位,以及士大夫儒學、律學修養的差距。
這種態度、觀念和言行,一方面是因為“無訟”的傳統,律學沒有活動空間,發揮不了什麽作用。一般讀書人出於功利目的,沒有學習法律的動力和興趣。
另一方面與中國古代傳統價值觀有關。傳統士大夫和官僚階層大都認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學的地位是有高下貴賤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術;文章和儒學則仁慈深遠,是先王之道。例如唐人認為:“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製,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製,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杜甫詩雲:“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宋人認為:“聖人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故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司馬光為相,更直言:“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朱熹也認為:“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遠探其本也。”
這種價值觀在對人才的評價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唐初宰相房玄齡、杜如晦“聽受詞訟,月不暇給”,唐太宗對此提出嚴厲批評,認為他們沒有把精力放到作為一個宰相應該做的事情上
(“求訪賢哲”)
。歐陽修對人的評語也以文章為貴、吏事為輕:“吏事不足汙子,當以文章居台閣。”
即使最為重視律學的元代,亦不乏類似表達,如“書破萬卷,何須讀律以致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修史。”“仁義禮樂,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輔治者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為輔治之具,非為治之本也。”“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申、商之法,豈能加於周、孔之道!學儒不愈乎?”“天下亦豈有舍儒而可以為吏者?”“人之為人,惟孔夫子劄薩克
(指《論語》一書)
不可違耳。”“劄薩克,華言猶法律也。” 明人認為:“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
明末清初顧炎武認為:“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批評“秦以任刀筆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驗也”。又說“諸葛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無間言”,“魏操、吳權任法術,以禦其臣,而篡奪相仍,略無寧歲。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最經典的論斷則是清代四庫館臣所雲:“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

顧炎武
在制度上,官方對學習儒家經典有強製性要求,屬於“必修課”,例如漢代小吏亦須通經。唐代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地方辦學亦“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對讀律則很少有這樣普遍的強製性要求。
當然,更具指標性意義的是人才選拔制度。漢代尚無這樣的限制,其時人才多出胥吏。但隨後開始變化,唐代明確規定,科舉考生出身“州縣小吏”的,“雖藝文可采,勿舉”。宋代“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金朝規定,律科舉人必須通過儒學考試,“知教化之原”,才能獲得功名:“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涵養器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為宜。”元代由吏出身者,可至宰執、台諫,“故士皆樂為吏”,但實際上,人才選拔仍以擅“文章”者為最上等:“方是時,國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藝,或以資,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薦,可立置館閣。”“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
明初選官三途並用,其一為吏員
(另二為薦舉、進士監生)
,著名循吏、蘇州知府況鍾即出身吏員
(“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
。但更多的是限制,明太祖朱元璋時禁止吏員參加科舉,“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 明成祖朱棣時又禁止吏員當禦史,“禦史,國之司直,必有常識,達識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明英宗時禁止吏員當郡守
(“吏員鮮有不急於利者”)
。這樣的制度安排自很難指望律學受到重視。
最後還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中國古代許多讀書人認為居官修身均有必要讀律,史書上也有相當豐富的秉公執法、大公無私的記載,但實踐中,普遍不大尊重法制,更不乏公然法外用刑者。而這和當事人是否讀律幾乎沒有什麽相關性。如宋代號稱重法慎罰,但據清代史學家趙翼統計,《宋史》中有七個地方官違法專殺的案例,其中六個涉及軍法,情況緊急,不妨便宜處之,“用重典以儆凶頑”,但第七個案例不過是一位繼子醉酒之後詈罵後母。而作出這一震驚宰相王安石決斷的主角舒亶,不過是一名剛剛踏入仕途的年輕小吏
(臨海尉)
。這也就難怪趙翼要批評宋代朝綱廢弛:“舒亶以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但此事並未影響舒亶仕途,反而讓其進入高層視野,官運亨通,後來更成為彈劾蘇軾的主要乾將之一。趙翼的統計限於死刑,如果將範圍擴大到一般違法處罰,則蘇軾亦在其中。
前文說過蘇軾重視法制,也熟悉法律,但蘇軾也認為,必要時可以法外用刑。他在元豐元年
(1078)
《徐州上皇帝書》中,引用漢代丞相王嘉“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的話,認為宋代亦“郡守之威權”太輕,表現之一就是“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認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他建議“京東多盜之郡”,“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並且“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蓄養爪牙”。
對此,蘇軾並非說說而已,而是切實付諸行動。在杭州知州任上,他曾經一年之內三次法外用刑。
其一是元祐四年
(1089)
七月,杭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帶領二百餘人到知州衙門鬧事。蘇軾調查後發現,此二人之父顏巽乃第一等豪戶,父子一向把持、操縱納絹事務,此次鬧事,就是針對蘇軾的納絹新政。本來州右司理院已“依法決訖”,但蘇軾認為,二人“以匹夫之微,令行於眾,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眾多之勢,脅製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決定“法外刺配”。判雲:“顏章、顏益家傅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製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刺配本州牢城,並上報朝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其二是元祐四年十一月,浙江災荒,社會不太穩定。蘇軾鑒於“浙中奸民結為群黨,興販私鹽,急則為盜”,擔心“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黨愈眾,或為深患”,請朝廷準許對於“應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群黨”,皆許“法外行遣”,等到情況好轉之後再恢復常態
(“候豐熟日依舊”)
。
其三是元祐四年十一月,福建商人徐戩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刻《華嚴經》並海舶載去交納,事畢又載五名高麗僧人來杭。蘇軾認為,“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將徐戩枷送左司理院查辦,並上書皇帝,“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後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
按照現代法理,在發生外敵入侵、社會動亂、重大自然災害等緊急狀態下,可以允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因此,蘇軾的上述觀點不可簡單地予以否定,而要具體分析。詳言之,蘇軾關於救災可以法外施仁的觀點應予以肯定,關於私鹽犯的法外用刑也可以接受,但法外刺配鬧事的顏章、顏益似無必要,因當時局勢和肇事者均已控制;法外懲處福建商人徐戩亦顯苛刻,其危害和影響似遠無蘇軾指稱的那樣嚴重,這只能從蘇軾本人的外交觀上去找原因了。事實上,“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很快就被蘇軾的政敵賈易等人抓住,作為攻擊他的一大罪狀。蘇軾被迫繼續外任。
元祐八年,蘇軾又因“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遭到台官彈劾
(“妄用潁州官錢”)
,但這次皇帝未予理睬。這大概也能反映世人的態度。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批評蘇軾違法的賈易本人則根本不學法律。賈易擔任常州司法入伍
(考上進士之後的第一個職位)
期間,“自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而史書亦讚美他“迄去,郡中稱平”。這樣一種對法律無用和無所謂的態度自不是個案和偶然,這或許就是限制中國古代法治和律學發展的民族心理基因。
總體來看,中國傳統社會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讀詩書更重要、更精深、更高尚,讀律則只是輔助性、工具性的,且格調不高。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後,社會上才逐漸重視法律,法學才逐漸成為熱門專業。至於真正把法律當一回事,尊重法治和人權,那更是後來的事情了。但中國古代士大夫關於讀律的重要性,以及讀律和讀書關係的論述,頗有獨到之處,對今天也有啟發。
(作者張群,系北京大學近代法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法學博士。原文標題為“也談’讀書萬卷不讀律’——兼及中國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觀”。文章選自《法史學刊·2019年卷·總第14卷》,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授權刊發。)
整合丨吳鑫
作者 | 張群
編輯丨徐悅東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