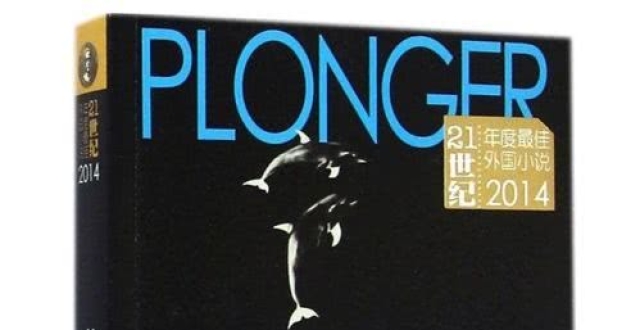12月28日,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因患癌症去世,終年79歲。阿摩司·奧茲於1939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父母為來自巴勒斯坦的移民。他的父親可以掌握多達16種語言,但在家中隻培養奧茲說希伯來語,以此增強其文化認同。長大後從事寫作的奧茲也就此成為以色列的代表性作家。奧茲12歲時,他患有憂鬱症的母親自殺,這件事情極大地觸動了奧茲,他的自傳性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曾描述過這些家庭生活。同名電影於2015年由娜塔莉·波特曼自導自演。
這部近六百頁的長篇小說把主要背景置於耶路撒冷,以娓娓動人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百餘年間一個猶太家族的歷史與民族敘事,抑或說家族故事與民族歷史。家庭與民族兩條線索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相互交織,既帶你走進一個猶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樂,又使你走近一個民族,窺見其得失榮辱。
今天,活字君特別推送阿摩司·奧茲為《愛與黑暗的故事》所撰寫的中文版前言。在前言中,從小向往中國文化的阿摩司·奧茲寫道:“中國和以色列位於亞洲大陸的兩端,代表著兩種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擁有許多共同之處,相互之間應該進一步加強了解。希望此書能夠對以色列人—中國人之間進行的一場深層次談話而盡一點綿薄之力。”
《愛與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
文 | 阿摩司·奧茲
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個詞形容我書中所有的故事,我會說:家庭。要是你允許我用兩個詞形容,我會說: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聽我用兩個以上的詞來形容,那就請你坐下來讀我的書。
在我看來,家庭是世界上最為奇怪的機構,在人類發明中最為神秘,最富喜劇色彩,最具悲劇成分,最為充滿悖論,最為矛盾,最為引人入勝,最令人為之辛酸。因此,我主要描寫單一的主題,不幸的家庭。
我寫《愛與黑暗的故事》以揭示一個謎: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麽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麽竟是如此怪誕的方程式,也許好和好相加等於壞?

我在《愛與黑暗的故事》裡沒有找到謎底。《愛與黑暗的故事》的讀者,若是你希望在讀過五百多頁之後發現究竟是誰犯下罪愆,那麽最好去讀別的書。
有些人撰寫回憶錄或自傳,開脫自己,證明自己的敵人有罪;或者證明作家本人一貫正確,其反對派永遠錯誤;或證明作家是一個出色的人,倘若他並不出色,便會歸咎於可怕的童年及其令人生厭的雙親,那麽無人可以期待從他那裡得到更多的東西。
這種痕跡,你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絲毫也找不到。我並非寫書向我的父母清算,也不是驅除我家庭和童年時代的惡魔。我來告訴你某些充滿悖論的東西:我的童年是悲劇性的——但一點也不悲慘;相反,我擁有一個豐富、迷人、令人滿足而又完美的童年,儘管為此我付出了高昂代價。
我並非寫書向父母告別。相反,當我覺得看見父母仿佛看見子女,看見祖父母仿佛看見孫兒孫女時才開始寫。確實,在家庭悲劇發生之際,我父母比我兩個女兒現在的年齡還要年輕。因此我可以以父母之父母的身份寫這部書,懷著憐憫、幽默、哀傷、諷刺,以及好奇、耐心和同情。
我寫此書把死人請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們,死者,則是客人。請坐。請喝杯咖啡。吃蛋糕嗎?也許吃片水果?我們必須交談。我們有許多話要說。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你們。

畢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一次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
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而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
我們在家裡隻談論怎樣看待巴爾乾戰爭,或當前耶路撒冷形勢,或莎士比亞和荷馬,或馬克思和叔本華,或壞了的門把手、洗衣機和毛巾。
那麽請坐下,親愛的死者,跟我說說以前你們從未向我說起的東西,我也會講述以前不敢向你們講述的東西。之後,我將把你們介紹給我的夫人和孩子,他們從來也沒有真正了解你們。如果他們和你們相互之間了解一些或許是件好事。而後你們結束來訪,將會離去。你們不會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來看看坐上一會兒,而後離去。
不,《愛與黑暗的故事》既非回憶錄,又非傳記,它是一個故事。比如,當我寫父母的臥室,寫我父母的父母,甚至父母、祖父母的臥室,我當然不能以研究為依據進行寫作。
我只能問詢我的基因和染色體:親愛的基因,請把死者的秘密告訴我。基因向我講述了一切,事無巨細——畢竟我的基因與他們的相同。
我的家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來到以色列。《愛與黑暗的故事》反映了他們在新家園的生活情形,同當時統治那片土地的英國人、同後來試圖毀滅以色列國的阿拉伯人抗爭。它並非一部黑白分明的小說,而是將喜劇與悲劇、歡樂與渴望、愛與黑暗結合在了一起。
他們對歐洲充滿失望的愛。如果要我們評判希伯來文學,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以色列全然充滿了渴望、創傷、侮辱、夢魘、歷史性的希望和單戀——單戀歐洲,或單戀東方,單戀聖經時代的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或小資產階級烏托邦。

阿摩司·奧茲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誠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倡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
我父親總是苦澀地打趣:三種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種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種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第三種就是我們,猶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人,也有南斯拉夫人——然後是我們,猶太人。
許多年過去後,我才理解在這連珠妙語的背後,隱藏著多少悲哀、痛苦、傷心和單戀。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五到六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隻教我希伯來語。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
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隻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歐洲,在那裡遭到歐洲人殺害。
整個童年,父母都在告訴我,我們的耶路撒冷成為真正城市的那一天將會來臨,不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而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理解,也不能理解,他們所說的“真正城市”是什麽意思。像我那樣的小孩不知道其他城市,即便特拉維夫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遙遠的童話。
而今,我理解了,家人所說的“真正城市”是指城中央有小河潺潺,各式小橋橫跨其上:巴洛克式小橋,或哥特式小橋,或新古典式小橋,或諾曼式的小橋或斯拉夫式的小橋。
我將告訴死去的人和活著的人,猶太人和歐洲人的對話尚未結束,萬萬不能結束。我們有許多東西要探討,我們確實有許多東西需要爭論。我們有理由痛心,有理由憤怒,但是更新我們和歐洲談話的那一刻已經來臨——並非在政治層面。
我們需要談論現在與未來,也應該深入談論過去,但有個嚴格條件:我們始終提醒自己我們不屬於過去,而是屬於未來。

莫言與阿摩司·奧茲
我非常高興能把這部作品奉獻給中國讀者。中國和以色列位於亞洲大陸的兩端,代表著兩種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擁有許多共同之處,相互之間應該進一步加強了解。希望此書能夠對以色列人—中國人之間進行的一場深層次談話而盡一點綿薄之力。
2007年6月19日於阿拉德
本文為譯林出版社出版《愛與黑暗的故事》中文版前言
end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