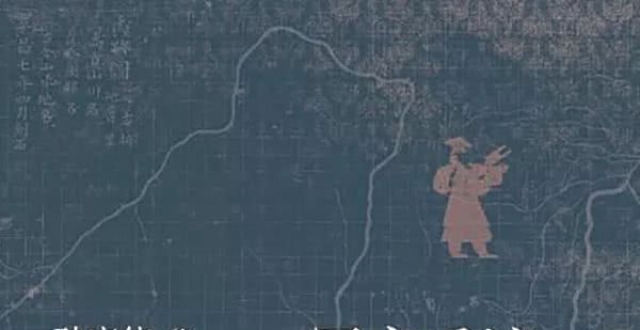王安憶的長篇新作《考工記》,像極了她那部膾炙人口的《長恨歌》,故被評論家們稱作“又一部低回慢轉的上海別傳”。

王安憶 著
花城出版社 2018-9
眾所周知,《考工記》乃春秋戰國時期的一部手工業技術文獻,記載各種工藝規範體系,體現了傳統文化對“工”的卓越理解。然而,王安憶在此巧妙借用同題,記敘上海“洋場小開”蛻變為普通勞動者的歷史過程,無疑具有別樣的意義。
縱觀王安憶的小說,她總愛以上海為舞台描摹這一類人,用她的話說,“跨越新舊兩朝的人,就像化蛹的蛾子,經歷著嬗變。新時代總是有生機,舊的呢,卻在坍塌,腐朽,迅速變成廢墟。”《長恨歌》裡是“上海小姐”王琦瑤,而在《考工記》中,則是“西廂四小開”之一的陳書玉。或許在王安憶看來,這類跨越新舊兩朝的人,最能呈現歷史縫隙裡的風流圖卷。
“上海的正史,隔著十萬八千里,是別人家的事,故事中的人,也渾然不覺。”作為歷史的監視者,一個“沒有面孔”的主人公,陳書玉總是消極被動地穿行在正史的夾縫之中。儘管小說不斷切入社會背景,令大歷史的面目影影綽綽,但個人的頹然與流散,始終是小說揮之不去的情感基調。
王安憶筆下的陳書玉,永遠有著不徐不疾的性子。他與世無爭,隨波逐流,或者說順其自然,卻有不幸中的萬幸。他生逢亂世,雖歷經坎坷卻有驚無險。六十年的時光,他安然度過。陳書玉的最大理想就是被遺忘,“最好被忘記,被時代忘記”。這也難怪,大歷史的“遺民”,終歸是那個“不合時宜的人”,“新規舊矩都失度,內心卑微得很”,只能做點抄經臨碑的事體。貼世界的邊縫,做時代的逃兵,不起眼,方才能夠歷經變遷而自我保全。
陳書玉的命運沉浮,不過是大歷史的小小浪花,驚不起一絲漣漪,卻是那個時代無數個體的縮影。正如王安憶在《跋》中所說的,“世事往往就是簡單,小說可不是,小說應該有另一種人生,在個體中隱喻著更多數。”
或許在王安憶看來,一切都是“散漫如流水的平常歲月”。故此,執著地做一名“大歷史的看客”,而將“物”推向前台,便是當然的選擇。就此而言,《考工記》的主人公與其說是小說中著墨最多的“西廂四小開”之一陳書玉,不如說恰是他那座“南市的老宅”,歷經時代風雨依然葆有“肅穆之靜美”的“煮書亭”。“這幢木結構的宅院,追究起來,哪裡是個源頭!榫頭對榫眼,梁和櫞,鬥和拱,板壁和板壁,縫對縫,咬合了幾百年,還在繼續咬合。”
事實上,這幢靜看人間數百年的舊宅,也最容易成為人們情感投注的對象。小說中,當時代風潮席卷而來時,奢侈的老宅自然是成分可疑的陳書玉的心頭之患。為了擺脫老宅,他謹小慎微,費盡心機。他主動將它出讓給街道辦瓶蓋廠,而自己則固守一方天地,過著隱士般曠日持久的孤寂生活。於此,“煮書亭”既是他的藏身之所,也是他永遠的牢籠,當然也成了他的宿命。“曾以為,是那宅子,和宅子裡的人拖累他,但大虞和朱朱的遭際卻讓他懷疑起來,分明感覺有一股更強大的力量暗中起著作用,就像水底深處的潛流,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終究,陳書玉和老宅相伴相生,一起接受修複和改造,如此延宕六十年。直到當年的“洋場小開”已然嬗變為普通退休教師,而年少時一起流連歡場的夥伴,也順理成章地在相濡以沫的患難中成為終生摯友。
據王安憶所言,《考工記》的寫作契機來自她漫長歲月中參觀房屋、聆聽歷史的偶然所得。一座老宅激起的心靈震蕩被她巧妙化用,凝聚到她所熟悉的上海“遺民”之上,以此勾畫舊年風物與歷史人倫的時代脈動。誠如她在小說後記中所交代的,“我將小說題作‘考工記’,顧名思義,圍繞著修葺房屋展開的故事。又以《考工記》官書的身份,反諷小說稗史的性質。”在她那裡,重要的固然是那個陳書玉,“這個人,在上世紀最為動蕩的中國社會,磨礪和修煉自身,使之納入穿越時間的空間,也許算得上一部小小的營造史。”
但舊樓的命運所折射的寓言意義,卻是更為關切的巨集旨。小說中的舊樓,最初作為精美絕倫的清代大宅,自有它的無限風光,而造化弄人,歷史的命運更多將它視為一件幸存的舊物,一個被拋棄的時代殘痕。經過兩百年的自然風雨和人間變局,舊樓依然屹立不倒,然而令人唏噓的是,當歷史的轉機終於到來,滿以為歷史的廢墟將重新複興時,它卻在偶然的利益纏鬥中頹敗下去,這便更能見出歷史風流雲散的宿命意義了。
正所謂:“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考工記》雖以上海為背景,卻並非為它的時代風貌賦形,而是要在這“上海別傳”之外,以陳書玉和老宅的遭際,將市民與房屋的世俗故事推向嚴肅的歷史大境界,進而共同詮釋所謂歷史的風流雲散。
文| 徐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