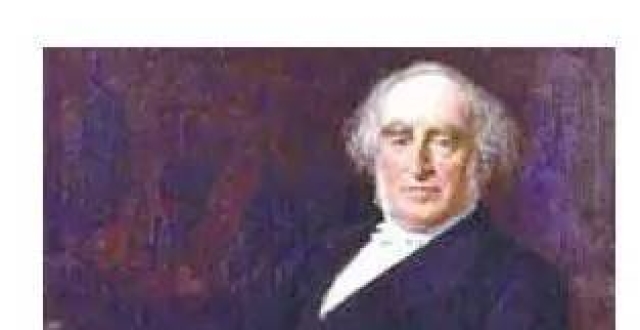本文來源:外國語
改革開放40年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發展紀實系列文章之三
2018年第5期
1977年10月4日,是我人生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是在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晚會三天之後,我們一行來自全國9所高校與來自外交部等多個部屬部門的24位年輕學子,晚上10點登上羅馬尼亞班機,由北京起飛途經卡拉奇,到布加勒斯特轉機後飛往目的地倫敦,開始了在當年無不令人向往的留學生涯。正是由於這個彌足珍貴的英倫留學之旅,讓我有機會從一開始,即跟隨祖國改革開放的跳動脈搏,見證及親歷著40年來我國翻譯研究領域的開放、傳承與演進。為此,我感到十分榮幸和自豪。
一
國門外的學術采擷與回歸
英倫留學三年,第一年在伊林高等教育學院(現名西倫敦大學)讀英國語言文學,第二年在中倫敦理工大學(現名西敏寺大學)讀英語語言學,第三年在埃克塞特大學專攻當時歸為應用語言學分支的翻譯研究。本人因自小受一位在外交部從事翻譯工作的近鄰的影響,十分向往翻譯工作,故而由高中畢業直接選送湖南師大英語專業就讀開始,就一直把主要興奮點落在了翻譯和翻譯功課的學習上。雖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未能如願成為專職翻譯工作者,卻也因為這個難得的留學機會,讓心中的翻譯夢開始以一種不同於原初的方式,慢慢地融入到了祖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譯學發展大潮之中。
記得那是1979年雪融春暖的三月,中倫敦理工大學現代語言學院的一場翻譯講座,由時任該院院長的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彼得·紐馬克教授主持,主講嘉賓為美國聖經公會翻譯部主管、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當時留學該校修讀語言學的我,無疑就成了聽課學生之一。雖然在國內大學所修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其中英語精讀課程包括了翻譯實踐的內容,另外學校間或也會提供一、二個翻譯講座,但實踐也好,講座也罷,當時在國內這類涉及翻譯的課程,都基本屬於翻譯實踐課的範疇,學的是某個句子、某段字詞是用直譯還是用意譯,此外可能還會提一提嚴複的信達雅,但談論最多的,似乎總是離不開直譯、意譯的問題。因此,那一次在中倫敦理工大學進行的翻譯講座,不僅成了我第一次聆聽到的奈達先生的講座,同時也是第一次聆聽到的、不同於此前在國內所能聽到的翻譯講座。當時,我作為中國留學生,從剛剛開始對外開放的土地而來,由於國內的長期封閉,對包括翻譯研究在內的國外學術發展動態,也包括早已名震海外的奈達本人及其譯學思想,自是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因而,奈達在台前所講的一切,基本上都是我以前不曾聽聞、不曾接觸過的,屬於全新的知識範圍而極富吸引力,再加上講者釋放出的那種談笑風生、睿智幽默氣質,使我倍感亢奮。正是那次非同一般的講座,將我帶入當代翻譯和譯學研究的海洋,使我進一步明確要在翻譯和翻譯研究的路線上向前走的決心,腦海裡也同時開始形成一個念想,要在學成回國之後,將在國門之外采擷到的異域譯學成果帶回祖國,介紹給當時資訊管道並不十分暢通的國內同行,為譯介、引進外來翻譯思想,現代化我們自己的翻譯研究,促進中外譯學交流,做些踏實的、個人綿薄之力所能及的工作。
於是,就有了本人1980年底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獲得國外碩士學位回國的人員之一,於1981至1991年間發表翻譯和翻譯研究作品20余種,其中包括1984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後獲香港商務印書館門市部1985年冬季10大暢銷書“榜首”稱號的《奈達論翻譯》;並有了1991年出版、2004年獲教育部推薦為“研究生教學用書”出版增訂版、至2016年止增訂版已7次重印的《西方翻譯簡史》和《翻譯學》(2000/2005)、《翻譯與翻譯研究概論——認知·視角·課題》(2012)、《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求索與發展》(2017),以及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後由譯林出版社多次再版的“BBC英國最偉大的100部小說”之一的《幸運的吉姆》譯著,等等。
值得特別追憶的往事之一,是本人對於奈達“翻譯科學”、“動態對等/功能對等”和“讀者反應”等三個概念的認知與譯介。這三個概念,是構成奈達翻譯思想的核心概念;是自本人對他的翻譯理論和思想譯介到中國以後,影響最大、引起爭議最多的外來翻譯思想之一;同時也是本人自1979第一次參加奈達講座起,至2004年與這位西方翻譯理論大師最後一次相見、相敘於羅馬國際會議止,我向他不下10次面對面請益和與之交談最多的翻譯理論話題,其中包括1983年他到訪北京外國語大學期間,邀約本人赴北外聽他第二次來華講座期間與他的討論;1985年他及奈達夫人到訪南京大學和南京金陵神學院期間,邀約本人在其演講之餘與他的交談;以及他先後三次到訪本人所在學校及寒舍與本人較長時間的交談與交流。
當然,在相隔30、40年之後的今天,在英文以外的華文地區,奈達的翻譯思想和他思想中的這些概念,都早已為人耳熟能詳,本文無意、也不適宜在此針對這些概念引發的各種爭議展開討論。但我願在此指出,特別就奈達所提“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翻譯科學)之說而言,不論是否認同它的意涵,或是否同意將“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這一英文表述譯為“翻譯科學”,我們都不能不回歸到奈達本人所表述的基本立場上,即奈達認為:翻譯具有多面性,它既為藝術、技術,也是科學;因此有時他在與本人的直接對話中,還語帶玩笑且不無欣賞地說:不少人甚至把他稱作“father of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譯科學之父)。需要再三指出的是,當我們在肯定或讚揚奈達的理論時,我們需要意識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不要盲從;而當我們在批評它的局限或不足時,卻又不能妄加指責,把那些本來合理的部分也否定掉。尤其是,有些人在後“言必稱奈達”時期,常常對奈達的一些核心理論橫加批評,甚者徹底否定,如對上面提到的他的“動態對等/功能對等論”和“讀者反應對等論”,可是又不拿出或拿不出可以用來替代的更好的理論和思想。這是我們在接受或者不接受外來翻譯思想抑或本國傳統翻譯思想時,所必須認真思索的。

譚載喜1978年於倫敦(留英時期)
二
改革開放成就了翻譯學在中國的發展
從上面敘述到的本人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以來的個人學術軌跡不難看出,沒有祖國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自己的英倫留學和隨後的回國貢獻。從巨集大層面看,沒有了改革開放,也就不會有今日中國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其中無疑也包括了中國翻譯研究領域的光輝成就。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祖國的全方位改革開放,才成就了1980年代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在中國的發生,以及在今天的持續演進和發展。
回顧這40年,中國翻譯研究的發展速度之快,規模之廣,成果之豐,都是以往任何時期不能比擬的。當代中國翻譯研究作為獨立學科自主發展的這個重要階段,其起始時間可以說有三個互相聯繫的標誌:一是,從純粹的時間層面看,它始於1980年。這一年,作為《中國翻譯》雜誌前身的《翻譯通訊》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編輯、出版和發行。雖然建國後曾經有過1950年創刊、1952年休刊、1953年複刊、1954年最終停刊的《翻譯通報》,1980年面世的《翻譯通訊》或許僅能視作《翻譯通報》在“休眠”半個多世紀後的延續,但畢竟名稱與編輯方針、出版政策及主管屬性乃至期刊內容都發生了變化,因此應當說這是一個嶄新開端,當下持久閃亮的中國翻譯研究之光,正是由1980年發行的這份《翻譯通訊》才真正開始點燃的。二是,從專業發展的層面看,當代中國譯學較大發展的起始年是1983年,因為這一年,《翻譯通訊》移交給中國譯協作為該會會刊,並於1986年改名為現在的《中國翻譯》,這標誌著在組織結構上中國的翻譯和翻譯理論工作者自此有了自己研討翻譯問題的專業和理論園地。三是,從理論研究的層面看,中國翻譯學的較大發展,是以1987年首屆全國翻譯理論研討會召開為起始標誌的。記得當年會議主要由《中國翻譯》編輯部的羅進德、高峰等人籌備,7月在青島舉行,本人有幸應邀與劉宓慶先生及其他幾位學界前輩與同仁,分別在會議第一天作大會發言,本人圍繞“關於建立翻譯學”的主題,闡述把翻譯學作為獨立科學學科發展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問題,相關發言內容先後在《中國翻譯》(1987年第3期)與《外國語》(1988年第3期)刊出。劉宓慶先生的發言內容,則主要涉及翻譯研究的中國特色以及如何展開翻譯研究的問題。與此同時,本人還在《外語教學與研究》(1987)、《湖南師范大學學報》(1987)等刊連續發文,就翻譯學的性質、內容、任務和研究途徑、方法等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自此,與翻譯學相關的種種問題即擺在了國內翻譯研究者們的面前,先後引起爭議,這些問題包括翻譯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要不要建立(或發展)翻譯學的問題,翻譯學的學科性質問題,翻譯學的中國特色問題,要不要引進以及如何引進、如何看待外來(特別是西方)翻譯理論的問題,等等。
在某種意義上,本人於1987 至1988 年間的上述會議發言和期刊文章,是繼董秋斯1950 年代初提出翻譯理論建設的主張之後,代表著再次有人旗幟鮮明地提出建立翻譯學的思想。雖然把翻譯研究作為獨立學科來建立的構想,西方學者霍姆斯1970 年代早期在其論文《翻譯學的名稱與性質》中已有所闡發,但我們需要特別指出,霍姆斯在1972年丹麥哥本哈根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宣讀的相關論文中,儘管討論了把“翻譯研究”作為獨立學科來發展的問題,但正如芒迪所指出,該文發表之初其實鮮為人知。一直到霍姆斯1986 年逝世兩年後,其紀念文集《譯稿殺青!文學翻譯與翻譯研究文集》將該文收入其中於1988 年正式出版,文章的影響才開始逐漸顯現出來。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本人在《必須建立翻譯學》(1987)一文回顧中外翻譯研究發展的問題時,未能研讀並觸及霍姆斯有關發展翻譯研究為獨立學科的主張。故此,不論如何,我們1980年代於國內再次提出“必須建立翻譯學”,這不僅順應了翻譯研究發展的歷史潮流,同時對我國新時期譯學研究的興起和譯學思想的喚醒與發展,可以說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誠如巴斯內特與勒菲弗爾在評述翻譯研究學科發展歷程時所指出,翻譯研究是在20 世紀80年代發展而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西方譯學發展如此,中國譯學發展也同樣如此。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國家全方位改革開放的發展而成就的,也是我們在審視譯學發展的過往成就與未來方向時,或可引以為豪的。
三
向世界敞開懷抱的中華譯苑
回首1980年代以來中國譯學作為獨立以至獨立自主學科的發展歷程,可從多個方面總結我們的發展成績。我們先來談談對外國(尤其是西方和蘇聯)當代翻譯理論和思想的引進和學習,其規模之大,足可視為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翻譯研究發展至今的一大特色,或曰我國當代譯學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成績。從最早於《翻譯通訊》1980年第3期發表的一凡的譯介文章《西方的文學翻譯》,到1983年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個外國翻譯理論文集《外國翻譯理論評介文集》,再到隨後陸續翻譯或編譯出版的各種外國翻譯理論單行本,包括《奈達論翻譯》(譚載喜編譯,1984)、巴爾胡達羅夫的《語言與翻譯》(蔡毅、虞傑、段京華編譯,1985)、斯坦納的《通天塔: 文學翻譯理論與硏究》(莊繹傳編譯,1987)、加切奇拉澤的《文藝翻譯與文學交流》(蔡毅、虞傑編譯,1987)、讓·德利爾的《翻譯理論與翻譯教學法》(孫慧雙譯,1988)、卡特福德的《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穆雷譯,1991)等,再到後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等多家出版社購買外國版權、以外國翻譯研究叢書形式在國內再版發行的60多部外國翻譯理論英文作品——無論是通過翻譯、編譯、評介或是直接引進印行來自國外(尤其是西方)的翻譯理論成果,所有這一切,對於更新我們的學術思維,推動國內翻譯學學科的建立、建設與發展,無疑都發生了正面的、積極的影響。
即使是對於那些較為排斥外國翻譯理論的翻譯學者,大規模外來翻譯理論和思想的引進,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也讓他們意識到,在翻譯研究的問題上,原來還可以存在許許多多不同於中國傳統的理論範式和思想方法。由此,我們關於翻譯的理論意識覺醒了,並且穩步向上提升了。廣大翻譯工作者,尤其是翻譯研究工作者,都逐步認識到了翻譯是一種有規律可循、有方法可用、有理論和原則可依的人文科學學科。對於這個事實的認知和理解,我們當然要感謝翻譯領域理論前輩們的思想貢獻。從古時支謙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飾”,到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到玄奘的“既需求真,又須喻俗”,到彥琮縱論譯者專業要求和人格操守的翻譯“十條”“八備”,再到現當代嚴複的“信達雅”、魯迅“寧信而不順”的“異化”觀,以及傅雷“神似”和錢鍾書“化境”等翻譯的“歸化”主張,正是有了這些開拓性的翻譯思想,以及當代學人對前輩思想所進行的耙梳整理(如羅新璋、馬祖毅、劉靖之等人作出的努力),才使得我們在理論意識的覺醒和提升上有所本。另一方面,我們也無可諱言地應當感謝外來(主要是西方和蘇聯)的翻譯理論和思想。不論我們接受與否,這些非我族類的“異域”元素、“異邦”思想和理論,至少是呈現出了一個與我不同的參照系,向我們提供了理論化翻譯的不同範式和途徑,從而觸發國人對於翻譯迷思的不同於以往的、較深層次的思考。雖然對外來翻譯理論和思想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全盤照搬,但它們當中許多對我們有益的成分,卻是我們不應當拒之門外的。
過去40年我們國家的翻譯理論發展證明,來自異域的翻譯理論和思想方法給我們研究提供的正能量,遠遠超出了同時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雖然,此種翻譯理論中的西學東漸,而非東學西漸,其中不無反映著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的現實影響,但暫且撇開 “權力關係”或“強權政治”的因素不說,當我們發現“他山石頭多又多”,又為何“不可為玉順琢磨”呢?應該說,形形色色諸如“源文本”“目標文本”“翻譯對等”“功能對等”“讀者反應”“文本接受”“文化轉向”等等外來譯學語匯、思想和概念在當代中國譯學領域的出現,恰恰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來翻譯理論和思想的影響,可以是一種正面影響,它拓寬了我們的譯學視野,帶動了我們對於翻譯問題的創新思考,在較短的時間裡促成了中國翻譯研究的現代化,並推動了我國翻譯學的持續向前發展,因此值得我們充分肯定。
四
本土譯學研究的斐然成績
中國譯學發展的第二個重要成績,是譯學著作和文章以前所未見的規模發表,逐步顯現出本土譯學研究的強有力發展後勁。40年來,除了上述大量譯介和引進外國翻譯理論作品的出版活動外,更多的當然是成千上萬篇非譯介性質的本土譯學成果的發表。每年,各類討論翻譯實踐或理論的文章,不僅見諸於國內主要翻譯研究專刊,如前面已經提到過的《翻譯通訊》及其後來更名的《中國翻譯》,以及《中國科技翻譯》(1988年創刊)、《上海翻譯》(原名《上海科技翻譯》(1986年創刊,2005年改現名)、《語言與翻譯》(1985年創刊)、《東方翻譯》(2009年創刊)等,而且也大量發表於其他外語及語言研究、語言學、比較文學雜誌,以及不少大學學報,其中主要包括《外語教學與研究》(1957年創刊,1966—1977年停刊,1977年複刊)、《外國語》(1978年創刊)、《當代語言學》(原初於1962年作為《中國語文》[1953年創辦]副刊的《語言學數據》發行,1966—1978年停刊,1978年以《語言學動態》之名複刊,1980年更名為《國外語言學》,2000年起再改為現名)、《外語與外語教學》(1979年創刊)、《外語學刊》(原名《黑龍江大學學報[外語版]》,1978年創刊,2000年改現名)、《中國比較文學》(1984年創刊)、《外語研究》(1984年創刊,原名《南外學報》,1987年改現名)、《外語與翻譯》(原《長沙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創刊,2014年獲審批改現名)、《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1980年創刊)、《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78年創刊)、《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1993年創刊),等等。
這裡,還必須特別提一提台灣與香港地區的幾份較有影響的譯學刊物:一是台灣的《編譯論叢》(2008年創刊),二是香港的《翻譯季刊》(1995年創刊)與《翻譯學報》(1997創刊)。這些刊物嚴格按照國際期刊慣例運作,發表了不少較高品質的譯學文章,為中華語境下的翻譯研究發展,同樣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另一方面,40年來出版的各類譯學書籍也不在少數,包括譯學專著、文集、會議論文、譯學詞典、譯學百科、翻譯教材,以及成百上千的譯學碩博學位論文等。據許鈞等提供的數據,在1979至2008的30年間,正式出版的翻譯研究書籍總共有1,600多種,其中大部分發表在1990年以後的時間裡。以各類譯學書籍的分布比例計算,翻譯教材或教學用書最多,佔總數的52%;其次是譯學論文集,佔13%;再次是翻譯技巧書或翻譯手冊,佔10%;然後是翻譯理論作品,佔9%;剩餘部分是翻譯歷史、辭書等工具類書籍。如果我們按此情況推算,並考慮到2008年以來中國譯學發展的步伐比以前更為進取,那麽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中國譯學領域迄今出版的書籍作品應已兩倍或接近兩倍於上述許鈞等所提供的數字。
當然,量多不一定就是質高。在眾多已經出版的譯學作品中,例如一些翻譯教程,其中有不少在內容上存在彼此雷同的弊端,有些討論翻譯問題的專著其實也都老生常談,缺乏創意。但無論如何,譯學作品的大量形成和出版,而且持續不斷,這一基本事實無可否認地從一個側面說明:翻譯研究在中國正以獨立或獨立自主學科的身份,穩步而蓬勃地向前演進著。
五
值得點讚的中國翻譯教育及其他
當代中國譯學發展的另一個主要方面,是在翻譯教學和翻譯學位教育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我們知道,在翻譯學作為獨立直至獨立自主學科的發展過程中,譯學人才的培養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沒有了譯學人才以及譯學後繼人才的出現,就沒有了譯學的持續發展,就沒有了譯學發展的未來。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知,並同時依靠著國家對於整個教育事業的重視,40年來我國翻譯教學和教育的發展可以用“突飛猛進”這幾個字來形容。我曾經發文指出,與西方相關領域相比,我們表現出了後來居上的強勁勢頭。例如,最近十多年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形勢的逐漸逆轉,西方各國開辦翻譯學系和翻譯人才培養的規模不僅未能大步發展,在某些方面(如翻譯學本科與碩、博學位教育方面)反而不斷退步或者停滯不前;相較之下,我國發展卻一直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景象。以研究生階段的翻譯專業性人才培養為例:據“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準)考試網”報導,自2007年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設定翻譯碩士專業學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簡稱MTI)以來,獲準開辦翻譯碩士專業的大學從2007年的15所,增加到了2016年的215 所,在校學生約 20,000 人;開辦本科翻譯專業(BTI)的大學,也由2006年僅3所增加到了2016年的230 所。另據許鈞等2009年寫的一個調查,全國約有1,200所高校開設外語專業,其中大多教授翻譯課,約20個博士點設有翻譯學方向,還有20所高校有研究型翻譯碩士學位點,而這些數字均不包括上述提供MTI和BTI教育的學校以及各種暑期班、業餘學校所定期或不定期提供的口筆譯培訓在內。
正如筆者曾經所指出的,雖然我們的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和翻譯學博士學位教育的發展速度、規模有時過於“神速”而難免不給人有些“盲動”的感覺,因而需要我們認真反思並進行適時有效的調整和修正,但不可否認的是,面對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在翻譯學位教育領域所顯露出的種種“疲態”,我們的發展卻表現出不斷向前的趨勢,這是令人鼓舞的。
當然,中國譯學的發展成績並不限於以上各節所述。不同的人,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理解,也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總結出不一樣的、數量上更多的成績。例如,近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語言與翻譯服務也以越來越產業化的姿態貢獻其中,因此我們似乎或可將語言與翻譯服務的產業化視作一大成就。此外,隨著現代科技,尤其是現代電子、網絡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進步,機器翻譯(包括網絡電子翻譯和同步語音翻譯機)不斷更新換代,我們也因此可把機器翻譯/電子翻譯/人機互補翻譯的進步總結為翻譯領域的主要成績,甚或是某種意義上的最大成績。但本文囿於所能使用的篇幅,無法過多拓展。而從翻譯研究的核心角度來看,以上各節所談之種種主要成就,應該說是對我國當代譯學發展狀態的恰當概括。
六
結語
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翻譯研究走過了40年。在這40年中,我們從大規模學習、引進外來(尤其是西方)的譯學理論,到挖掘中華翻譯傳統,到積極參與國際譯學對話、發展帶有自己文化特色的當代中國譯學話語,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發展至今,就總體而言,我們的翻譯研究尚談不上已完全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在不少方面,尤其在譯學思想和理論認知的廣度、深度和創新度方面,我們與別人的差距仍然存在,或者說我們的發展空間仍然很大。這是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必須銘記於心的。
在今後的譯學發展中,我們的翻譯理論傳統和思想主張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參與世界的平等對話乃至躋身世界最先進的譯學理論行列,除了對中國譯學發展中的不足進行反思外,更重要的是應結合反思,來探索和開辟未來發展的路徑。在探索過程中,我們需要處理好各個層面的關係,包括理論引進與理論自創的關係、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自然智能與人工智能、人工翻譯與機器翻譯、傳統理念與現代科技的關係等等。即是說,我們在未來的譯學發展中,應當盡量在繼承傳統思想與立足當下研究之間、在弘揚民族特點與尊重翻譯普遍性特徵之間、在引進外來翻譯思想與開發本土理論資源之間、在理論源於實踐與實踐升華出理論的認知之間取得平衡。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在認識上取得了這些平衡,我們的翻譯研究就能得到持續發展,就能有更加廣闊的前途。

深圳大學特聘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兼),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哲學與理論、西方翻譯史論、翻譯的文化政治學研究、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中英語言文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