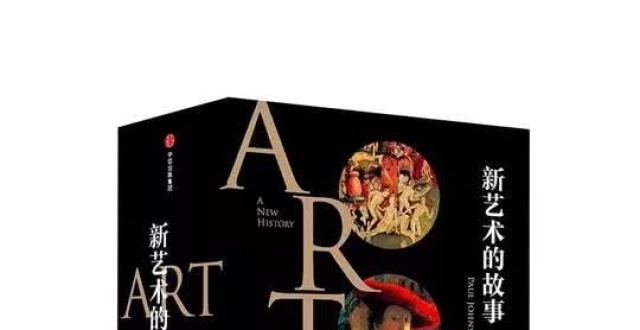何以會有被稱作風格的東西?
被肯尼思?克拉克描述為“我所讀過的最才華橫溢的藝術批評著作之一”的《藝術與錯覺》,是一部有關製像的經典研究。它試圖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何以會有被稱作風格的東西?這個問題也許簡單,卻很難回答。貢布裡希教授對圖畫再現的心理學及歷史的探索,充滿睿智而包羅萬象,從而引領他進入許多重要領域。在說明肖像製作遠比它看起來要困難這一問題的過程中,貢布裡希對許多新老看法作出了考證、質疑與再評價,那些新老觀點包括模仿自然、傳統的功能、抽象問題、透視的有效性,以及對表現的解釋。
《心理學和風格之謎》一文為貢布裡希文集《藝術與錯覺》導論中的前兩節。
著者:[英]E. H.貢布裡希
翻譯: 楊成凱 李本正 范景中
校譯: 邵巨集
書籍由廣西美術出版社出版。
本文已獲授權。
配圖:埃舍爾(Maurits Cornelis Escher)作品(除標注外)。
文章如下:

貢布裡希
藝術是心靈之事,所以任何一項科學性的藝術研究必然屬於心理學範疇。它可能涉及其他領域,但是,屬於心理學範疇則永遠不會更改。
——馬克思· J·弗裡德倫德爾《論藝術和鑒賞》
[Max J.Friendl?nder,Von Kunst und Kennerschaf t ]
一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幅插圖一目了然地揭示了“風格之謎”[riddle of style]一語在這裡有何含義,它比我講話說明要迅速得多。阿蘭[Alain]這幅漫畫明確地總結出一直縈回在若乾世代藝術史家心頭的一個問題。不同時代、不同的國家再現可見世界[visible world]時,為什麽使用了這樣一些不同的方式?我們認為逼真的繪畫在後代人看來會不會變得難以令人信服,就像埃及的繪畫在我們眼中一樣?一切與藝術有關的事物是否純屬主觀,或者說,藝術問題有無客觀標準?如果說有客觀標準,如果說採用今天在人體寫生課上教授的那些方法可以完成更為忠實的模仿自然的作品, 不是埃及人採用的那些程式所能比擬的,那麽為什麽埃及人當年沒有採用我們的方法呢?是否有可能像我們這位漫畫家所暗示的那樣,在埃及人的知覺中,大自然另具有一副面貌呢?這樣一種藝術視覺變異性[variability of artistic vision],也能幫助我們說明當代藝術家創造的那些令人莫名其妙的影像來自何處,難道事實不是如此嗎?

這些問題關係到藝術的歷史。但是,僅憑歷史學方法無法尋求問題的答案。把已往發生的一些變化描寫出來,藝術史家也就功成業就。他專心於研究藝術流派之間的風格差異,他也改進了描述方法,以便對流傳至今的往昔藝術品進行分類、編排和鑒定。把本書所載的多種多樣的插圖瀏覽一遍,我們或多或少地都會有藝術史家在研究工作中的反應: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幅畫的主題,而且還連同著它的風格;我們看見這裡有一幅中國風景畫,那裡有一幅荷蘭風景畫,這裡有一個希臘頭像,那裡有一個17世紀的肖像。我們已經把這樣一些類別看成天經地義,幾乎不再去問為什麽分辨一棵樹是中國藝術家畫的還是荷蘭藝術家畫的竟是如此容易。如果說藝術不過是,或主要是個人視覺的一種表現,那就不可能有什麽藝術史。我們就毫無理由像現在一樣, 認為凡是在相距不遠的地方畫出的樹木必然是一家眷屬,相似乃爾。我們就無法指望阿蘭畫的人體寫生課中的男孩子們會畫出一個典型的埃及式的形象。我們也就更不能希冀鑒定一個埃及式人物確屬3000年前之作,還是昨天偽造的贗品。藝術史家這一行業奠基於海因裡希·沃爾夫林[Heinrich W?lfflin]總結出的一個信念,即,“各個時期皆有其所不能為”。闡述這個奇怪的現象不是藝術史家的義務,那麽又是誰的責任呢?

二
過去有一個時期,關心藝術再現的方法是藝術批評家的本分。那時,藝術批評家是那樣習慣於首先以藝術再現是否準確來評價當代作品,他們毫不懷疑再現技術已經從簡陋的草創階段發展起來,達到了完美地呈現錯覺的地步。當年埃及的藝術採用幼稚的方法,因為埃及藝術家的見識不過如此。埃及藝術家的程式大概是不無道理的, 但是不能被完全認可。我們今天已經擺脫了這種美學觀點,這是20世紀前半期席卷歐洲的那場偉大藝術革命取得的不朽成就之一。藝術欣賞課的教師通常要設法糾正的第一個偏見,就是認為藝術的高超在於它跟照相一樣毫發不爽。風景明信片或海報女郎已經成為慣用的陪襯,學生們以它們作對比,學會怎樣看出藝術大師的創造性的成就。換句話說,美學理論已經放棄原來的主張,不再注重逼真的藝術再現這個問題, 即藝術中的錯覺問題。這在某些方面的確是個解放,誰也不想恢復從前的混亂狀態。但是,由於藝術史家和藝術批評家都不想為這個持續多年的問題花費心力,它也就變得無依無靠,無人重視了。於是,逐漸滋生了一種印象,認為錯覺問題既然跟藝術沒有什麽關係,在心理學上必然也很簡單。

我們無須求助於藝術就能說明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任何一本心理學教材都能給我們一些棘手的例證,說明所涉問題的複雜性。且看幽默周刊《飛葉》[Die Fliegenden Bl?tter ]登載的這幅簡單的特技畫[trick drawing](下圖),

兔還是鴨?
它已進入哲學討論之中。我們既能把這張畫看成兔子,又能看成鴨子。懂得這兩種讀解[reading]並不困難。描述一下我們從一種解釋[interpretation]轉換到另一種解釋時發生什麽變化,就不那麽容易了。顯然我們並沒有那種錯覺,以為自己面對一隻“真的”鴨子或兔子。紙上畫的這個形狀跟那兩種動物中的哪一種都不大像。然而在鴨子的嘴變成兔子耳朵時,毫無疑問這個形狀發生了一種微妙的變形,而且把在此以前被忽視的一個部位加以突出,成為兔子的嘴。我說它是“被忽視”[neglected], 然而在我們又轉回“鴨子”這種讀解時,我們能否繼續說它被忽視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看“那裡實際”是什麽東西,不得不拋開它的解釋只看它的形狀,我們很快就會發現這一點實際上無法兌現。的確,我們能越來越快地從一種讀解轉向另一種讀解,我們在看到鴨子時,也還會“記得”那隻兔子,可是我們對自己觀察得越仔細,就越會發現我們不能同時感受兩種更替的讀解。我們將看到錯覺難以描述,難以分析。因為,雖然我們的頭腦可能意識到任何一種特定的感受必定是個錯覺,可是嚴格地講,我們不可能觀察自己怎樣體驗一個錯覺。

如果讀者感到這個斷言有些難以理解,那麽總有一件產生錯覺的工具近在身邊可以驗證這個斷言:浴室的鏡子。我指定的是浴室,因為我讓讀者去做的實驗以在鏡子蒙上一些蒸汽時效果為最好。在鏡面上描摹出自己的頭部輪廓,再把頭部輪廓線圈住的地方擦乾淨,這是體驗錯覺主義再現的一項引人入勝的練習。因為等到我們把這一切真正乾完以後,我們才明白鏡面上那個影像是如何之小,而它給我們的錯覺卻是“面對面地”看到了我們自己。準確地講,它必定恰恰是我們頭部一半大小。我不想以這個事實的幾何證明來干擾讀者,不過本質上也很簡單:因為鏡子總是出現在我和我的映像正中間,所以鏡面上的大小就是形式大小[apparent size]的一半。然而無論這個事實用相似三角形來證明是如何無可置辯,人們總是對這個斷言有明顯的懷疑。儘管有幾何學證明,我也要固執地認為我在刮臉時實際看見了我的頭(本來大小), 而鏡面上頭的大小卻是虛像。三者不可兼得,我不能在使用錯覺時去觀察錯覺。

藝術作品不是鏡子,然而它們跟鏡子一樣,都有那種令人捉摸不定難以言傳的變形魔術。善於內省的學者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最近極其生動地給我們描述,當他試圖“追蹤”[stalk]一個錯覺時,連他都是如何遭到了失敗。望著委拉斯開茲[Velázquez]的一幅傑作,他想觀察一下在他後退過程畫面上顏料的點點畫畫變形為一幅理想化的現實景象時,會出現什麽情況。但是,無論他怎樣進進退退地嘗試,也不能同時看到兩個景象,因而事情是怎樣發生的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始終在跟他捉迷藏。在肯尼思·克拉克這個例子中,美學問題和心理學是微妙地交織在一起的;在心理學教材中出現的例子,情況顯然做不到這一點。我在本書中經常發現,還是把對視覺效果的分析跟對藝術作品的分析分開為宜。我知道這樣做有時會使人感到對藝術作品不夠恭敬,我希望讀者意識到事實恰恰相反。
再現不一定都是藝術,然而其神秘性卻不會因為它不是藝術而減弱。我記得很清楚,最初讓我看到製像[image making]的威力和魔術的倒不是委拉斯開茲,而是在我初級讀本中發現的一個簡單的畫圖遊戲。書中有一節小詩告訴你怎樣首先畫一個圓圈再現一個麵包(因為在我的故鄉維也納的麵包是圓的),上頭再畫上一條曲線就使得麵包變成一個購物袋,在它的提手上加上兩條小曲線就會使它縮成一個錢包,這時再添上一條尾巴,就出現了一隻貓(下圖)。

怎樣畫一隻貓
我在學這個訣竅時,感到好奇的是變形[metamorphosis]的威力:那條尾巴破壞了錢包形象而產生了貓;你不把錢包的印象抹掉就看不見貓。既然我們遠未完全理解這一過程,又怎麽能指望探討委拉斯開茲的作品呢?
我在開始探索這個問題時,幾乎未曾想到錯覺這個課題竟會把我引入如此遙遠的領域。我只能請求有這項蛇鯊之狩[Hunting of the Snark]活動的讀者在這自我觀察[self-observation]遊戲中經受一些鍛煉,倒不是去博物館,更多的還是在日常接觸種種圖畫和影像的場合中——坐在公共汽車上或者站在候車室裡。他在那裡看東西顯然不會算作藝術。它不像那些追模委拉斯開茲手法的低劣藝術作品那麽矯揉造作,卻也不那麽令人困惑。

當我們研究那些身兼偉大的藝術家和偉大的“錯覺主義者”[illusionist]的往昔藝術大家時,藝術研究和錯覺研究就不可能處處涇渭分明。因此,我更加渴望盡我所能,明確地指出本書的用意並不是或明或暗地主張在今天的繪畫中使用錯覺主義手法。我之所以要防止在我跟我的讀者和批評家的交流中產生這種誤會,在於事實上我對非具象藝術[nonfigurative art]的某些理論抱以謹慎態度,而且在相關的地方會略 為提及其中的一些問題。然而以此為對象就要背離本書的主旨。我絕不會否認,曾被已往藝術家引為殊榮的再現技術的種種發現和效果今天已經變得微不足道。可是我認為,如果我們接受時下的思想,認為這些問題從來與藝術無關,那麽我們就面臨著跟過去的偉大藝術家失去聯繫的現實危險。大自然的再現何以在今天可以看作有些陳腐,這個緣故應該是藝術史家最應該值得注意的。已往任何時代也不像我們今天這樣,視覺影像的價值竟如此的低廉。招貼畫和廣告畫,連環畫和雜誌插圖,把我們團團圍住,紛至遝來。通過電視螢幕和電影,通過郵票和食品包裝,現實世界的種種面貌被再現在我們眼前。繪畫在學校裡教授,也在家裡演習,或者作為一種療法,或者作為一種消遣之計;許多普通的業餘愛好者也掌握了一些技法,那些技法會被喬托[Giotto]驚歎為地地道道的魔法。大概連我們在早餐穀物盒子上看到的那些粗糙的彩圖,也會讓喬托那個時代的人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從此得出結論,認為那些穀物盒子比喬托的畫高明。我不是那種人,但是,我認為再現技術的成功和庸俗化向藝術史家和藝術批評家兩方面提出了一個問題。

希臘人曾說知識始於驚奇。我們不再驚奇,也許就有知識停止進展的危險。我在本書各章中,自定的主要目標是恢復我們的驚奇感,再次為人類竟能用形、線、影、色呈現那些被我們稱為“圖畫”[picture]的視覺現實的神秘幻象而感到驚奇。柏拉圖[Plato]在《智者篇》[Sophist ]中說:“難道我們就不應該說以建築藝術製作一所房屋,而以繪畫藝術製作另一所房屋,一種為清醒者而製造的人工幻夢嗎?”我不知道還有什麽比它更好的描寫方法能再次教會我們怎樣感到驚奇;當然有許多為清醒者而製造的人工幻夢已被我們排斥在藝術王國之外——這也許不無道理,因為我們稱之為美女照片也好,稱之為連環漫畫也好,它們都是過於有效,幾乎難以作為夢的替代物——但是這個事實絲毫無損於柏拉圖的藝術定義的價值。如果從恰當的觀點看,甚至美女海報和連環漫畫也可以發人深省。正如對散文的語言沒有認識,詩學研究終有欠缺一樣,我認為藝術研究也會由於探索視覺影像[visual image]的語言學而日益得到豐富完善。我們已經看到影像學[iconology]的要點,它研究影像有寓意[allegory]和象徵[symbolism]用法中的功能,研究它們跟可稱為“不可見的觀念世界”[invisible world of ideas]的指稱作用。藝術的語言對可見世界[visible world]的指稱方式既是那麽明顯,又是那麽神秘,迄今仍有許多奧秘,除能像我們運用語言一樣熟練地運用它——無須通曉它的語法學和語義學——的藝術家自己外,無人知曉。

在藝術家和藝術教師為學生和業餘愛好者編寫的許許多多書籍中,蘊藏著大量的實踐知識。我本身不是藝術家,所以我已避免超出論證的需要而過多地涉及這些技術問題。但是,如果本書各章能被看作是為了在藝術史領域和職業藝術家領域之間架起急需的橋梁而建的臨時橋墩的話,我就會感到愉快。我們想在阿蘭的人體寫生課上相會,以我們甚至——如果幸運的話——知覺科學研究者都能理解的語言去討論那些男孩子們的問題。
(本文僅為《藝術與錯覺》導論的一部分,完整內容請研讀書籍,文末有購買鏈接)

關於作者
恩斯特·貢布裡希教授爵士,功勳團成員(O.M),高級英帝國勳爵士(C.B.E)。1909年生於維也納,1936年進入倫敦的瓦爾堡研究院任教職。從1959年起,擔任倫敦大學古典傳統歷史教授及院長,直至1976年退休。
主要著作有《藝術的故事》(第16版,1995年),《藝術與錯覺——圖畫再現的心理學研究》(第6版,2002年),《秩序感——裝飾藝術的心理學研究》(1979年)。還出版有論文集,“文藝複興藝術研究”四卷,第一卷《規範與形式》(1966年)、第二卷《象徵的影像——貢布裡希影像學文集》(1972年)、第三卷《阿佩萊斯的遺產》(1976年)、第四卷《老大師新解》(1986年),《木馬沉思錄——藝術理論文集》(1963年),《影像與眼睛——圖畫再現心理學的再研究》(1982年),《敬獻集——對我們文化傳統的讀解》(1984年),《我們時代的話題——20世紀的藝術與學術問題》(1991年),以及《藝術史反思錄》(1987年),《偏愛原始性——西方美術和文論交匯的趣味史》(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