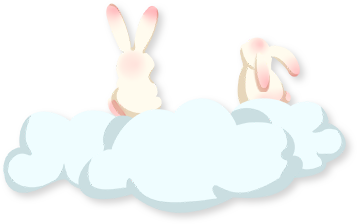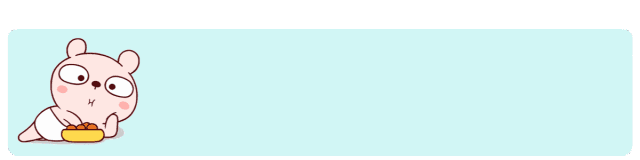人類生來對死亡既害怕又好奇,後來有一群人病了。
01 死亡體驗館「續命」
四月初的時候,丁銳通過《奇葩說》可能給他的醒來死亡體驗館續了命。2017年的夏天,i黑馬曾經對他的體驗館作了一篇深度報導,題目是《為什麼投入400多萬的「死亡體驗館」一年半就做不下去了?》,當時丁銳告訴記者,打算在「明年清明節關門」。不過現在看來,門還沒有關死,大量在2018年清明節後出現的報導,讓醒來受到了不少公眾關注,於是這家體驗館決定把它的生命再往後延一年,網站公告說直到2019年4月4日才會永久關閉。
如此一來,可能會有懷揣好奇心的人來這裡做一次「假死」。看丁銳的現場,他談成功人士的死亡焦慮,介紹十二輪淘汰製遊戲, 「無常」 之門、 「彼岸」、 「歸零」、 「重生」,你會發現裡面混入了太多文化主義,或者說是用文化對死進行的一次體驗式解讀。


這不是死亡和文化的第一次接觸,作為文化的一粒塵,死亡一直有其「追隨者」,且無國界之分。
02 VRC_Fuzz 的VR斷頭台
10月底,一則日本網友自製的MOD引發了網路熱議。這位網名叫作VRC_Fuzz的日本人讓玩家通過虛擬現實體會一次被處決的經歷。在環繞式音效的作用下,幽深的幾何空間透出讓人不寒而慄的恐懼,在巨大鍘刀落下的一瞬間,雖然玩家內心知道是假的,但卻被嚇癱了。
在科技不那麼發達的此前,日本就有所謂的「入殮體驗節」,這個東亞民族對死亡有一種詭異的執著。如果不是《入殮師》封獎,可能很多人並不願對日式死亡文化多瞅一眼。不同於我們對死有避而不談的忌諱,他們可以很熱血地做一件活著的事,但又可以很隨意地談論另一個世界。若從根本上解釋這一點,那就是宗教的震懾力。
過半數日本人信仰凈土宗,所謂「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身不退「,只要完全靠倒阿彌陀佛,一切擔心都是多餘的。所以,「死」對於日本人來說沒有什麼大不了。
為年輕一代中國人所熟悉的《人間失格》作者太宰治,在39歲那年終於擺脫了這個人間。如果說有人覺得死之於太宰治的人生是一種解脫的話,那麼川端康成就是用完整的生命周期詮釋了作家之「死」。年輕時的他曾評論自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73歲那年,他選擇口含煤氣管結束生命,或許在那一刻,他已將自殺視為藝術成就。


「自殺而無遺書,是最好不過的了。無言的死,就是無限的活。」——川端康成
03 被「附體」的藝術
如同文學與死亡的不解之緣,美學對死的崇敬甚至比文學更強烈。雷諾阿說過「只要有點進步,那就是進一步接近死亡」,生和死就像坐在長椅兩頭的兩個人,往中間挪一下,意味著距離更近。米開朗基羅臨終留了這樣一句話給世人,「事物好不容易如願表現出來的時候,也就是死亡。」這時候,你大概會想到梵高,但他的死和太宰治有些類似,雖然梵高比太宰治早生50多年,但他們都是生得絕了而投入了死的懷抱。
可是有一位畫家,他的作品就在描繪死亡,活到72歲自然地死去。雖然他是馬蒂斯的老師,但可能由於他甘於隱世地創作以及神秘主義的畫風,今天許多人知道梵高,卻不知道古斯塔夫·莫羅。莫羅的畫說是神秘主義,不如說雜糅了各種宗教的影響。晚年時期,莫羅的畫風張狂起來,他的《命運女神和死亡天使》已經有了野獸主義的影子,後人這樣解釋「在這幅畫中所塑造的命運女神手執寶劍主宰生與死,整個畫面籠罩著死亡的恐怖,令人不寒而慄」。其實莫羅一生大部分時間是與社會隔絕的,對於他人而言,這也是一種「死」吧。
如今,還有不少藝術家樂於在大眾面前撕開死亡的面目,似乎這就是藝術的使命之一。但他們並沒有讓今天的人在身心靈上擺脫死亡,因為普通人感知死亡是從肉體的消逝開始,精神很難單獨進入假設。於是有一些人試圖通過生物科技來拉長生與死的距離,對「生」做手腳,但卻發現這並不是活人想要的。


拒絕、憤怒、掙扎、抑鬱、接受 ——《論死亡與瀕臨死亡》
04 李飛飛和 3.5 億「病人」
與賀建奎嘗試以一己之力闖入基因工程禁區不同,這世上還是有很多正常的科研人員。雖然近期媒體寫了很多關於愛滋的文章,無論是科普還是數據分析,愛滋尚不是全中國最嚴重的疾病。
世衛組織在2012年發布過一份題為《抑鬱症:全球性危機》的報告,指出抑鬱症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負擔疾病,預計在2030年將上升至世界第一大疾病。2016年全國官方統計,中國患抑鬱症的人數是3000萬,2017年這個數字超過了5400萬,患病率為 4.2%。放之全球,約有3.5億人患上抑鬱症,患病率為4.4%。得了這病,超過70%的人將在一生中都伴有明顯的抑鬱癥狀,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只有10%接受了藥物治療。
那些情緒低落、百無聊賴、對什麼都沒有興趣的日子,讓他們成了人間的獨角戲。如果不接受治療的話,完全憑運氣任病情發展。但以上數字只是被確診的患者,還有一部分人壓根不知道自己病了,出於各種內外壓力,對於心中的疑惑和恐懼難以啟齒。其實抑鬱症的治癒率較高,約80%的患者通過積極乾預和治療都能取得明顯療效。但也許是對他人產生了抵觸,大部分患者不願面對臨床檢測,於是另一些人想到或許可以用AI輔助完成這件事。
不久前,李飛飛和她的團隊帶來了這項研究成果,通過口語和3D面部表情評估實現抑鬱症自檢。這次使用的機器學習模型,採取了兩個技術部分來組成:1、句子級的「概要」嵌入;2、因果卷積網路(C-CNN)。數據部分採用的是多模態數據:(a)3D面部掃描影片,(b)音頻錄音,可轉化為可視化的log-mel聲譜圖,以及(c)患者講話的轉錄文本。最終需產出兩項指標,PHQ評分和抑鬱症分類。


實驗中,他們把音頻、3D面部掃描和文本輸入C-CNN,將多模態句子級嵌入裝進抑鬱症分類器和PHQ回歸模型裡,通過這樣的方法和現有測量工作進行比較。結果是,和經過臨床驗證過的PHQ水準相比,該模型的平均誤差在3.67分,相對誤差為15.3%。在檢測重度抑鬱症上,則達到了83.3%的敏感性和82.6%的特異性。
這項成果自然是喜人的,至少面對遙控數字助理,病患沒有那麼排斥,對於潛在抑鬱症的篩查有很大的推動性。但是,報告中說了「早期檢測可能影響到60%未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成年人,並讓他們有機會獲得治療」,這依然是一部分人的救贖,剩下的40%會走向何處呢?


重度抑鬱症的一種結局:自殺
回到丁銳在《奇葩說》裡的敘述,他說「我看過很多成功的人,他們只會越來越焦慮,因為他們時時刻刻強調的是控制和精準」。不如這樣說,控制和精準都是因為害怕失去,而死亡是一切現世的終結。焦慮一旦達到極致,精神就會走向扭曲,或許這群人需要的不是文化主義的安慰,而是科學治療。
成功人士為什麼是抑鬱症高發群體?這裡提一下任老吧。在他老人家的最新談話裡坦言「2000年前,我曾是憂鬱(抑鬱)症患者,多次想自殺,每次想自殺時就給孫董事長打個電話。」直到2006年時,那天機緣巧合下任老坐在西貝筱面村吃著飯,看到載歌載舞的內蒙農民散發出的「不自棄」,回去之後流了很多淚,從此再沒有想過自殺。
其實,底層的人連飯都吃不飽,出身即艱難,又有什麼心思去思考人生呢。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早就說過,最底層的需求是生理需求,第二層是安全需求,第三層是社交需求,第四層是尊重需求,第五層是自我實現需求,最上層是自我超越需求。「自我超越」是後期加上去的,他本人的解釋是「缺乏超越的及超個人的層面,我們會生病、會變得殘暴、空虛,或無望,或冷漠。」如他所料,很多人倒在了自我實現上,他們最後在命運的洪流中和自己失散了。


「接受自我」對一個活人來說很重要。
05《聖朱尼佩羅》
這是《黑鏡》第三季的第四集,醫療系統已經開發出意識存儲再生技術,患有絕症或老年癡獃等病症的病人,可以在每周六定時定量試用系統進入聖朱尼佩洛這座虛擬城市,用於緩解他們的痛苦或通過懷舊記憶治療老年癡呆症。按照法律,死者在生前可以自願選擇死後是否將意識駐留在聖朱尼佩洛。
從21歲開始就與病床相伴的約克夏在得知自己時日不多後,嘗試體驗系統。她選擇回到1980年代末,並在那裡遇到了凱莉,一個熱情開朗的黑妞。但想到21歲時因為出櫃與父母爭吵,在高速公路上發生車禍而癱瘓,面對眼前這個擊中她靈魂的女孩兒,約克夏逃走了。

 播放GIF
播放GIF
一周後,約克夏想明白要在生命最後的時刻畫一個圓滿的句號,她又來到酒吧見到凱莉,這一次兩人都沒有退縮。就在約克夏以為找到愛情的時候,她發現凱莉失蹤了。於是每到周六,她就進入系統在酒吧焦慮地等候,終於有一回她等到了凱莉。而凱莉卻像個渣男一般,拒絕了她。在天台上,凱莉說現實中的自己也是將死之人,但她不確定是否將意識留在虛擬城市。最後,二人決定見一見現實中的彼此。
就是這一次見面,凱莉決定向約克夏求婚,在病床前,牧師為兩人舉行了簡單的儀式。隨後,凱莉作為家屬在約克夏的安樂死協定上籤了字。約克夏回到聖朱尼佩洛等待凱莉,她不確定對方會來,因為凱莉的家人都沒能夠在虛擬城市裡永生;但她又相信著,走在人生盡頭的凱莉會來。終於,約克夏等到了佳人之約,凱莉的遺體在墳墓裡陪伴家人,意識則和約克夏在一起。
這個挽救人生遺憾的故事,看似美麗,卻是自我實現主義的極端化。逆向思考一下,如果能重新來過,我們還會珍惜現在嗎?


「如果我死了,說明我活過。」 —《真實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