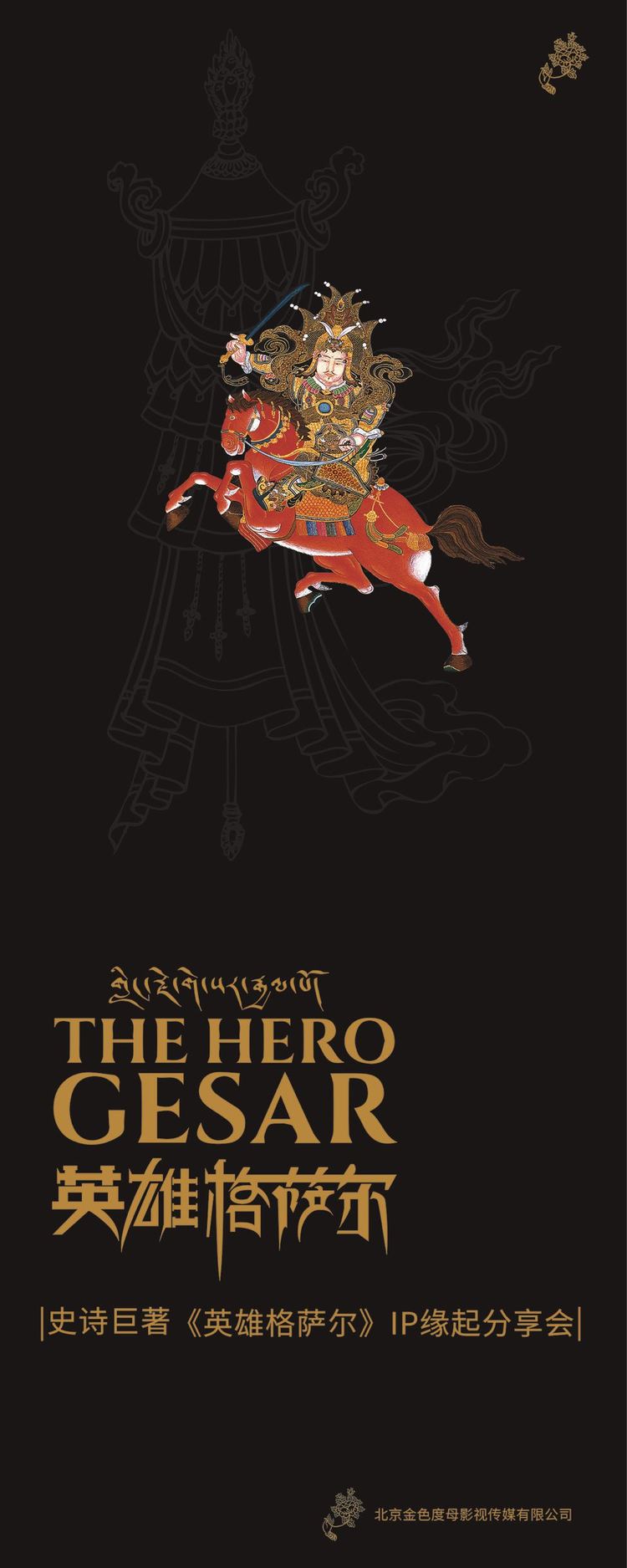1
評論
守望名叫甘南的那片
草原
文 | 李瑪

剛傑·索木東,又名來鑫華,藏族。1974年出生,甘肅卓尼人。有詩歌、散文等被譯成英、藏、蒙古、維吾爾、朝鮮等多種文字。著有詩集《故鄉是甘南》。現供職於西北師范大學。
“
在剛傑·索木東簡潔樸實的詩句中,我們欣賞到了甘南獨具特色的地理風貌,感受到了善良熱情的藏族人民的美好品性,領略到了藏族悠久燦爛的文化的魅力,他的詩歌有一種回味無窮的“酥油茶”的清香味。
”
藏族詩人剛傑·索木東的詩歌作品豐富,創作風格較為一致,在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漢語詩歌創作中較有代表性。他的詩歌中充滿了強烈的故鄉情結,表現出詩人對故鄉的守望。在守望中,詩人以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來審視故鄉,並在對故鄉的書寫中反觀生命的意義、人生的價值,以此豐富了詩歌的內涵。甘南這塊“高地”成為詩人揮之不去的情結,成為詩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使其詩歌具有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氣息和哲理思辨色彩。
難以忘懷的鄉情
剛傑·索木東曾說:“我文學創作的原動力,來自骨頭裡奔騰著的血脈。”這“血脈”就是作者的故鄉情,是一個赤子對故鄉自然風光、文化習俗、親朋好友的無限思念、讚美、眷戀,這鄉情猶如一條清澈而永不斷流的小溪,滋養出了詩人的那顆潔白無瑕的詩心。

甘南風景
甘南位於我國甘肅省西南部,青藏高原東北邊緣與黃土高原西部過渡地段,境內有廣闊的草原、驚豔的自然風光、厚重的人文景觀。詩人20歲時離開了故鄉甘南來到蘭州求學,從此與故鄉“相聚”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少,但這並沒有使他與故鄉甘南的關係變得疏遠淡化,反而使他的鄉情更加濃厚。在《故鄉是甘南(組詩)》《清晨,突然想到甘南》等詩歌中,詩人從不同側面和不同角度描繪了故鄉的山水、人情和文化,在或柔美、或傷感、或激越的詩歌旋律中,盡情地傾訴了他難以割捨的鄉情,使其詩歌具有了一種鄉情美的審美特質。
鄉情是詩人永遠的心結。在對故鄉的書寫中,詩人終於回到了“故鄉”,回到了甘南那片純潔、開闊、豐滿的草原,與甘南融為一體。這種美的特質,對於剛傑·索木東來說,不僅代表著他的創作風格,更加表現了他溫柔而包容的美好品格。他的詩歌表現的不是小我情懷,而是一種受藏傳佛教文化影響,把自己融入到了一切生命之中大我的博愛情懷,這樣使他和他的詩歌抵達了另外一個生命的“故鄉”,也因此有了廣度和高度。剛傑·索木東的詩歌以難以割捨的鄉情,感動了我們浮躁、迷茫、冷酷的靈魂。
難以排遣的鄉憂
在剛傑·索木東詩歌裡,甘南是一個出現頻率較高的詞語。詩人在一次次“歸鄉——離鄉”的時間和太空組合中審視現實的故鄉。在此基礎之上,他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眼光來審視現實的故鄉,這又使他的詩歌在抒情中閃耀著一種理性的光芒,表現出一種更為高遠、豁達的人文關懷情結。剛傑·索木東的詩歌既有對故鄉摯愛、思念、讚美的濃烈情感,同時又有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衝擊下的故鄉“變”與“不變”的思考和難以排遣的鄉憂情懷。
面對市場經濟和現代城市文明不可阻擋的洪流,甘南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此同時,生活在這片藍天白雲下的農牧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也悄然發生了變化。當詩人回到故鄉面對眼前的“變化”時,故鄉的一些人、事、物已和兒時眼中的不一樣了,這使他感到陌生和擔憂。在《甘南:用四季的四種方式懷念·冬》中他這樣寫到:“一盆牛糞火燃起的冬天/阿媽剛把最後一粒種子/連同秋天一起收起/一場大雪/已經迫不及待地落滿草原/冬天的甘南/羊皮襖捂不熱的甘南/一個新的生命需要誕生/一個黑臉蛋的新娘坐守雪域/她和她黑帳篷般的幸福/像長夜一樣漏風/在甘南/一首牧歌正逐漸生疏/一條老路正逐漸生疏/在第一個季節裡/懷念的寨子/正逐漸生疏”。詩人由故鄉的“變”而引起了思考,他一方面讚成故鄉的“變”,推崇與時俱進、求變求新,賦予優秀傳統文化以新鮮的血液。但另一方面,詩人在詩中也表現出了擔憂,比如城市消費觀念的湧入,故鄉曾經熟悉的迷人風光、淳樸的人性和優秀的傳統文化,正在發生著變化或消失。如《塔爾寺》中,“神聖的經卷中/袞本賢巴林/絳紅色的僧衣/正在隱去/喧鬧的塔爾寺/我只能空手而來/空手而去”;《打鐵,或者一個久遠的印象》中,“三十年後,再次路過/街坊,那間打鐵的屋子/富麗堂皇,迎面而立/一個妖冶的姑娘”;在《茶、馬、或者遠逝的古道》中寫到,“而誰又在/將醒未醒的夢裡/為我注入/母語丟失的歷史”等等。“喧鬧的塔爾寺”隱喻故鄉在商業化的進程中已經變得世俗而浮躁;“一個妖冶的姑娘”隱喻故鄉淳樸無私的人性的消失;“母語丟失的歷史”隱喻那些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文化的改變或消失。這一切的變化或消失令作者在《甘南:用四季的四種方式懷念·冬》中感歎:牧歌正生疏,老路正生疏,寨子正生疏,文字簡練,節奏急促,真切地抒發了詩人對故鄉這些本不該“變”的美好人、事、物發生改變時所產生的深沉憂患感。

塔爾寺
遊走於故鄉與城市兩地的詩人,不僅給我們描繪出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般的故鄉,同時也描繪出了一個貧瘠荒涼的故鄉,這兩種故鄉在詩人的筆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讀者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故鄉。如《在甘南》:“高原最高的地方,那些/頑強盛開的鮮花都叫做格桑/那些黑臉膛的漢子/深藏著骨縫裡的憂傷/一泓泉水流下山崖/那麽多的傳說,開始/風一般流行/是誰,又把貧瘠的甘南/擱在了不食人間煙火的雲端”。故鄉如格桑花一樣美麗,如康巴漢子一樣堅強,如傳說一樣神奇,但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在這些華美的外衣下“深藏著骨縫裡的憂傷”,這“憂傷”源於故鄉的荒涼貧窮,作者將目光轉向了一個更深的層面來“剖析”故鄉,看到了故鄉“不變”的一面。
由於甘南特有的地理環境原因,造成了這裡交通不便,導致當地一些地方經濟發展狀況較差,教育基礎設施薄弱,同時,一些落後的思想觀念也進一步加劇了貧窮的延續。詩人在一遍遍的回望中叩問自己:“走出故裡我就能擺脫困苦嗎/甘南,遙望經年的故鄉/貧窮苦難夜夜撕裂我流血的心願/情所獨鍾的卓瑪姑娘喲/緊握皮鞭的玉腕骨瘦如柴……”(《走出甘南》)詩人在詩中提出了一些社會問題,希望探索出一條符合本地情況的脫貧致富之路,讓故鄉的人們早日過上幸福、文明、和諧的新生活。
難以忘卻的鄉思
剛傑·索木東自離開甘南藏區後,就長期在蘭州求學工作。在遠離故鄉的城市,詩人眺望遠方的故鄉,並用樸實的文字組成一首首包含著至真至美的詩篇,來抒發鄉思之情。這種鄉思在四季的輪回中被拉長,成為一根“剪不斷”的絲線,一頭連接著故鄉,一頭連接著漂泊異地的詩人。

在詩人筆端,鄉思不僅是對故鄉具體的人、事、物的思念,它有一種更深層的抽象內涵,是一種在現代文化觀念熏染下的藏族知識分子的,對族群文化的“鄉思”,更傾向於內心世界的思想和精神的層面。如《高原上的狼毒花開了》:“終於可以對這個午後說出暖意/終於可以,對那株變了色的狼毒/努力說出,我的讚美——/荒蕪的大地,已經無需證明/你的根系,究竟有多麽龐大/站在母語丟失的路口/也無法洞悉,那些/和骨頭一個顏色的紙張/經世不腐的秘密/如你所願,/這個夏天/高原上的狼毒又開得茂盛無比/——滿山都是,統一/晃動著的腦袋”。狼毒花在詩中不僅僅是故鄉特有的一種植物,更重要的是象徵著藏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是一種頑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體現。詩人在異鄉想起高原盛開的狼毒花,不由得想到了民族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一種更深層的鄉思之情不禁從內心升起。
受到藏文化熏陶的詩人,成人後離開了自己的故鄉,來到了大城市,身處另一種文化群體之中,這樣使他和故鄉有了一個時間和太空的距離,通過現代都市文化與“故鄉文化”的比較,使他更加清醒地看清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優點和不足。他曾在訪談中提及自己“不遺余力地努力詮釋和傳播著優秀的母族文化和個人情感”。這是詩人創作詩歌的一個原因,他要通過詩歌創作,從審美的角度完成一次文化尋根之旅。今生今世在詩歌中一遍又一遍念及那遙遠而咫尺的故鄉——甘南,在思念中回歸故鄉,再現優秀傳統文化。
在剛傑·索木東簡潔樸實的詩句中,我們欣賞到了甘南獨具特色的地理風貌,感受到了善良熱情的藏族人民的美好品性,領略到了藏族悠久燦爛的文化的魅力,他的詩歌有一種回味無窮的“酥油茶”的清香味,這種味道使他的故鄉情結有了民族特色。從他的詩歌中,我們也看到少數民族知識分子重述本族群歷史文化傳統的精神需要。
2
創作談
人世溫潤,詩意
而行
文 | 剛傑·索木東
我出生在甘肅甘南。位於青藏高原和黃土高原過渡地帶的這片土地,被費孝通先生稱之為“青藏高原的視窗”和“藏族現代化的跳板”。從西羌到吐谷渾到吐蕃再到近代,歷史上一直是多元文化交相映輝的地界,更是一片風格迥異、風骨獨具的文學沃土。
在這片藏漢二元文化浸潤的土地上,民間生活中充斥著古老的諺語歌賦,許多人開口即誦。記得很小很小的時候,一個大字不識的老祖母,就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充滿著大智慧的諺語:“別急著念瑪尼,先去做點念瑪尼的事情”,等等。在百年老木屋那一排排因多年日曬而四處龜裂的簷柱裡,我和兄弟姐妹們拿棍子掏出築巢的鳥兒和結網的蜘蛛,頑皮玩耍的同時,也掏出了這個屋簷下牛一樣苦累了幾輩的女人們,梳頭時塞進去的凌亂白發!從那個時候起,我和兄弟姐妹們開始知道了手握歲月的痕跡,感覺生活的艱辛和母愛的偉大。之後經年,母親凌亂的白發就在我生澀的筆端,如一場場鋪天蓋地的大雪,不分季節、紛紛揚揚地落下……
這些植根於血脈的東西,慢慢溶解在人近中年的生活和寫作中,反覆回味,受用無窮。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藏族作家的文學創作大多都從詩歌起步。我的文學之路亦是如此。之所以走向文學之路,往大裡說,應該是神性和詩性始終彌漫著的青藏高原,給予了我和雪域大地上所有的族人,與生俱來的那種靈性和詩性。正是植根這片土地的優秀文化,讓她的兒女們能夠在這個浮躁的世界裡,長久地持有一份豁達而寧靜的內心——這恰恰就是文學乃至所有藝術最需要的。
母族文化是文學的源動力,民族性的表達是文學創作的緣起。只有在自己熟知的文化中汲取營養,我們和我們的文學才能不斷成長,才能實現自己的跨越,才能讓自己的創作基於民族文化而躋身世界文化之林,才能在更高的層面上達到一個新高度。
我的創作,也是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和認知開始,並一直向這樣一個高度努力和靠近。
在蘭州讀書、工作的20多年裡,多元文化的滋養,讓我自己慢慢完成了從“青藏詠歎調”式的單純抒情,到“人世溫潤”的自然表達的過渡。自己的文字也慢慢有了更廣闊的太空。
也就是說,當我們貼近母性大地,用“眾生”的眼光來審視世界和學會表達時,創作就會超越自我,抵達一個前所未有的溫潤境地。
文學創作是超族裔、超人類的創作。我們之所以基於這樣一個族裔性的群體創作,恰恰就是在強調族裔性的同時,超越族裔性,也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個概念。
毋庸置疑,在漢語語境中,作為藏族作家的“邊緣感”和藏族文學中用漢語創作的“邊緣感”,曾經在一段時間內桎梏著自己的創作。但是,前進一步就會發現,邊緣感其實就是自己的一個局限性認識,或者說是自己的一個不成熟的創作狀態。因為在文學創作中,永遠沒有“中心”和“邊緣”之別。如果一個作家的視野開闊了,創作成熟了,任何“邊緣”都會成為“中心”。在真實的紀錄和表達裡,我們逐漸和母族融為一體,逐漸和人類融為一體,逐漸和世界融為一體。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8年10月22日2版
本期編輯 | 叢子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