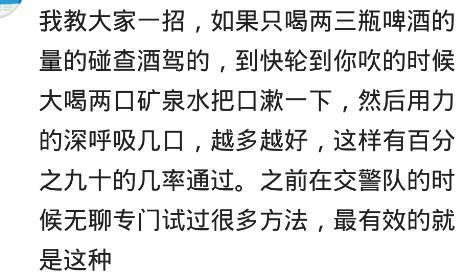一
“我沒有喝醉,胡言亂語的是酒杯。”
這句話出自一個當年的校園詩人,筆名駱駝。我跟他已經快二十年沒見了。如同大部分酒友記憶中的片尾一幕,我倆的最後一次聯繫,是在電話裡說“哪天喝頓酒吧”,然後一晃二十年,人還是沒影,先把他的詩拿來用用。
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的,則是本周一的一次酒局。一起吃飯的是八頭男人,大家相識已經三十二年,年齡加起來也超過了四百歲。
我喝酒的一條重要原則是:不要跟那種成心要把別人灌翻的人喝酒,不要喝那種不能把自己灌翻的酒。這天的飯局對於前一句來說完全不是問題,大家都搶著把自己搞倒,所以不到八點半,哥幾個帶來的幾瓶白酒就見底兒了。
而後一句對我來說有點兒問題,因為某些原因,俺只要了一瓶紅酒,雖然也頻頻舉杯,雖然其他人也沒有逼迫,但自己卻深深體會到了不能同桌同步暢飲的痛苦。尤其是飯局結束,沒醉的人當仁不讓世界充滿愛誰誰地要擔當起清理戰場的善後重任。
我走出飯館,先清點人數,發現少了三頭。其中小牛和小強最後時刻的臉色還算正常,應該屬於一秒鐘都不耽誤趕回家去吐的類型,而另一個不見蹤影的老谷卻很讓人擔心,因為他剛剛在飯桌上就吐了。我掏出手機,想給他打個電話。這時阿光還愛撫著我的腦袋,強烈要求叫代駕開上他的車,先送俺回家。撥了幾次,終於通了,原來老谷出飯館後自己蹲在馬路邊,不願見哥幾個,只想一個人靜靜,思考一下人生。我開始做他的工作,想把他從草叢裡勸出來。一番苦口婆心之後,老谷還是選擇了跟灌木叢待在一起,而我打電話的時候,阿光的代駕已經來了,被比較清醒的康師傅架到車上絕塵而去,完全忘了要先送俺回家的反覆承諾。我望著馬路兀自發愣,又見胡尼拖著淚汪汪的小顧往好不容易攔下的計程車裡塞,而小顧還在慷慨激昂地嚎叫。這人上大學時的外號就叫“騾子”。
沒過一會兒,飯館門口就只剩下了孤零零、沒喝多的一個我。
二
這次喝酒,是受春節期間一次飯局的刺激。
那次飯局我沒有參加,這導致了更痛苦的局面,因為飯局會有人通過微信現場直播,讓外面的人乾巴巴看著,或眼熱嘴饞,或鼓勁撤火。
開喝沒一會兒,就有人發上來一張現場圖片,是阿光和大朱兩位。

看這倆很像警察部門掃蕩非法色情場所時那些被抓獲的客戶,我心裡有種莫名其妙的痛快感受。
事實上不到八點,阿光就不省人事了,熬到飯局結束也沒醒過來,而他們吃飯的包間是在二樓,只好由幾個加起來快一千歲的老戰士,喊著號子,順著陡峭的樓梯,把他抬將下來。其間還有人喊“大家往這兒看”,拍照留念。

寫到這裡,不得不插一句:要想喝得盡興,千萬不能在那種富麗堂皇的飯店裡開搞,那種地方會讓你不由自主地端裝起來。只有在那種亂七八糟的小酒館,才能把自己喝得亂七八糟的。
這次飯局是在大年初三,據說一直持續到初八,大朱看到當天的照片,還彷佛能聞到酒味,中人欲醉。
三
沒喝多的人跟喝多的人在一起,痛苦之處並不在於要乾一些力氣活甚至買單,而是那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尷尬和孤獨。
如果大家都處在理智的水準線上,很好,朋友就是這樣決心交的;如果大家都開始騷情,也很好,朋友就是這樣交下去的。最可怕的是騷情的頻率不一致,因此不能共振。
比如喝多的人,自己的身體好像是別人的,既能做出無比笨拙的動作,也能產生遠超平時的靈敏反應;而別人的身體卻像是自己的,可以拍,可以掐,可以親密無間。兩個喝多的人正好,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正好兩兩相抵;最怕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
喝多的人說一些自己認為很重要的蠢話,能夠反覆說無數遍。如果聽的人也是喝多的狀態,便會一遍遍地呼應,甚至一次次地落淚,不覺其累,不厭其煩,換一個清醒的人試試?
跑調到讓人捂耳朵的歌唱,肉麻到令人起雞皮疙瘩的動作,保留節目只有保留到這時候才好釋放出來,儘管此前已經上演過無數次,但照樣自己陶醉,同桌喝彩,不演反倒不夠意思,可要是觀者清醒得有正常藝術鑒賞力,只會覺得不好意思。
更不要說那些章魚般的擁抱,熨鬥般的撫摸,交杯酒達人頻頻舉杯,堅定的異性戀者開始同性間的親昵甚至強吻,有人邁著凌波微步就是撂不倒,有人猝不及防摔個鑽老頭被窩。
然後再抖露些相互間以前的糗事,還多是發生在酒桌上的。這些無聊又肉麻的話,一定能把一個正常人逼瘋。
所以,不喝酒的人,不要跟喝酒的人在一起喝酒。
敲黑板。我說的“不喝酒的人”,指的是不享受喝酒、不願意喝酒的人,並不是不能喝酒或酒量很小的人。這就說到了酒桌上的第二條法則:“我幹了,你隨意”,隻把自己喝好就夠了,不要眼睛盯著別人。
仗著自己能喝,就要求對方也要跟自己喝一樣多的人,哪怕是口酒井,也屬於酒風不浩蕩的人。
如果飯桌上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打酒官司,為我比你多喝了一口、你的杯子沒我的滿我再給你加點兒而纏鬥不已,那不是共振,是相互禍害,是共同浪費。
四
客觀地說,喝酒並不是多麽值得誇耀的事兒,尤其是給別人帶來打擾和麻煩的時候。但一個人要沒有年少輕狂時光,也確實蒼白乏味了些。我曾經在網上看過一張照片,幾個年輕人像拖死狗一樣拉扯著一個爛醉如泥的兄弟,各自的臉上也是酒水混雜著淚水,標題叫“說好不哭的分手飯”,頓時想起俺畢業時那些同樣掏心吐肺的場景,老淚縱橫。
當然,最惡劣的就是酒後駕車。這一點無可爭議。如今大家只要一開喝,就毫不猶豫地提醒開車的彼此叫代駕。但這個意識和法律規定也就是近幾年才有,再往前追溯,“愛的代駕”是沒有的,只能慶幸那會兒大家命好。
楊葵酒量大,性子穩,當年雖然酒後開過幾次車,但都很穩健地完成了任務。嗯哼,只有一次例外。
那次酒後,葵老開車,我和非非搭車。先送非非到家。進了那個小區,等非非下了車,楊葵端詳了一下周圍的地形:我得開到前面倒個車。
好啊,正好讓俺下車撒泡野尿。我說。下車。
等我找到一塊人見不得的地方,解決了內急,然後回到下車的地方,等倒好車的楊葵回來。
幾分鐘過去了,寒風呼嘯,我感覺像過去了幾十分鐘,終於忍不下去掏出手機,委屈得都要哭了:大嬸,你在哪兒呢?
啊你沒在車上嗎?稍等,馬上馬上。楊葵在電話裡應道。
等到他的車過來,我上車,葵老說,他倒過車來之後,感覺我上了車,就坐在後座上,就開車馳去。路上還一直跟我探討人生呢,直到接到我的電話……
沒過多久,我看到一條社會新聞。哥幾個喝酒,結束後送一個喝大的哥們回家。那兄弟住胡同大院,到大院門口,說馬上就到家了,跟幾個朋友告別。結果,他在走回家的途中,看到路邊有座拆了屋頂和窗戶的廢棄房子,就忍不住進去,想歇會兒再走……冰天雪地中,這一下就沒再起來。
據說死者家屬還把那幾個朋友告到法庭,賠了一筆錢。
這件事兒為我以及我所認識的鐵血戰士敲了警鍾:酒後送朋友,必須全須全尾的,送到家,送上床。
五
“送到家,送上床”的事兒,我做得很少,大多是被送的,因為俺也屬於搶先把自己喝倒的角色,但從來沒有享受過被送上床的待遇,哼。
可要是兩人都喝大了,那就只能兩害相較取其輕,由說話較利索、智商殘存較多的人來承擔護送任務。這在我和阿光之間較常發生。
某次酒後,我架著不知所雲卻喋喋不休的阿光來到路邊,努力騰出一隻手來叫計程車,但過往車輛無不敏捷地繞我倆而行。
那次漫長的計程車啊,等車過程中,阿光向我掏了隱藏在他心窩子最深處的八卦,聽得我耳熱心跳,不住歎天,又忍不住擔心自己酒醒後再也記不起來。果然,第二天真就什麽印象也沒有了。娘的。
失敗了十幾次之後,我不得不把阿光橫臥在路邊的松牆後面掩飾好,然後一個人若無其事地站在那裡,伸手攔車。嘿,馬上就停下來一輛。
我先打開後車門,說句“師傅等一下”,再蹣跚到松牆後,把阿光扶上車。
折騰這些的時候,我聽到清脆的聲響。估計是司機師傅在抽自己的耳光,恨自己不長眼,上了當。
計程車開動,阿光越來越沉醉,既不能抒發感情,也沒法探討人生,只會不停地呻吟,依稀說著“想吐”。
對不起師傅。我歉意地說。
司機的嘴也沒閑著,開始向我描述他自己個兒。聽起來這是位黑道大哥,江湖人稱“石景山一條龍”,好像還蹲過大獄。
我這邊肅然起敬,司機繼續從容不迫地講述自己的事跡,拳打西城,腳踢海澱,威名鎮通縣,然後說,前兩天有醉鬼吐他車上了,還不給錢,他把那小子好好修理了一番。
這時我才回過味兒來,急忙表態:師傅您放心,他要吐您車上,我賠您三十塊洗車錢。肯定的。
司機頓時卸下包袱,露出工人階級的憨厚本色,嘴巴也調到溫馨又從容的夕陽紅頻道。等到阿光家,車剛停穩,我還沒做任何動作,師傅已經迅雷不及掩耳地來到了我們旁邊,迅速打開車門,幫我把阿光扶了出來。
然後,我聽到司機師傅長長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六
確實,吐人車裡這事兒,比吃飯時爭著結账還不地道。所以老酒鬼即使不能約束自己的色心、賊膽、粗口,也會努力掌控好嘔吐欲。
比如“交杯酒達人”牟森,平時沒少讓住得很近的楊葵開車送回家。只要上了車,他就開始全身運氣,發覺情況不好,及時透明地上報。
刻不容緩之際,平時威風凜凜的牟老更加惜字如金:葵,停。
葵停,他下車,吐,再上車。到小區,並不上樓,而是抱著樓下那棵鬱鬱蒼蒼的大葉楊,把自己徹底吐乾淨了再回家。
十幾年下來,牟老始終抱著固定的那棵樹。也不知道相較周圍其它同類,這棵樹是什麽心情,什麽狀況。聽,樹葉颯颯作響。
但吐在車裡的後果,我是知道的。
某次酒後,彤彤執意要開車送我回家。行車路線會是這樣的:我們吃飯的地點是在東南五環外,我家是在西北四環附近,而彤彤家又在東五環外。即使你的數學能力比證監會官員還要弱智,都可以算出這是一個多麽違背經濟規律的建議。但喝酒的另一條鐵律這時又發揮了作用:不要跟喝大的人比誰的主意大。
最終,我還是乖乖上了彤彤牌小轎車,由沒有喝酒的彤嫂掌舵,彤彤坐在副座上,發出一些完全沒必要發出、完全沒必要聽從的行車指令。
來到我家小區門口,我下車,彤彤也下車,哥倆擁抱,相互伸手把倆人掰開,然後目送彤彤上車、彤嫂發動,俺再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到六必居。
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給彤嫂打電話,得知他們已經回到家中。奇怪的是,送俺的一路,彤彤一切如常,但往自家返的路上突然發作,吐在了車裡。
事情的後續是這樣的:
第二天,彤嫂把昨晚草草收拾的車內又清理了一番,然後開車上班。
到第三天,彤嫂依然感覺到車內味道難聞,就去洗車處,讓專業師傅來清理一番。
洗車的小夥子捏著鼻子,把車內七七八八收拾好,然後一扭頭,彎腰哇哇大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