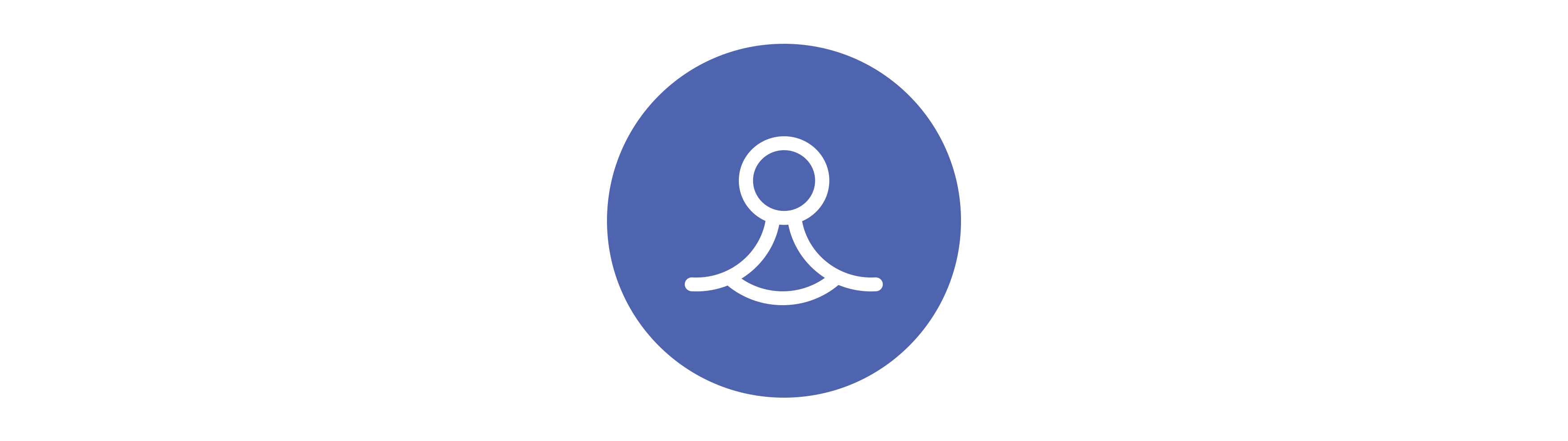(採訪:張笑晨 受訪:黃盈盈)
黃盈盈的辦公地點就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性社會學研究所裡,辦公桌被書圍了起來,老家在溫州的她就蜷在大椅子裡。辦公室裡很多書堆在地上,摞起來有半個人高,一本又一本,它們大多是性社會學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卻只能用作內部交流。
在無事的時候,黃盈盈就在辦公室掐本英文著作開始看,在潘綏銘看來,作為他學生的黃盈盈“愛看書、膽子大、英文好” 。剛入門的時候黃盈盈還是個小姑娘,現在已經接了他的班,掌管了中國人民大學的性社會學研究所。黃盈盈不負眾望,逐漸被社會所熟知的同時,也產出頗豐,今年出版了《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

▲《性/別、身體與故事社會學》
和普通的社會學著作不同,黃盈盈的新書有很多方法學的味道,她把“故事社會學”作為方法的一種,強調在一個故事生產出來背後的社會因素:在一個特定社會情境下,什麽樣的故事出得來、什麽樣的故事出不來;又是什麽樣的社會因素導致了這一結果,一個故事為什麽會在這樣的社會出得來,在另外一個社會情境下就出不來。吊詭的是,迫於多種原因,新書中的一章,就遭到了刪節,也就是說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這樣的故事是不能被看見的。
黃盈盈選了不那麽經常被提起的性故事:乳腺癌患者、老年女性、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和一個豪放女,她自己形容這本書是一個“讓隱形的故事顯性化”的過程。在眾多故事中,老年女性的故事讓她心裡咯噔了一下,因為在很多時候老年女性被看成一個無性的身體。在更多情況下,女性的性就不被提起。
“當那個年紀比較大的受訪者,那個人其實我認識蠻久了,當她比較正面的去談絕經之後,自己在性方面的一些實踐和感受的時候,其實對我觸動還是蠻大的。”黃盈盈回憶起自己跟一個老年女性的訪談時,依舊印象深刻。

▲性取向的多元化
很多時候,性社會學是不被主流社會學界所重視的。“在研討會上他們就說,你們研究的內容不重要”,但是散了會到了飯桌上,大家都圍著黃盈盈問她在會上說的東西,她只能苦笑,“他們覺得階層重要,但我們這個也不是不重要啊”,而在黃盈盈看來性的議題中,也包含著階層的議題,“很多情況下,性裡面就有階層、有等級啊”,在某些社會中,性能力、性取向和性癖好就是決定階層的重要原因,而不同的階層在性上也呈現出不同的樣態、擁有著不同的可能。
潘綏銘不怎麽認同其他社會學家對性社會學的評價,“說我們沒用,他們就有用嗎?”。潘綏銘認為性社會學好歹能幫幫普通人,“社會學是教育主流社會的,有一個人聽你的嗎?”,他顯得有些激動。
黃盈盈想用這本書見見大眾。每天早上黃盈盈打開手機刷朋友圈,“其實看到的都是一個個故事”,但是她不會立刻相信其中一個,她習慣了質疑和分析,“你可能感覺社會學家挺冷漠的”,她有點打趣自己。但是她希望給大眾提個醒:不要輕易地相信每天看到的一個又一個故事,一開始應該嘗試去分析、質疑,而不是一點就著,“用批判性的視角來看現在流傳的各種故事,看看能不能解構它。如果解構完了、分析完了,還是覺得要有怎樣的看法,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

▲解構朋友圈
在黃盈盈看來,作為大眾要有“反”的能力,“就是要有能力戳破這麽講故事的動機”,要不然很多事情情緒一爆發,可能導向什麽後果都難講了。
黃盈盈把研究過程放在書裡,甚至是大段大段的訪談原文,還有被訪談者懟她和她的學生的內容,她反思自己為什麽會被質疑,為什麽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潘綏銘記得黃盈盈讀研的時候第一次獨自去田野調查,去一個紅燈區,“我當時根本沒想過她敢去,當時是一個香港的老師找到我,說有沒有人想去”,當時沒有手機、也沒有微信,黃盈盈只能每天用固定電話給他打一個,轉眼十幾年過去了。
聽好書:
老師您覺得就這個社會層面來講,現在好像很多基本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們在討論性、性別、平權、女權這些問題,是否過於超前了呢?
黃盈盈:
這看你怎麽去判斷基本問題。當然這裡面有好幾個議題,性、性別、平權、女權要分開來講的。但是我就說我熟悉的領域,性和性別這一塊。那其實我覺得沒有超前的說法。因為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本身你判斷了有一些問題是更重要的,有一些問題是可以往後先放一放。但是我對這個我覺得是有點看法的,就像以前不光是有一些更為基本的問題,還有後面的性、性別、平權。我們就先瞎聊,有一回飯局上好多都是女權主義者,有的人就說性別的議題比性更重要,性別都沒有解決幹嘛要談論性的問題?就是認為性別比性重要。其實不光是性與性別有這樣的優先排序問題,很多人覺得相比於其他議題,貧困問題,甚至家庭問題,性別、性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兒。但是我覺得這個預設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憑什麽認為性、性別比其他的議題就不重要,標準是什麽。因為你要是從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這個程度上來說,性這個議題老早就有話說,人之初對不對?這些議題沒什麽哪個比哪一個更重要或者更不重要,在現階段我也認為性的議題和多元性別的問題就應該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重要不重要本身、基本不基本本身,我覺得它應該是需要被反思的。
聽好書:
所謂的當一個新聞變成一個故事,成為現在新聞比較經常講的非虛構寫作,當這個東西出現的時候其實有一些巨集大的議題是更重要的,像當年《南方周末》的那種寫作的形式更巨集大的議題,非常重要的東西其實是在故事中被磨滅掉了。
黃盈盈:
對,其實這裡頭我覺得有兩個可以討論的,一個是對於故事的理解,就像一個典型的故事,就像你說的,它是有這樣一個發展脈絡的。但是有的時候我們社會學也會泛泛地只是說我們在聊一個什麽東西,倒也不見得非得說這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說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故事其實是很複雜的,而且它沒有那條清晰的邏輯線在裡面,它很多時候也是很糾結的,到後面去表述的時候你是把它清晰化了,那是一個回顧性的。
你說性侵的故事,我為什麽經常會存疑呢?就在於現在很多是要勾起你對以前的回憶,你當時事情是怎樣的呢?當時很可能是一種曖昧的狀態下,但是後面大家發展不好了,關係撕裂了,回憶起來性質就可能變了。那你現在教我說,當年是被性侵了,我覺得這裡頭可能也沒那麽簡單吧。當年我不知道我是被性侵了,現在我知道這個概念了,我終於知道當時我是被性侵了,我覺得這個邏輯是挺需要考慮考慮的。因為你當時可能是在一種挺曖昧的,或者人在處關係的時候就有這個特點,很多事情就是挺曖昧的,大家就是這個感情,或者是這個狀態,它不是那麽明確地說我同意,可以,就是這種所謂的同意嘛,其實很多親密關係中沒那麽簡單一刀切切下來的,這個故事是一個很曖昧的故事。但是你現在去回憶給了它一個判定,而且要以非常清晰的立場給它貼一個標簽,太清晰和確定了。

▲很多親密關係中沒那麽簡單一刀切
聽好書:
在這些人裡面你覺得哪個主角對您印象最深刻呢?您覺得特別有意思的?
黃盈盈:
可能深刻的點不太一樣,但是這裡頭如果說讓我馬上有反應的,會是經血那部分,其實老年女性的那個點我當時是挺觸動的。因為對老年女性我們確實有太多的想象,會覺得那是一個絕經的身體,那是一個沒性的身體。本來女性的性是一定程度上不被討論的,對老年女性那就更是這樣了,包括女性本身,她都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性的身體。所以當那個年紀比較大的受訪者——那個人其實我認識蠻久了,當她比較正面地去談絕經之後自己在性方面的一些實踐和感受,其實對我觸動還是蠻大的。
另外文姐這個故事,其實變性朋友我有不少,可能故事對於我來說、對於大眾來說,是很多人不知道變性這個現象,但是我可能已經知道了不少基本的內容。對我來說,那個故事其實更有意思的是那種對話,就是我的學生和她做訪談的那種對話。因為文姐是非常強勢的也接受了很多訪談的那麽一個人,這個放在從我的故事社會學的脈絡裡就很有意思,所以我是從方法學上非常感興趣這個故事的。
當然了,這裡說到的陽春的那個故事是因為,她屬於確實是不得不讓你印象深的那麽一個人。我是在開會的時候認識她的。她很多的這種說法和實踐,很多做法其實在一定程度上說,是異類的,也就是剛才你提到的,你會把她放在超前的這個部分。
很多人其實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故事,就會覺得很驚訝。但是是因為我們沒接觸到,還是因為這樣的人本來就少呢?有的時候是你沒有太空讓這樣的故事出來,這也就是我剛才說的,你有沒有一個太空讓不同的故事出來,這種故事一定出不來的,這種故事一講出來大家就會覺得有各種問題吧,總之就會覺得各種政治不正確、道德不正確,你就不可能使得讓這個故事被大家看到,以至於讓人們覺得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這個人群人數可能是很少,但她存在的意義,包括陽春出現在這本書裡面的意義在於讓讀者看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不是社會上沒有的,是有的,只是原來的敘事結構裡面沒有它。這就涉及到一個知識結構和我們說的故事套路,有沒有這樣的一種可能性讓它存在。這就變得非常重要了,它的重要性不在於人多還是人少,小眾還是大眾,而在於這樣的一類故事有沒有可能出來,我覺得它的意義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