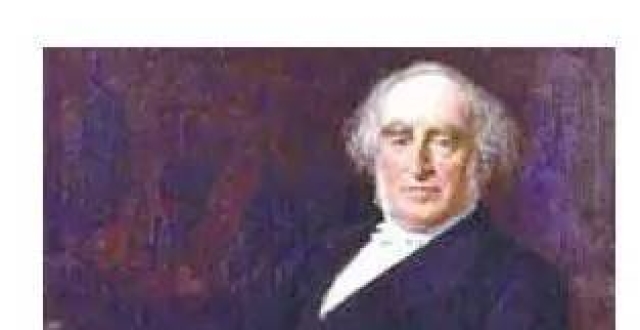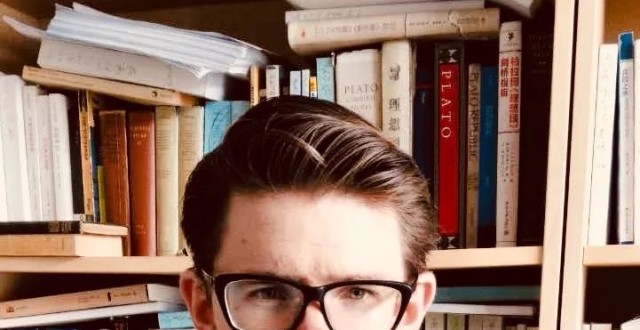高本漢——姓高,本來就是漢人嘛——那是他的自我介紹。我們都知道他來自金發碧眼的北歐,為中國的音韻學研究,說他是樹立了一座裡程碑,不如說建立了一套歷史語言學的範式,引導了幾乎整個二十世紀的音韻學。
我們前面提到,偉大的乾嘉學派中的佼佼者段玉裁,晚年陷入了深深的困惑,那就是‘支脂之’這三個古代是不同音的字,各自到底該怎麽念呢?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原因,並不是他學問做得不好,而是這個問題在清代古音學的範式中,本身就沒法解決,於是這個問題就成了古音學史上的一樁懸案——直到高本漢來到中國,開始著手用歷史語言學的範式研究中國的音韻學,才解決了這個中國學者們解決不了的大難題,而高本漢引入的印歐歷史比較語言學範式,也改變了此後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大方向。開辟了二十世紀以來音韻學研究的新路。僅此一點,高本漢就足以在漢學研究的歷史上留下不朽的一筆。
但高本漢的漢學上成就不止於此,他對中國的先秦典籍非常熟悉,而且都作過詳細的注解和考證。高本漢也是中國青銅器研究的專家,堪稱漢學家中少有的多面手。高本漢不僅學術研究上成績斐然,他的學術經歷也很傳奇。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他是如何走上與中國音韻學結緣的路線的吧。

圖4.3:創立二十世紀中國音韻學範式的瑞典人高本漢
高本漢(Bernard Karlgren)是瑞典人,1889年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是高中教師,在學校教授瑞典文、希臘文和拉丁文。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聰明而又能乾的家庭婦女,精通四種語言。在家庭的熏陶下,高本漢從小就對語言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他十幾歲的時候就對古典拉丁文和希臘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還將使用這些古典語言的詩歌翻譯成瑞典文。早在中學時期,他就能在詩歌中運用各種古典的格律。不但如此,高本漢還是一個極富有音樂天賦的人。他不但會彈鋼琴,還會拉小提琴。正如趙元任一樣,高本漢的音樂天賦以及他敏銳的音感,在以後他的語音學生涯中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幫助。為了避免誤會,以為做語音學一定要好耳朵,這裡必須插一段。早期語音學還在‘口耳之學’時,耳朵好壞的確有決定性作用。但1940年代有了語圖儀以後,理論上聾子都能做語音學,當代的錄音技術、語音分析技術就更不用說了。這就象古代天文學一定要好視力,但有了望遠鏡後,視力不是大問題,有了射電望遠鏡,視力已經無關了。朱曉農小學裡有過一個不及格的成績,就是音樂課,中學還是3分。現在在他的新浪部落格中他還寫道:二十五有志於音,五十而立,五十四不惑,五十五知天籟,五十六耳背,五十七什麽什麽!可見現在做語音學跟耳朵好壞沒大關係。
高本漢的時代正是瑞典方言運動如火如荼的時代,學者們對各地的方言產生了很大興趣,紛紛對自己的方言進行調查記錄。高本漢也參加到這次運動中。他在14歲的時候調查了離他家不遠的地方的幾種方言,並在他16歲利用其調查的材料發表他生平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論文的內容是關於達拉納省的方言。
1907年時高本漢高中畢業,就讀於瑞典的烏普薩拉(Uppsala)大學,成為方言學家和斯拉夫語專家J. A. Lundell教授的學生,主修北歐語言、斯拉夫語和希臘文希臘文,並立志將比較歷史音韻學的方法應用於當時還沒有人以此方法研究的中文上。由於瑞典內並沒有人教授中文,高本漢前往聖彼得堡,跟著名的漢學家伊鳳閣(A.I. Ivanoff)教授學習漢語,但時間很短,隻學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次年,高本漢坐船前往上海,到中國進行方言調查。在船上,高本漢靠一本英國傳教士寫的漢語課本,自學了漢語。到達上海之後,高本漢北上前往山西太原,在山西省立大學教授德語和法語,在課余時間,高本漢四處調查各地方言。在掌握了大量中國方言材料的基礎上,高本漢將漢語分為24種方言的語音體系。
從1910年到1912年,高本漢在中國生活了兩年,為他的博士論文準備了充分的材料。1912年1月,高本漢返回歐洲,在回到烏普薩拉之前,他來到來巴黎,在當時最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Pelliot)和沙畹(Chavannes)的指導下,進修了兩年中文,同時對其調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進行整理。高本漢1915年回到烏普薩拉撰寫博士論文,並通過了博士答辯。這篇論文是以法語寫成的,題目是?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這就是後來被趙元任、李方桂和羅常培三位大語言學家合力翻成中文,並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音韻學研究方向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一直到最近,這本書還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
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高本漢留在了烏普薩拉大學擔任副教授。到了1918年,高本漢被任命為哥德堡(Gothenburg)大學的東亞語教授。高本漢以前從沒學過日語,但是他憑借自己過人的語言才能,在一年內就學會了日語,並開始教授日文課。1939年,高本漢接替考古學家安特生成為瑞典遠東博物館的館長,至1959年退休。同時,高本漢繼安特生之後擔任博物館館刊編輯的工作,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自從擔任館刊編輯之後,高本漢的大部頭重要著作就都登載在這本年刊上,同時也以書籍的形式出版博物館的專題論文系列。
高本漢的研究成果並不僅限於語言學這一學科內,在漢學的其他門類中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26年高本漢發表的《左傳真偽考及其它》一書,基於其導師沙畹對《史記》的研究成果,考察了《史記》對《左傳》的引用。同時他也發揮語言學家之長,對《左傳》的語法現象和語法特徵進行了系統的考察。他後來指出,《左傳》獨特的語法,是非常不容易模仿的,因此也反駁了所謂的《左傳》為劉歆偽作的說法。另一方面,高本漢對中國古代青銅器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從銘文、形製、紋飾風格各方面綜合地區別銅器,並提出了自己的分區域斷代標準,在西方有很大的影響。
雖然高本漢在研究上成績斐然,但是終其一生,這位漢學家都過著拮據的生活。前面說到,他的著作都發表在期刊上,後來又被盜版出書,他根本拿不到任何稿費來補償他所付出的心血。為了謀生,他到處去作關於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和政治的演講,還曾經用筆名發表了三部長篇小說。這時候他的語言學家本色又體現了出來,小說中的主人公總是一位成功的語言學家,然後就會有美麗的姑娘愛上他。小說很暢銷,曾被翻譯為荷蘭文,丹麥文和芬蘭文,但高本漢也並未從其中獲利多少。當然,也從來沒有美麗的姑娘被小說打動,愛上這位貌似古板的漢學大家。
本文來源:公眾號“科大朱曉農”,作者朱曉農、焦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