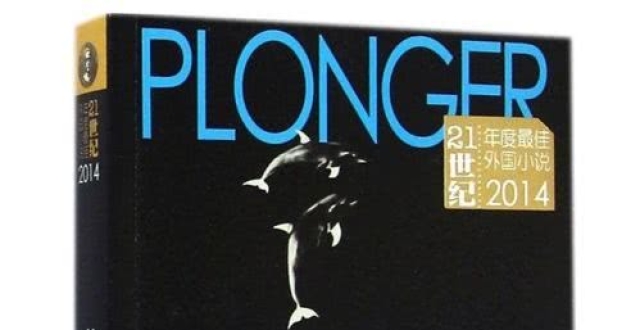今天我們的評審書目——《藍夜》,來自美國女作家瓊·狄迪恩。她唯一的女兒因病突然離世,悲痛之餘,她以文字記錄與女兒的點滴回憶,以此與摯愛道別,獲得走出悲傷的力量。她說,我們需要學會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關於婚姻、孩子和記憶,關於人們願意或不願面對的一切……透過這些文字,我們終將意識到必須學會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歡迎大家持續關注“評審團”,我們將不間斷地為大家送上最新鮮的閱讀體驗。書評君期待,在這個新欄目下,向所有人提供關於閱讀的優質評價,也同新的優秀“書評人”共同成長。
The Jury of Books
評審團
本期書目
《藍夜》

作者: [美]瓊·狄迪恩
譯者:何雨珈
版本 :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9年5月

作者簡介:
瓊·狄迪恩,美國女作家、記者,生於1934年。她在小說、雜文及劇本寫作上都卓有建樹,在美國當代文學領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05年,瓊·狄迪恩獲美國國家圖書獎。2013年,美國政府授予瓊·狄迪恩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她的寫作風格慣用獨特的角度審視人生,以簡約細膩的筆法刻畫人物,她敘述故事時並不巨細靡遺,而是乾淨利落、突出關鍵細節、斷裂文句,在字裡行間留出一片片空白,留給讀者遐想的空間,回味的余地。
主要作品有《藍夜》《向伯利恆跋涉》《奇想之年》等。
它講的是什麽?
藍夜將盡,夏日已去。
本書是瓊·狄迪恩的代表作,為了紀念逝去的女兒,她寫就此書。
狄迪恩在書中探尋生與死、情感與自我之間的關聯:是否我們從根本上無法互相了解,甚至對彼此一無所知?是否因為我們的不同,使我對你的痛苦甚至離去的預兆置若罔聞?是否即便沒有生死的阻隔,我們也不曾真正親密?
關於失去,關於悲傷,關於幸與不幸,關於婚姻、孩子和記憶,關於人們願意或不願面對的一切……她說,我們需要學會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爾的急流旋渦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它為何吸引人?
為了生存,我們講述。
——瓊·狄迪恩
讀來令人心碎。這是對失去的熱切追索,跟死亡與時間的悲傷斡旋。
——《紐約時報》
美國版《我們仨》,《奇想之年》的姊妹篇,一本獻給摯愛的告別之書。
美國國家圖書獎、人文獎章得主,當代現象級女作家瓊·狄迪恩,奧巴馬為她頒發“國家人文獎章”,稱她是“美國政治和文化至為尖銳和值得尊敬的觀察家”。她的文字鼓舞了幾代女性的思想與精神。
《藍夜》搶先試讀
我不知道多少人會自認是成功的父母。自覺成功的人一般會舉出那些象徵著(他們自己)社會地位的東西:史丹佛的學位、哈佛的MBA、常春藤聯盟大學畢業生聚集的律師事務所的暑期實習。而不怎麽願意自誇做父母的技巧的人(也就是大多數人),會像念經一樣重複我們的失敗、疏忽、不負責任和各種托詞。“成功父母”的定義經歷了非常明顯的變化:從前我們認為,成功的父母能夠鼓勵孩子進入獨立的(成人)生活,“提升”他們,放手讓孩子去飛。如果孩子想要騎著單車衝下陡坡,父母可能會象徵性地提醒一下,衝下這個陡坡就會進入一個四岔路口。但歸根結底,最想培養的還是孩子的獨立精神,所以父母也就不嘮叨,不過多地提醒了。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項結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動,父母可能會提醒一句,但隻提一次,不會再說第二次。
我在二戰期間的孩提時代便是如此。在戰爭中長大,就意味著我需要比在和平時代更強的獨立性。父親是空軍的財政官,戰爭剛開始那幾年,母親、哥哥和我就跟著他。日子過得並不算艱難,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間,生活在美國軍事設施附近的那種異常擁擠、混亂不堪的狀況,我的童年也絕不是安居無憂。在科泉市,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房子,那是精神病醫院附近的平房,有四間屋。但我們沒有打開包袱收拾行李,媽媽說沒有必要,因為隨時都可能接到“命令”(“命令”對我來說是個神秘的概念,不容置疑)。
每到一個地方,大人們就希望哥哥和我能適應,能湊合,能在建立生活的同時也接受眼前的事實,那就是無論我們建立怎樣的生活,都會因為“命令”的突然到來而終止,被推翻。我從來都不清楚到底是誰下的命令。但就算我覺得不合理,也不會有什麽實質性的改變。世界正在大戰。戰爭不可能因為孩子們的願望有任何緩和或轉移。孩子們容忍了這令人不快的事實,得到的回報就是他們可以創建自己的生活。這些孩子的父母面臨的最好選擇,就是任由孩子們自由野蠻地生長,而這背後隱含的影響,卻無人去深究。
戰爭結束了,我們又回到薩克拉門托的家。但家庭教育的主題依然是放任自流。我還記得十五歲半拿到實習駕照時,就覺得可以吃完晚飯從薩克拉門托開車到太浩湖了。要沿著蜿蜒起伏的山間高速公路開兩三個小時,到達之後,我們又立刻轉頭開回去,因為車裡的飲品都帶齊了,再沿著來路開兩三個小時回家。我開車消失在內華達的高山之中,而且還算是徹夜醉駕,結果爸媽一句都沒有說我。我還記得,大概也是十五歲的時候,在薩克拉門托北邊的美利堅河漂流,結果被大水衝進一個分水壩,然後拖著漂流艇來到上遊,又玩了一次。對於我這樣的行為,爸媽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
一切都是過眼雲煙。
現在實在是無法想象了。
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已經沒有時間讓你去容忍孩子這樣大膽放肆的消遣了。
儘管這種良性的忽略讓自己受益,輪到我們當了父母,對成功的判斷標準,卻是我們能對孩子進行多麽嚴格的監控,恨不得把他們緊緊拴在身邊。巴納德學院院長夏竹麗建議父母多給孩子一點信任,不要對他們大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攬。她提到有位父親,專門休假一年來指導女兒的大學申請準備工作。她提到有位母親,親自陪著女兒去見系主任,討論一個研究項目。她又提到另一位母親,說因為自己付了學費,要求校方把女兒的成績單直接寄給她。
幾年前,波士頓東北大學的盧因女士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寫了大學校園裡代溝變小的問題。不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家長們的問題,也指出了學生自己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一個月和家人的手機通話時間遠超三千分鐘。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個很有用的學術資料庫。“我可能會給爸爸打電話,問他‘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是怎麽回事?’這比自己去查找資料容易多了。他什麽都知道。我爸爸說什麽我基本都會信。”另一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生被問,有沒有覺得和父母太親近了,她一臉茫然不解:“那是我們的父母啊,他們本來就應該幫我們。這本來就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啊。”
我們越來越覺得,這樣深入參與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別正當的行為,對他們的生存至關重要。我們把他們的號碼設為快捷撥號,通過聊天軟體注視他們,追蹤他們的去向。我們認為打過去的每個電話他們都要接,只要他們計劃有變就要向我們報告。我們總是胡思亂想,覺得一離開我們的視線,他們就會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險。我們會把“恐怖主義”掛在嘴邊,彼此警告“世道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樣了”“不能放任他們乾我們以前乾的事了”。
然而孩子總是要面臨危險的。
女兒金塔納出生之後,我沒有一刻不在擔驚受怕。
我怕游泳池,怕高壓線,怕水槽下面的鹼水,怕藥櫥裡的阿司匹林,怕“破碎男”本人。我怕響尾蛇,怕湍急的水流,怕泥石流,怕出現在家門口的陌生人,怕沒由來的發燒,怕沒有操作員的電梯,怕空蕩蕩的酒店走廊。恐懼的原因顯而易見:這些東西可能會傷害她。問個問題:如果我們和孩子能清楚地了解彼此,這恐懼會消失嗎?是我們倆的恐懼都會消失,還是只有我的恐懼會消失?
成年後的我們,便漸漸淡忘了童年時的沉重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