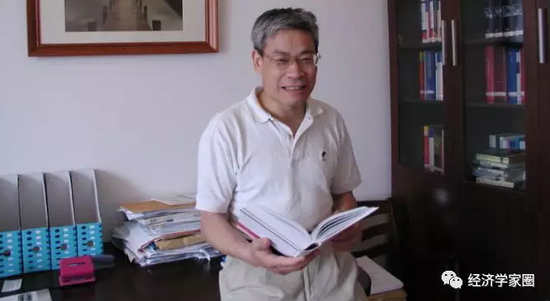編者按:2019年2月28日19點19分,著名經濟學家馮蘭瑞在北京協和醫院離世,享年99歲。
馮蘭瑞是老一輩經濟學家,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她在按勞分配等問題上發聲,提出社會主義階段論等重大觀點,推動了改革開放的破冰,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下文轉自《經濟觀察報》2005年4月25日發表的文章“馮蘭瑞:回眸平靜滄海下的險灘暗礁”,記者為黃錇堅。以此紀念這位逝去的經濟學人。
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05年3月24日揭曉,獲獎者分別是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除了常在媒體出現的吳敬璉,其他三位,在大多數青年人心中,卻只是一個模糊的符號。他們曾經倡導的理念、曾經衝破的思想障礙,今日已顯得非常遙遠。
回顧過去二三十年中國經濟學的衍變,除了四位獲獎的學者,其實還有更多被忽略的學人。不論如何評價,85歲高齡的馮蘭瑞都可以躋身中國當代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之列。著名學者、中顧委委員於光遠曾如此評價她,“當代中國女經濟學家中,不論從寫作之夥、見解之深刻和敏銳,無出其右者。加以她又付出很大的時間和精力從事經團聯經濟學學術活動的組織工作,更為經濟學家們所熟知”。
陽光明媚的四月,我們來到馮蘭瑞的住處。這是北京東單和東二環之間的一個小胡同。抬眼望去,華潤大廈和國際飯店就在不遠處,不斷蔓延的高樓吞噬著老北京的胡同裡弄。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這個獨門小院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深長:當全球化和現代化衝刷一切時,仍然有人堅守著歷史的河床。在資本和商業瘋狂擴張的年代,安心向學又需要多大的堅韌和清醒。
在大學課堂,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茲已佔據教科書的醒目位置;在報章雜誌,制度、產權、公司治理等名詞,已成為默認路徑,幾乎無須解釋。而按勞分配、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概念,卻仿佛已被蒙上時間的塵土。只有回到錯綜複雜的歷史現場,人們才能發現,從打破“兩個凡是”至今,思想之流已衝破多少關卡,它奔騰的浪潮在未來將衝向何方。
革命青年
思想家劉小楓曾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分為四組代群:“五四”一代、“解放”一代(三四十年代生長,五六十年代進入社會文化角色)、“四五”一代與“遊戲的一代”。何家棟也有類似觀點,他將20世紀中國思想家大致分成五代:世紀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紀末的一代,而這個道統的主鏈是梁啟超——胡適——顧準。
當我們問及馮蘭瑞,她屬於哪一代知識分子時,她回答說,“按組織規定,1937年七七事變前參加革命的,都算紅軍。我是1934年初二被迫輟學後參加星光讀書會,1937年春天參加自強讀書會、救國會,勉強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後來就是‘三八’式,我1938年1月入黨。算‘三八’式也可以。”
馮蘭瑞1920年9月生於貴陽的一個小康之家。在青年歲月,她和那個時代的優秀青年走著相同的思想之路。那一代人的追求,是爭取民族解放,實行民主制度,發展經濟,建設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以及爭取個人的自由和解放。這些思想的形成與她自身的遭遇、與共產黨的宣傳和教育分不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到貴陽時,11歲的馮蘭瑞就跟隨姐姐上街遊行,宣傳抵製日貨,大同學高呼“誓死不當亡國奴”的鏡頭深深印在她的腦海中。而到上高中時,她已三次被學校開除,第一次的起因是同教師辯論,第二次是因為挽留校長,到教育廳請願,第三次則是因為與教會學校的“洋教士”發生衝突。
這個桀驁不馴的女子,終於在第三次輟學後不再上學。陶行知先生的話“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名言幫助她作出了選擇。從星光讀書會、自強讀書會到“重慶市各界救國聯合會”,她逐漸成長為一個職業革命家。
這個時期對她人生道路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六舅謝凡生。這個長她7歲的舅舅,1931年離開家鄉貴陽去了上海。舅舅請她父親勸外婆允許他外出上學,他在信中說:“我的前途是要靠我自己來創造的”。在他,這意味著要走革命之路。在11歲的馮蘭瑞心中,這有著某種人生啟示的意味。愛好音樂、選修小提琴的舅舅,在上海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但反動當局卻逮捕了他,酷刑和虐待奪去了他的左腿。
當親友們將謝凡生營救回家鄉時,馮蘭瑞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位啟蒙老師。舅舅給她的最大影響,是讓她有機會看到許多進步書籍,比如高爾基的《母親》、綏那菲莫維奇的《鐵流》等等。其中,《地底下的俄羅斯》、《俄羅斯十女傑》是她印象最深的兩本。
1938年初,18歲的馮蘭瑞在重慶加入中國共產黨。她白天在外搞青年救亡運動,晚上刻蠟版印文件。她不知道,這時舅舅已是中共貴陽地下黨的縣委書記。兩個人就這樣互不知曉地為著同樣的組織默默工作。
從報業到經濟學
1940年,為逃脫國民黨的多次追捕,馮蘭瑞終於前往當時進步青年心中的聖地——延安。中央組織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參加編寫青年運動史。在完成十年內戰青運史的同時,她還寫了一本《徐特立傳》。1946年秋,馮蘭瑞與李昌結婚。隨著戰局的變化以及李昌工作的調到,她先後在張家口的《晉察冀日報》、華北軍區《戰友雜誌》、上海《青年報》(擔任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中國青年報》、《哈爾濱日報》工作。
青年時期的馮蘭瑞一直讓自身隨著革命的洪流前進,到1954年時,她終於有了一點自己的職業選擇。時任《哈爾濱日報》總編輯的她,興趣從報刊編輯向學術方面轉移。她放棄了報社的領導崗位,考入中央高級黨校(即日後的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學專業。
在黨校期間學習的馬克思主義和《資本論》,20年後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文革中,“走資派”馮蘭瑞和“黑幫”李昌在河南乾校被分別監督勞動改造,但她一直沒有中斷看書學習。1974年,西方國家出現了新的經濟危機。當時於光遠找到回京治病的馮蘭瑞和幾個人合作,選編《馬恩列斯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書。此後,在國務院政研室和社科院,馮蘭瑞都是工作在於光遠的領導下。他們在思想戰線上有多年共同的經歷,建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不久,胡喬木也找到馮蘭瑞,請她參與選編《馬恩列論生產關係》,另外還有兩個組編《馬恩列論商品經濟》、《馬恩列論階級鬥爭》。馮蘭瑞說,編這樣的語錄“其實很簡單,就是把馬恩列文集中論生產關係、論商品經濟、論階級鬥爭的段落找出來,剪貼就成了。我去時生產關係這個組已有三個人在那裡編,但他們對經濟學不熟悉,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所以專門把我找去了。”馮蘭瑞接著笑道,“1979年以後編語錄已不時興了,所以沒有出版。”
回眸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
1975年,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建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這個由他領導的“秀才班子”,後來被“四人幫”稱為“鄧記謠言製造公司”。馮蘭瑞親身經歷了這個只存在四載的機構的風風雨雨,她清晰地記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幫”繼而和“凡是派”展開的驚心動魄的鬥爭。她前幾年所寫的回憶文章“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在文中,馮蘭瑞對政研室負責人之一胡喬木在“批鄧”運動中的動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周總理去世時,我們都很悲傷。毛主席去世時,大家卻很迷茫,不知道國家會怎麽走。”馮蘭瑞說。在逮捕四人幫後,華國鋒主席依然批鄧。1977年2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同時發表“兩報一刊”社論,題目是“學好文件抓住綱”,文中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
但就在這個當時的最高指示發布後沒幾天,首都經濟學界就在於光遠的倡導下召開了第一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馮蘭瑞說,會議實際上就是用行動突破“兩個凡是”。四人幫認為,按勞分配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為澄清這種謬論,1977年至1978年,經濟學界舉行過四次全國性的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這些討論,構成了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一部分。
除參加會議外,馮蘭瑞還與蘇紹智合作,在《人民日報》發表多篇文章,如《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此文獲1984年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等等。以後馮又參加了政研室集體寫作《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這是一篇按勞分配理論討論總結性的文章,經過鄧小平審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署名,於1978年5月5日於《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全國各大報同日轉載,中央台即日廣播。
這些基本理論問題之爭已與今日的熱門話題相距甚遠,人們很難領略其中的風險、艱辛和要害。馮蘭瑞解釋說,一方面,有些謬論與領袖的“偉大理論指示”分不開的。毛澤東會見丹麥首相哈特林時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差不多”。另一方面,理論爭論的背後,是社會發展的實際困境。馮蘭瑞說,“當時工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我們政研室去一些地方調查,出版了一本書:《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那時候實行平均主義,八級工資製級差很小。民間流傳‘四個一個樣’ :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快乾慢一個樣,乾好乾壞一個樣,乾與不乾一個樣。獎金取消了,計件工資也停了。缺乏激勵機制,大鍋飯無法調動人們的工作積極性,生產上不去,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在衝破“凡是派”的障礙後,思想理論領域仍有無數暗礁。在馮蘭瑞看來,1979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主持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思想解放的高峰。而且,從1976年四人幫垮台到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前半段,可以說是上個世紀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則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有過一段暫短的自由思想爭鳴。她近年來多次提到思想理論界的坎坷的開端——“階段風波”,就發生在理論務虛會閉幕不久以後。
在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上,馮蘭瑞與蘇紹智有一個聯合發言《論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文章後來在《經濟研究》的1979年第5期上發表。他們認為,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是一個漫長的時期,必然要經過發展程度不同的若乾過渡階段。該文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兩位“理論權威”指責他們,說此文“否定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多次開會組織批判文章,而且不許發表作者的反批評。直到中央文件闡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後,對這篇文章的指責才告結束。
馮蘭瑞在自己的最新文集中感歎道,歷史是不能忘卻的,人們往往“忽略了存在於平靜滄海萬頃碧波下的險灘暗礁”。本想塵封往事的她,近年來又拿起筆,記錄她曾經歷的思想戰場的刀光劍影。
按勞分配-勞動力商品-遷徙自由
社會主義有沒有失業、勞動力是不是商品,這樣的話題早已消失在今人視野之外。但在80年代,這仍是意識形態的禁區,而且影響到經濟體制改革的諸多舉措。馮蘭瑞很早就關注這些話題,闡述自己的看法。她是國內最早研究勞動就業理論並卓有成就的經濟學家。1980年發表的《勞動就業問題六議》等文章,指出我國現階段不可能消滅失業,1988年,她率先提出以勞動力的市場配置取代行政配置,並明確了勞動力的商品性質。
為了研究體制改革和勞動就業問題,馮蘭瑞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進行經濟調查。她記得有一次在蕪湖,看到那些“集體家庭宿舍”,每個不到20平米的房間住著兩三家人。各家一張床,床前掛著布幔“隔開”。床頭地上放著煤球和爐子、鍋瓢碗盞、腳盆、臉盆和便盆。職工居住條件之惡劣,慘不忍睹。幾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諸多不便,經常吵架和發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繪的貧民窟。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關心、去研究他們的勞動工資、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沒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
馮蘭瑞後來的研究工作,越來越進入社會現實層面。1993年,已73歲高齡的她,進入新的研究領域——社會保障。針對當時“多家分管、條塊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監督”的狀況,她提出應“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管理機構”。1996年她發表了《中國第三個失業高峰的情況和對策》,該文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國內外報刊轉載摘登和引用的達30多家,並於1997年獲《新華文摘》第一屆“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獎。在新世紀,她的研究從城市化、允許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深入到公民的遷徙問題。
我們在馮蘭瑞的口述歷史中穿梭了3個小時,85歲的她依舊神采飛揚。最後,她向我們,也向所有後輩提出兩個問題:什麽是社會主義,中國向何處去。這或許也是貫穿她的學術生涯的命題。
離開馮老的家時,我們在院子裡看到一片小竹林。她將自己的屋子稱作“倚竹齋”,典出清代詩人黃仲則的《都門秋思四首》。1972年,一家人陸續從乾校和邊陲返京。造反派走後,院子裡滿是垃圾、雜草和碎石,假山、涼亭、噴水池都破敗不堪。每到黃昏寂寥或中夜不寐,她就想起黃仲則的“寒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一次香山之行讓她發現,原來北方同樣宜竹,於是就在東側窗下栽種了一株毛竹。現在,竹已成林。
竹之高雅、剛正不阿、秀勁挺拔、無限生機,正是馮蘭瑞人品學識之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