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學家圈 胡景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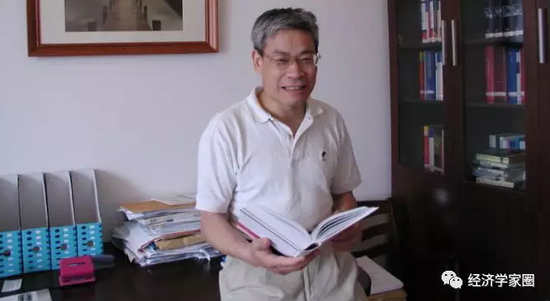 本文作者:胡景北,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教授
本文作者:胡景北,同濟大學中德學院教授
“近年,不少經濟學者主張創立中國自己的經濟學理論,典型的代表人物有清華大學的李稻葵和上海財經大學的田國強兩位知名經濟學家。”
遠離“創立中國經濟學”一類的扯談。
一位年輕朋友最近詢問我對田國強和李稻葵兩先生近來關於建立中國政治經濟學或者中國經濟學言論的看法。
我特地找了兩位先生的文章,即田國強的“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和李稻葵的“中國經濟學界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兩文的共同特點是要求建立中國經濟學,儘管他們所用的名稱不同。
其實,不管用較長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用較短的“中國經濟學”以及介於其間的其他名稱,中國只能有一種經濟學,不可能存在具有本質差異的比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學”。兩先生說法雖然不同,但也不謀而合地要求只有一種經濟學。
誠然,中國最近二十年存在互不理會的兩個經濟學圈子,一個以政治經濟學為名,一個以西方經濟學為名。根據兩先生的意見,這種狀況不應當延續到“新時代”。因此,我把他們的說法視為同一的建立“中國經濟學”說法,而忽視它們之間的次要差異。同時,由於他們分別用“基準理論”和“與西方自由經濟學理論分庭抗禮的經濟學理論”來表示他們設想的中國經濟學,我就用基準理論簡潔地表示他們所說的中國經濟學的含義。
對他們的文章,我的評論如下:
第一,兩先生儘管是著名學者,但在這個問題上他們不自量力。中國經濟學不是他們(當然更不是我)能夠討論或建立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如果真的能夠創立的話,它也僅僅能夠由領袖人物開創和建立。我們所能做的,是學習領會並在自己專長的方面再發揮發揮而已。兩先生喜談“中國特色”,但他們似乎並不了解中國特色,否則,他們不會忽略中國這一重要特色。
另外,他們對“新時代”似乎也不了解。比如李文談的都是舊事,而田文說的比如中國經濟學要做到的三個有利於,便與過去的“三個代表”似曾相識;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長官”的說法雖然不錯,但和“新時代”之“新”還是兩回事。
第二,更重要的是,我不同意中國經濟學的說法。在特指的情形下,人們不妨使用中國經濟學概念,比如技術變化的中國經濟學或者國企改革的中國經濟學等等。但就基準理論而言,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中國經濟學。
確實,中國經濟近四十年表現出色,中國經濟今後的路最好有理論指導。但解釋和指導中國經濟並不必然要求什麽“中國經濟學”。世界大部分國家經濟都有表現出色的時期也都有理論指導的要求,可世界上有幾個學者聲稱要建立本國的經濟學去解釋與指導之?
李稻葵舉例說亞當·斯密講的是英國故事、弗裡德曼講的是美國故事,因此中國需要中國經濟學來講中國故事。這是嚴重誤解。如果真是那樣的話,我們完全不必讀斯密和弗裡德曼。對李稻葵的這一說法,我想引用具有權威性的馬克思來反駁。馬克思在解釋他為什麽待在英國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時候說:
“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大家看,連馬克思這個德國人都在英國研究當時的經濟。為什麽?就是因為普適的經濟規律當時最典型地表現在英國,經濟學家因而在英國更有條件發現經濟規律並建立理論。馬克思在其著作裡大量列舉英國的例子,以揭示他所認定的經濟規律是如何在實際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如果我們像李先生那樣認定斯密是英國經濟學、弗裡德曼是美國經濟學,那麽,馬克思也只能夠算“英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了。
再舉一個具體例子。馬克思研究農業的時候,明確假定農業隻生產小麥,但他——至少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依然揭示了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規律。毫無疑問,中國南方的學者可以發展出有“中國南方特色”的農業經濟學,其中假定農業隻生產水稻、中國北方學者亦可以用麥子高粱兩產品假定建立“中國北方特色”的農業經濟學。但是,假設此類特色的經濟學沒有發現任何與馬克思不同的基本規律,這類經濟學充其量也僅僅是馬克思理論的一種推廣或發展。
如果我們參照馬克思的做法,那麽,在具有普適性的經濟規律表現得最充分最典型的地方,經濟學基準理論最容易發展出來。就此而言,過去的馬克思待在英國,現在的比如Acemoglu跑到美國,還有斯密和弗裡德曼留在祖國,都是試圖創立或發展基準理論的那些人的天才選擇,因為這兩個國家在他們的時代分別是經濟規律表現最充分的地方。當然,大部分人不是天才。我本人就是因為明白自己才學不夠才在畢業後決定歸國的(不過,我完全相信有些才華橫溢的經濟學者為了報效祖國而歸國)。
在其他地方,由於各種原因,經濟規律表現得不夠充分不夠典型。為了解釋那些地方的經濟,人們在基準理論之側,需要考慮導致經濟規律不充分起作用的各種因素。這是一個簡單常識,無任何可爭議之處。
我們需要懂得的是,如果這些解釋成功,第一它們不推翻基準理論,第二它們不足以建立新的基準理論(否則一個地方有一套“基準理論”,世界上就沒有基準理論可言),第三它們只是基準理論的應用和推廣。應用拉卡托斯(Lakatos)的概念,這些成功解釋只是為基準理論增加了輔助層,而非否定了基準理論。
宋錚曾經寫過“中國需要什麽樣的經濟學研究”文章。但他的文章常常被誤解。其實,讀一下宋錚等人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研究中國文章,就會發現那頂多是為所謂的“西方自由經濟學”的基準理論新塗了一個輔助層,而非證偽它們或建立新的基準理論。外國的例子,比如巴羅與格瑞利合作撰寫過《歐洲巨集觀經濟學》(Barro/Grilli,European Macroeconomics),布達與維羅茨寫過《歐洲背景的巨集觀經濟學》(Burda/Wyplosz,Macroeconomics:AEuropean Text)。他們在書名中加入“歐洲”字樣,是因為他們討論的是“富有挑戰性的特定環境”即歐洲環境下的經濟問題,即經濟學基準理論在特定環境下的應用,而非另立一套“歐洲特色”的基準理論。
第三,李稻葵為了說明中國經濟學的必要性,甚至斷言:“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在經濟理論上的‘貿易逆差’一定會帶來經濟政策層面的被動甚至敗仗,而經濟政策層面的敗仗一定會帶來經濟發展的倒退。”。他的這一斷言過於武斷了。
李稻葵舉的例子是日本上世紀末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失誤。可是他沒有說明日本的政策失敗和日本沒有發現經濟學基準理論直接有什麽關係,而只是說日本的失敗源於“日本經濟學研究長期落後於實踐”。然而,在這次失敗之前,日本經濟學研究(指基準理論層面的研究)更落後於實踐,更靠進口理論,但日本經濟增長卻獨樹一幟。
我們自己國家在四十年前,有著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頂峰的“政治經濟學”,全世界人民在學習紅寶書,經濟理論無“貿易逆差”可言,可經濟政策敗仗的情形卻屢見不鮮。而在最近四十年,中國進口經濟理論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李稻葵和許多“有識之士”抱怨不止,但中國經濟政策好像沒有什麽敗仗可說,反倒是經濟發展特別出色。因此,說不定正是大規模的經濟學“貿易逆差”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所以,我擔心的倒是,如果中國真的像田、李兩先生所說的那樣建立自己的經濟學,中國經濟政策可能又回到敗仗不斷的時期。
應當說,國與國之間經濟政策層面的被動甚至敗仗,是常見現象,和所謂經濟理論上的“貿易逆差”毫無關係,或者說,這些政策層面的正確和錯誤,絕大部分和基準理論無關,而和決策者的個人信念、手頭資訊與偶然因素關聯更大。其實,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是,絕大部分國家在絕大部分歷史階段都是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的“貿易逆差”國,因為任何時期的基準理論總是由極少數人在極少數國家內建立的,絕大多數人總是學習並採用他人的基準理論,絕大多數國家都必須進口基準理論;同時,絕大多數國家都因為進口基準理論而得益。換一個歷史階段,也許中國有個別人建立起那個階段的基準理論並被全世界其他國家採用,那也決不表示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相對中國就會失敗,否則中國人建立起的基準理論就達不到“基準”的標準。
第四,正如馬克思和波蘭尼等人強調得那樣,當代經濟是市場經濟。無論一個人在市場經濟之前加上什麽修飾詞,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徵是不變的。當代經濟學基準理論就是市場經濟的基準理論。誠然,當今時代依然存在著非市場經濟國家,例如現在的朝鮮或四十年前的中國。但即使針對這樣的國家,經濟學者也不可能另辟一套基準理論。他們所要做的是在市場經濟的基準理論之上,加上其他因素去解釋。例如,林毅夫先生對中國經濟在1958-1962年或在1980年前後表現的解釋之所以令人信服,便是根據這樣的原則做的。
我的年輕朋友亦說,斯密當年建立經濟學不是也要有利於英國君主嗎?確實,斯密是那樣想的。然而,斯密不要求比如賣肉者和買肉者為了君主利益而買賣。在斯密那裡,賣肉的為自己利益賣肉,買肉的為自己利益買肉 (我們很多人親眼目睹過此類現象:附近沒有配套商業的新建小區才開始入住,就有人趕來附近賣菜。這類現象就是斯密理論的源泉)。斯密只是相信每個臣民追求自己利益的行為最終會有利於君主。注意,在斯密那裡,賣肉者和買肉者皆與君主具有同等法律地位。比如英國的肉鋪沒有任何上級長官。如果按照中國的長官層次分級,則英國一個小肉鋪亦可以算 “正國級”,因為店主自己就是最高長官者。正是因為如此,後人才普遍認為斯密開創了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如果我們同意斯密的話,那麽,把君主改個名就夠了,新的基準理論不可能建立也不必要去建立。
如果不同意斯密理論,像田先生那樣需要長官或者像李先生那樣與“西方自由”分庭抗禮,那就確實需要新的經濟學。賣肉者和買肉者若在交易中被長官,這一交易便無法用市場經濟的經濟學解釋。可假使一個個企業和消費者在交易中竟然自由地不被長官,“有利於長官”和“反對自由”的提議便無法落實到微觀層次,兩先生的提議就會成為空話。因此,如果兩先生的提議要落實到經濟學基準理論中,中國確實需要一套新的經濟學,一套非市場經濟的經濟學。當然,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經濟便不是市場經濟。可是,兩先生真的主張中國應當走上非市場經濟路線嗎?我想,那些要求消滅私有製的人,多半不會相信他們。
第五,目前許多人指責“西方經濟學”不適用於中國,所舉的幾乎都是經濟政策層面理由,比如沒有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等等,而鮮有觸及基準理論的理由。與所有科學一樣,經濟學也有學與術之分。正如前面所說,經濟學的“學”不可能直接解釋中國或任何一國的經濟現象。就拿馬克思經濟學來說,它也無法直接解釋,因此人們才提出該理論的中國化或者在中國“創造性地”應用該理論,而不是建立一套新理論。
西方經濟學之所以成為市場經濟的基準理論,是因為它適合於西方、東方以及南方和北方,只要這些地方承認市場經濟。但是,在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任何國家,西方經濟學的應用都需要該國學者的創造性。打個比方,在長江和泰晤士河建橋都需要工程師的創造性,但中國工程師不需要新創一套力學基準理論,英國工程師也不能把“英國力學”直接用於建橋。毫無疑問,中國經濟學者在創造性地應用現代經濟學方面做得嚴重不夠,其中原因不在這裡討論。但是,如果著名學者不認真發揮自己在中國應用經濟學時的創造性,反而把創造性嚴重不夠的問題說成是經濟學本身的問題,那便既誤導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誤導青年學子。
此外,我還想指出,任何對中國最近四十年經濟成功的解釋都是不完全的,完美解釋的要求永遠不可能實現。我們看看對其他國家例如英、德國、美、日經濟成功的解釋,就會發現多種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解釋,而這些解釋所依據的基準理論還是同一種!因此,儘管我們需要更加令人信服的中國經濟的理論解釋或指導,但是我們必須明確,任何理論(即使真有所謂的中國經濟學)解釋和指導都有局限性,都不能非常令人滿意,更談不上令所有人滿意。而這樣的不滿意不應當僅僅成為理論工作的動力,它更應當成為任何理論都具有局限性的提醒劑:畢竟,把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理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且應當不會再來。
最後,我想起大約二十年前,當我最初擔任研究生導師的時候,我曾經要求我的學生遠離所謂的“政治經濟學”。今天,我對向我詢問的年輕朋友的建議依然類似:像“非禮勿視”那樣地遠離“創立中國經濟學”一類的扯談!!把精力專注在經典文獻和你特別關注的個別問題上!!
“夜話”,2018年第5期,2018年3月13日
責任編輯:張恆星 SF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