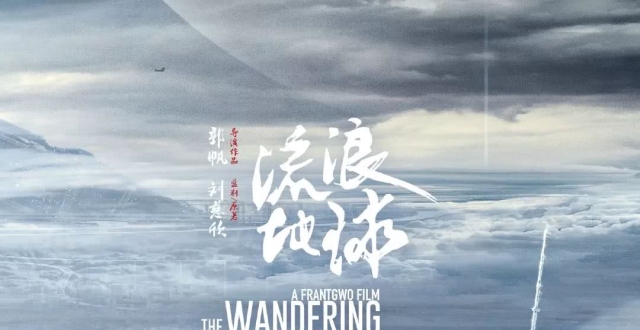無論我們多麽熱淚盈眶地感受到自己將要邁入中國科幻新世紀,國產科幻作品創作的困頓都是事實。這種事實掩蓋在《流浪地球》中投向木星耀眼的火光之中,讓人難以看清未來的方向:我們到底想要書寫的是向好萊塢大片進發的技術史詩,抑或是回歸科幻本源的社會探索?前者和後者到底是互相成就還是互相衝突?浮躁的IP化、影視化、爭奪大眾注意、努力通俗化的年代還能不能容下一篇創作的淨土?

《流浪地球》海報
引爆票房的《流浪地球》被視為“中國科幻元年”的誕生而獲得了大量關注。目前,許多觀眾對影片讚賞有加,觀察他們的評論可以發現,他們大多積極把《流浪地球》和中國科幻產業的發展捆綁在一起:“終於,輪到我們仰望星空”、“中國導演能拍出這樣的硬科幻,想想就激動”“工業化程度在國內前所未有”等形容出現在媒體與網民的評論裡。從這種敘事方式的廣泛流行和對《流浪地球》的跨時代意義的讚美中,我們得以窺見中國科幻是如何在高歌猛進的產業化進程中徘徊的。
《流浪地球》是災難片而不是科幻片
《流浪地球》改編自劉慈欣的同名小說,講述因為太陽即將擴張並發生爆炸,人類必須用推進器帶著地球逃離家園、前往比鄰星的故事。電影大幅度改編了原作的情節,將原作中描繪地球通過木星引力加速離開的幾個自然段進行大幅度擴寫成片。技術和特效方面,《流浪地球》確實已經在低成本預算中盡可能做到了國產影片中的較高水準,值得從工業角度加以讚賞,在此不作贅述,僅從內容上來談談這部在宣傳中一再強調“硬科幻”以及“中國科幻的突破”的作品在科幻性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瑕疵。

《流浪地球》劇照
就算不考慮原著中的假想(帶領一個海洋佔比超過百分之七十的行星飛離太陽系)是否合理,《流浪地球》在整體設定上也有著許多明顯的瑕疵。首先,也許是為了更通俗易懂,劇情中涉及的科學知識只有洛希極限和氫氣能夠助燃,其他複雜的設定(地球運動的原理,轉向發動機的設計,運動中的地球地表變化以及原因等等)都被帶過不提。其次,最後的高潮,拯救地球的方案更是十分敷衍地呈現:依靠一個年輕人想起自己小時候爸爸說過的氫氣可燃這種簡單的科學知識,就立即實施方案拯救地球,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實驗論證或者計算,例如:點燃木星產生的衝擊力是否足夠幫助地球脫離木星引力的同時保障地球的安全?點燃的範圍和方式應該是怎樣的?為什麽片中稱這個方案可行性為零,主角們卻一試即成功?
除此之外,片中只要涉及科學技術的地方,各種漏洞比比皆是:人類可以隨意采礦發展熱核聚變;駕駛方式非常傳統的運輸車;比現代還要落後的未來地下城安檢系統;緩慢前進還遭遇地震數次停擺但是十餘小時就能從北京開車到赤道的救援隊;毫無延時的空間站/地球通話;輕易被燒毀的飛船中控系統;能夠以1000馬赫的速度推開地球卻不破壞其基本結構,甚至只是讓主角破了頭盔而已的衝擊波……
科幻小說在科學上的嚴謹性一直被公認為是其區別於其他幻想文學(如奇幻、玄幻等)的最大原因。1926 年,最早的科幻雜誌Amazing Stories創始人 Hugo Gersback 提出科幻小說這個概念時,就將其描述為“關於科學家的小說”(fiction about scientists),認為其不涉及那些憑空捏造的科技,不濫用魔法與超自然元素,而是基於科學的合理預測。從這一點來看,稱呼《流浪地球》為技術黨推崇的“硬科幻電影”實在勉為其難。

《流浪地球》劇照
此外,《流浪地球》不夠“科幻”的原因還在於缺乏對科學技術造成人類社會影響的探討與思索。作為一部科幻電影,《流浪地球》只是把核心敘事簡單處理為“人類與宇宙帶來的災難相抗衡”。這是一部英雄史詩式災難片,其主線為:人類有難——試圖解決困難——解決失敗——英雄登場——英雄解決失敗——英雄嘗試其他方案,並作出犧牲——英雄拯救了人類,和別的好萊塢電影別無二致,幾乎可以嵌套進任何商業災難片的典型敘事結構。與《後天》、《世界末日》等電影一樣,它在巨集觀敘述上,一再展演具有重大意義的地標毀壞,凸顯災難的可怕;在微觀上,則著力描寫小家庭/團隊中的生離死別,用演員哭喊和音樂不斷煽情。
著名美國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認為科幻的一大意義是凸顯技術面前的人性:“它所關注的是人類對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所作出的反應。”但《流浪地球》完全忽略了人性衝突和技術帶來的殘酷抉擇。例如,保留人類文明傳播的可能性還是拚死一搏拯救低概率存活的地球這一重大抉擇,被煽情化地用一番過年團圓和父愛的演說化解。還例如,依靠抽簽決定是否能進入具有生活資源的地下城,代表著人類/政府選擇放棄那些沒抽中簽的數量繁多的人的生命,讓他們在寒冷的地表死去,但與此相關的複雜人性掙扎卻沒有得到絲毫展現。影片中人性只被粗暴地處理成兩種:失望放棄的與抱有希望繼續抗爭的人類,伴隨著“毀天滅地”的特效奇觀,共同迎接災難。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在科學設定上不夠完美,在技術和人性展現上都有一定瑕疵的災難片作品,被賦予了極大的美譽和意義。歸根結底,我們無法忽視,與其說這是對《流浪地球》的讚美,不如說是對中國科幻影視發展的讚美:人們期待中國影視行業太空科幻題材的發展已經很久,早已處在極度的渴望與焦灼之中。《流浪地球》作為國產電影,在選題和製作工藝上的突破則回應了他們的期盼。
這種期盼來自於中國電影產業進入了以好萊塢體系為標準的全球市場後所產生的一種結構性焦慮。科幻電影,是一種重工業、高成本、高概念的獨特電影類型,代表了電影工業的最高標準,多誕生於產業成熟的國家(如美國),它既關乎資金與技術,也關乎國家自信。另一方面,作為舶來文化的科幻能夠得到西方國家的認同和理解,成為了中國文化輸出,在文化與價值觀上尋求更高的認同感與地位的完美工具。因此,科幻不可避免地和愛國情懷,民族成功捆綁在一起。
事實上,從2015年《三體1》奪得雨果獎之後,開始積極發展的中國科幻產業也積極利用著這種民眾情緒打造宣傳熱點,大量科幻IP被影視公司搶購並投入製作的同時,投資方、科幻從業者和媒體每一年都會進行激動人心的科幻“元年”敘事,試圖證明科幻的產業化發展為文化騰飛帶來了巨大成功。

《流浪地球》劇照
瘋狂發展的中國“科幻”
從產值和作品數量上來看,中國科幻文化在轟轟烈烈的產業化過程中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期。南方科技大學發布了《2018中國科幻產業報告》,2017年中國科幻產業產值超過140億元人民幣,到了2018年,僅上半年產值已經接近100億元。值得注意的是,高額產值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由科幻影視所貢獻的。
2017-2018年,共有30余部國產科幻網劇上線,其中單集平均播放量在500萬以上的有9部,出現了《鎮魂》、《顫抖吧,阿部》、《天意》、《端腦》等社會影響力較大的作品,產值高達16億元。同期網絡大電影共上線 47部,用戶付費約11億元。同時,還不斷有新的科幻影視作品在2019年上映,例如和《流浪地球》一起上映的《瘋狂外星人》以及即將在暑期登場的《上海堡壘》等等。
同時,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些影視作品的尷尬之處:錢莉芳同名小說的科幻劇集《天意》曾引起極大的關注,其影視化改編被稱為“東方科幻的一次大膽嘗試”,但實質上卻讓不少原著粉絲們大失所望,認為這是一部被篡改得亂七八糟的狗血偽歷史劇。而改編自劉慈欣小說《鄉村教師》的《瘋狂外星人》則已經完全脫離原著,不再有嚴肅的外星文明思考,主要賣點為爆笑荒誕的市民生活與明星演員陣容。而其他的網劇就更無法到傳統科幻迷的認同,不過是披著科幻外衣的其它種類故事:用雷射槍代替了普通武器的普通冒險作品,用機器人代替了其他種族的跨宗族戀愛故事,用時空歷險解釋穿越回古代的瑪麗蘇意淫……
這些“科幻影視作品”都缺失了科幻應該秉承的核心價值——基於現實和技術,對人類,世界形態進行捕捉和重述,用替代現實(alternative reality)來描繪過去和未來。這種推斷與前瞻,創造了一種隻屬於科幻的語境:不僅可以突破對人類、人性的認知,也可以突破對時間、空間的定義。例如《美麗新世界》中暢想的技術改變思維與情緒的社會,《2001太空漫遊》思考的宇宙與人類生命根源,《我,機器人》拷問的人性和倫理定義……
確實,要為“科幻”定下一個確切而無可爭議的定義和標準非常困難,但國內目前大多數科幻影視作品幾乎不涉及任何對技術以及技術所帶來的社會的想象也是毫無疑問的。就算把它們當中其中的科幻元素替換成魔法、超能力、修仙氣功,這些故事也照樣成立。正如劉慈欣曾經說的“讓我們剝開科幻這顆洋蔥:最外層是那些把科幻作為外衣的武俠和言情;然後是把現有的技術進行超前一步的應用所產生的故事;再向裡是可能出現的技術和世界。”換句話說,並不是只要把故事背景放在太空就是科幻作品,只有當科幻元素是整個故事的核心,圍繞其進行思想與情感的表達的作品,才能稱得上是科幻作品。
但在積極產業化,人人都想從“科幻”這一文化熱點中分一杯羹的情況下,層出不窮的科幻組織和投資者不斷入局,“掛羊頭賣狗肉”擦邊球的行為也繼續如火如荼地進行。就在去年11月23日召開的我國科幻領域唯一的國家級會議——2018中國科幻大會上,產生了極為荒誕的場景:《王者榮耀》被評為最佳科幻遊戲,而幾乎沒有任何科學基礎的“修仙機甲”類網文竟然也被納入科幻範疇……
當然,也有人把這些“泛科幻”/“擦邊球”理解為引導大眾對科幻的興趣,扶持科幻產業發展的輔助品。然而實際上,我們既難見到多少通俗影視的觀眾由此對看科幻內容產生興趣,也無法忽視作為科幻發展基礎的內容生產並不樂觀。就在中國科幻大會上,銀河獎最佳長篇獎出現空缺,其他獎項如最期待IP獎、特別獎、原創圖書獎等都頒給了《上海堡壘》、《驅魔》、《流浪地球》等舊作。與之對應的是,在2017年100余億的科幻產值中,科幻小說閱讀市場產值總和僅有9.7億元。這一系列現象都揭示了繁花似錦,人人都在談IP,周邊商品大行其道的科幻產業底下巨大的創意空洞。就像劉慈欣所稱,今天真正的科幻讀者依舊不多,寫科幻的估計有一萬多人,有名氣的二三十人,有影響力的作品更少,中國科幻發展的“黃金期”也許根本沒有隨著產業化到來。

《流浪地球》劇照
困頓的科幻創作
在科幻世界貼吧,有網友討論到,18年的一場科幻新書發布會上的互動提問環節,一位資深幻迷向《科幻世界》主編姚海軍先生提問:“十幾年前雜誌上何夕、王晉康的科幻小說即使拿到今天都讓人覺得很好看,但為什麽這幾年雜誌拿不出那樣好的作品了?為什麽《科幻世界》越來越難看了?”
這個尖銳的問題並不是第一次被讀者提出。如果以“《科幻世界》/中國原創科幻為什麽越來越難看了”為關鍵詞,可以在網絡上搜索到成千上萬個帖子。參與討論的人往往都是對科幻情有獨鍾的老幻迷。有意思的是,近幾年,就在科幻雜誌與圖書的發行量不斷增長的同時,這樣的問題卻越來越多地被提出來——人們從嫌科幻不夠看到嫌不好看了。
綜觀近幾年的科幻作品狀況,確實可以看到蓬勃之下的某種困頓。虛浮行業中的泡沫下,這幾年科幻作品的出版的確增多了,但是有限的增量中,推出最頻繁的就是已經成功擠入通俗小說潮流的不同版本的《三體》以及劉慈欣的其他小說精編。新的長篇原創小說實在是難得一見,讀者難以尋覓到佳作。
中國科幻創作中,年老和年輕作者出現了嚴重的斷代。十餘年前,不只“何慈康松”(何夕、劉慈欣、王晉康、韓松)各有特色的科幻寫作模式令讀者津津樂道,還有一批作者在《科幻世界》上大放異彩:星河、潘海天、柳文揚、蘇學軍、劉維佳、凌晨、趙海虹等為代表的 70 後科幻作者創作出一批優秀的作品。這些科幻小說在形式上摒棄了老派在中國科幻小說的科普說教模式,更接近同時期歐美科幻小說的風格,在題材選擇上更加寬泛,平行宇宙、外星人入侵、時間旅行、虛擬現實、克隆技術等以往很少涉及的題材在他們的作品中大量出現。同時,由於所處時代背景的原因,他們往往對迅猛發展的科技文明帶來的全新生活體驗抱有浪漫想象的同時,又懷著對現代進步的質疑,對都市生活、工業景觀和機械化的厭棄,以及對失落精神家園的懷舊感傷之情,乃至上升到對人性的終極拷問,這一時期是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發展飛速的繁榮時期。
2005-2006年左右,70 後科幻作者群體逐漸淡出了中國科幻小說創作的前沿,或主動(如潘海天、劉維佳等逐漸退出科幻文學創作領域)或被動(如柳文揚身故)地告別,即便選擇繼續堅守者(如星河、凌晨等),無論是在創作數量還是影響力方面,較之以前都有所下降。之後接力的80後科幻作者則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狀況,夏笳、陳揪帆等雖然有名但作品不多,其他80後作者則少有知名作品。
目前,《科幻世界》對新一代作者依舊保持著強大的扶持力度,彭思萌、阿缺等作者都得以一期發布多篇文章的待遇,楊晚晴、查杉、索何夫、柒武等作者也有多次發表機會。相對比下,“老牌作者”的文章頻率降到偶爾發表。但這樣煞費苦心的“捧人”力度並沒有帶來多少成功的作者或作品,普遍讀者都開始發現優秀科幻文章稀少,期與期之間內容品質差距大。
另一些機構試圖用Mook的新形式為科幻作品發表開辟新路線,但內容都各有缺憾,並有湊數之嫌——“未來事務管理局”的《時間不存在》有幾百頁,短篇小說數量有限,附贈的是大量枯燥的訪談。“湛盧文化”的《十二個明天》刊登了劉慈欣的新作《黃金原野》,但不只這篇數年磨一劍的小說讓不少讀者失望不說,匹配的書評更是十分不靠譜。編輯部邀請了一幫顯然不怎麽讀科幻的名人來做點評,結果有人記錯了經典科幻的作者,有人弄錯了主角,還有人點評了《三體》,而且竟然還有“微軟小冰”的一篇囈語般的點評。
無論我們多麽熱淚盈眶地感受到自己將要邁入中國科幻新世紀,國產科幻作品創作的困頓都是事實。這種事實掩蓋在《流浪地球》中投向木星耀眼的火光之中,讓人難以看清未來的方向:我們到底想要書寫的是向好萊塢大片進發的技術史詩,抑或是回歸科幻本源的社會探索?前者和後者到底是互相成就還是互相衝突?浮躁的IP化、影視化、爭奪大眾注意、努力通俗化的年代還能不能容下一篇創作的淨土?沒有人知道答案,但的確有人感到了危機,劉慈欣說“ 現在,科幻文學有一種無意識或有意識的‘去靈魂化’,這就是我所說的科幻所面臨的更大威脅,它在從根本上動搖科幻存在的基礎……當我們把目光從星空收回,投向怨男信女們可憐巴巴的小心靈時,科幻離死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