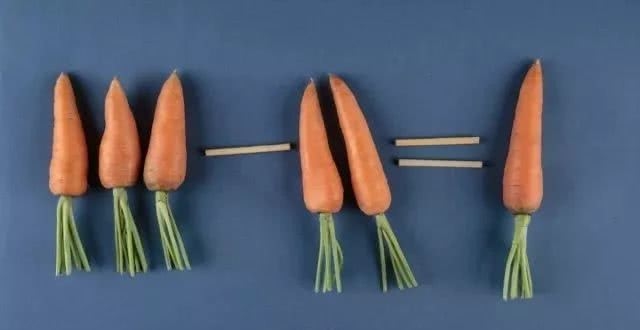文|龔菁琦
專注力
這是一種會變化顏色的頭環,分別戴在三個小孩的前額,像故意反著戴的耳機。
紅色代表忘我,黃色代表集中,綠色代表走神。燈的顏色一換一閃,在腦門上格外顯眼。一根電線把頭環跟電子看板相連,螢幕上的數字隨著孩子們的專注力的升降而變化,35以下是走神,65以上是高度集中。
5月的一天,北京建國飯店舉辦的頭環招商會上,小孩兒坐在台上,台下呼啦圍著幾百號人,他們是家長、培訓學校的老師、投資機構的老闆、對腦科學感興趣的醫生,甚至還有區塊鏈創業者和軍工廠的銷售代表。
「大家看,馬上60了。」穿著鈷藍色西服的韓璧丞,綴著一個領結,邊看螢幕邊念著,「58,59,60……這個很專注,已經到67了。」數字達到峰值時,他的手在空中揮了揮,像一個樂隊指揮家,撥動著數字的節奏。
韓璧丞是頭環製作公司BrainCo的CEO。公司給自己的產品取了一個貼切的名字:賦思頭環,意在提高人的注意力。他們做的是一門測量專注力的生意,因為與學習密切相關,最先觸及了老師和家長。
教育培訓機構校長卞玲認為,以往要判斷一個學生是不是走神都是靠模糊的經驗,要麽兩眼發直,要麽交頭接耳,有時很難發覺,頭環是一項偉大的技術,「解放了老師」。
但是,自頭環誕生以來,也一直伴隨著質疑。一方面,在監控人的專注力時,它到底算不算一種變相監視?商業應用的邊界在哪兒?另一方面,這種用外力提高孩子學習能力的方法,是不是一種過度培養?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反對完美》一書中提到過科技發展帶來的倫理困境,試圖用萬能的金錢和技術,把自己升級,這是以生活意義和根本幸福為代價的。
但對於頭環的發明者來說,並不認可這些質疑的合理性。
在招商會現場,韓璧丞演示了頭環的奇妙功效。他示意幾位小朋友配合他,「閉上眼睛放鬆一下,就是冥想,溜個號,看看誰放鬆得最好。」
「大家看這位已經降到50多了,這個已經30多了。」台上頓時一片綠色,台下有人拍照,有人驚歎。韓璧丞咧嘴一笑,「在課堂上只要溜號,或者打個盹,我們全部都知道。」

降維打擊
15歲的李坤是北京一所知名中學的高一學生,她是頭環首批志願使用者之一。
2018年10月,她從一位同學那裡得知一項哈佛的黑科技,「一個頭環,能提高注意力。」出於羨慕同學居然認識「世界頂級學府的牛人」, 李坤也想了解哈佛研究員是什麽樣。她加入了一個40人的微信群,報名了實驗。幾天后,頭環快遞到了她家裡。
她沒有想過去網上搜評價,也沒多問同學,馬上拆開包裝就戴上了。媽媽提醒她注意,可能會有異塵餘生,她倒是不怕,「最壞無非是變傻一點。再說,哈佛的技術能差到哪去呢?」
每次戴上頭環,通過前額和耳後的柔軟凝膠,李坤總能感覺到些許緊繃感。耳朵裡會傳來一陣很細的嗡嗡聲和嘶嘶聲,說不清是電流還是磁場的聲音,她也無法找到一個形容詞,「不是疼也不是暈,是一個東西在那裡監測。」
那時頭環還沒有正式投入市場,但韓璧丞已經研究它7年了。作為頭環的發明者,32歲的他有一張絡腮鬍子包卷著的圓鼓的臉,笑起來一副憨態。常有人稱呼他「韓博士」,這是因為他另一個身份是哈佛在讀博士生。
回溯創辦公司的起因,他的解釋是對科研的癡迷,具體來說是對材料研究的執迷。在一段從未對外公開的視頻裡,韓璧丞在哈佛大學的地下室做實驗,他穿著白襯衫,背後立一個擁有全身科技感外殼的機器人。他兩眼朝向前方,手慢慢抬起,機器人也跟著抬手,他手指轉圈,機器人也照著做。
「比鋼鐵俠還牛。」韓璧丞對《人物》記者強調,鋼鐵俠只是機器控制,用一套動力系統,而他完全依靠神經接口,用腦念去控制機器。然而,打通大腦與機器需要特殊的材料做銜接,他一開始就是為了研究這種凝膠材料而費盡心思。
2011到2013年,韓璧丞每天腦子裡想的都是怎麽把電極材料研究出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被邀請參加紐約一個創業大賽,上台講了12分鐘,就拿到了10萬美金,公司也應聲啟動。這之後,韓璧丞的研究駛入了快車道,2015年凝膠材料終於被攻克。
賦思頭環隨後誕生。2016年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科技展覽會上,韓璧丞戴上頭環,用意念控制了40多個智能家居設備,讓人看得眼花繚亂。
他也曾給投資人展示,當別人想拿手去開門,他把頭環一戴,一想,門叭地打開了,投資人嚇了一跳。技術解釋起來自然特別費勁,這邊和投資人演示好技術,講好了原理,回頭投資人就和別人說,「今天上午遇見一大師,有特異功能。你聽過嗎,腦控。」
但是,前金立手機副總裁俞雷,卻很相信這項技術。2018年11月,他第一次接觸頭環時就被這項技術擊中了。「太震驚了。」當時正在哈佛參觀的他立刻斷定,「這是千億級的生意。」
他決定加入這家創業公司,負責商業落地。俞雷的到來,標誌著公司商業化的開始。降維打擊是他給出的方案,在俞雷看來,選一個好的賽道,一個正向形象的場景非常重要。「一幫哈佛的學霸幫你做出這樣的東西,告訴你學習成績應該怎樣提高。上座率肯定不會低。關鍵是要非常正面、積極,教育最符合這一點。」
公司高層意識到,專注力是家長和老師的痛點。如何售賣專注力,首先得有讓家長感興趣的說法。韓璧丞抓住了這一點,他常常從一個場景說起:每個人大腦都是由860億到1000億個神經元所組成,大概兩萬多個基因轉錄而成,大腦和大腦之間沒有太多區別,「但成績之所以有所區別,就在於學習狀態和認真程度。」
專注力的行銷方式也各式各樣。BrianCo會賣家長一份孩子的專注力報告,也可能是培訓班裡的招生廣告詞,「每提高1%的專注力,能夠提高6%的閱讀成績和8%的數學成績。」在講求特色的輔導班市場,專注力的賣點意味著能讓孩子高效率地做完作業,「這是家長們最喜歡的。」俞雷說。
「說大了,它能提高一代人的學習能力和工作狀態。相當於培養一批學習工作效率超級高的特種兵。把一個國家的戰鬥力都提來。」韓璧丞覺得這件事意義重大,「就算做廚師,專注的廚師也會比粗心的廚師做飯做得好。」

好玩的事
李坤試戴頭環後,發現自己的注意力和一棵小樹的成長有關。手機連上頭環,只要盯著螢幕上的樹,樹會從小幼苗長高,開枝散葉,數值也會蹭蹭增長。不長時,她就得使勁盯著。
她認為這棵樹很有靈性,似乎能猜到她在想什麽,「比如我餓了,等下吃什麽,一想數字就往下掉。必須什麽都不想,樹是你腦袋裡唯一要關注的影像。」
她每天都沉溺於讓樹成長的遊戲裡,「太神奇了。」看完幾分鐘樹成長後,再戴著頭環繼續做作業,按要求要記住一種專注的感覺,她形容「似乎就是不太知覺身邊發生什麽」。
10多天之後,李坤感覺到發生很多變化。有一次媽媽進來澆花,她戴著頭環寫作業,媽媽出門後她才發現水滲到腳邊。當時書桌就挨著放花的窗台,而往常只要一推門,李坤就能聽見。此外她也發現一些上課時的改變,往常跑步過後再坐回教室,半天心都飄著,但現在有幾次,她能感覺到坐下時全世界安靜下來。
盯著小樹的遊戲,並不只令李坤一人著迷。2019年4月,頭環項目開始進入學校、培訓機構,五十六中就是其中一個。五十六中在北京本來籍籍無名,在BrianCo組織觀看了一次現場專注力表演之後,學校領導打消了技術上的顧慮,頭環順利進入課堂。
學校選中了初一一個班的數學課堂,試驗頭環效果。在發放頭環前,學校給學生們開了一個培訓會,並一一短信告知家長。班上只有三個學生家長認為「沒有必要」,或是「擔心有異塵餘生」,數學老師魏思回憶,「學生並沒太多疑問,大多當成一件高科技的事,好玩的事。」
第一堂課戴上頭環時,大家像佩戴勳章一樣格外專注。有孩子不時從手錶映出的影子看頭上的顏色,「要看兩三次」,還有學生叫身邊人看頭上是什麽顏色。魏思記得整堂課大家都非常興奮,專注力平均數值很高,「課堂裡一片紅」。
上課期間,只有一個學生舉手問,「這個專注力數據會發給家長嗎?」台下哄堂大笑。下課後,學生們都爭相去看自己的數字,像看遊戲排行榜一樣,「都想爭當專注力第一名。」
久而久之,這個班的數學課上課前,「看今天教室裡紅色多少」,就成了老師和學生們共同的遊戲。30多位學生一起盯著小樹看,當他們的頭環紛紛轉成紅色時,課堂裡就會一片亢奮。

學生的秘密
頭環試戴兩個星期後,李坤得到來自歷史考試的反饋。一天,歷史老師神神秘秘,讓全班猜猜第一名是誰。李坤並沒多想,她對歷史、地理這類「只需背誦」的科目並不感冒,從不刷題,課後也不跟老師交流太多,成績也從不搶眼。
但是,當老師念出她的名字,全班「哇」的一聲。在這之後,她是歷史考試的常勝將軍,她感到「有點莫名其妙」,後來想或許是「頭環」的作用。
歷史課考高分的邏輯並不複雜,課上老師會標出記憶重點,記住則能得高分。以往她認為回去背誦即可,並不太聽課,聽過她也不會去記憶。她形容最近上歷史課時,能靜下心跟著老師思路走,這些重點被鑲嵌在記憶中,不需要再複習,在考試時總能一個個拔出。
成績變好後,李坤沒有和任何同學提起過「頭環」。她澄清不是故意隱瞞,是不知從何說起,「跟他們說現在我可以控制我的腦電波?有一個專注力?人家會覺得你這是一個氣功。」
「氣功」、「巫術」,或者「下一代技術」,在研究腦科學10年的紐約州立大學博士杜乾看來,這些詞匯都是大眾對神經科學的誤解。她認為,李坤的成績和頭環本身關係不大,至少一半功勞是她自己。「在腦科學領域有一個專門的詞,叫神經反饋訓練。人腦本身很聰明,能調動可塑性去適應機器,從而得到訓練、提高,就好像你請一個健身教練,最後身上的肌肉還是你自己長出來的,他們只是提供所謂的科學訓練方法而已。」
科學的訓練方法是基於能夠準確測量專注力,以獲得精準的神經反饋。但測量的理論基石100年前就已存在,「如果說走進神經科學現實應用的大花園,腦機接口技術,只是大花園裡踏上的第一塊石板。」杜乾對《人物》記者說。
過去戴上電極帽,上面有8到128個不等的電極,塗上滿滿的導電凝膠,緊貼頭皮,不管美不美觀,做完實驗就得洗頭。杜乾說,現在的頭環把以上一系列都簡化,通過一個穩定性高的凝膠點,像一個麥克風一樣支在前額,能聽到大腦裡發出的微弱聲音,「這是腦機接口技術最大的貢獻」。
僅是這一點微小的創造,一大波公司開始做測腦電波頻率的產品。美國有muse等多家腦機接口公司,頭環也已經成為矽谷成功人士的生活標配。與BrainCo在國內用於教育不同,國外大多用頭環來輔助冥想。
一項技術能不能成為生意,需要看解放多少生產力,這是人工智能領域一個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在BrainCo公司的創始者們看來,頭環能夠解放老師的監督,但有時候數據也不能反映學生的真實狀態。
自從五十六中數學課堂上使用頭環後,平時不易察覺的細節都開始放大,比如,每次老師要求全班同學放鬆冥想時,一位學生每次都沒做到,「非常明顯,大家頭上都是綠色,只有他是紅色。」顏色在這裡代表著豐富的含義,紅色是緊張、認真,黃色是正常,綠色是渙散、走神。常駐班級的BrainCo公司代表樓小燕說,那個學生「性格太叛逆了」。
此外,緊張、局促等情緒在課堂上也變得無法掩飾。一位學生在被點名回答問題時,臉上滿不在乎,但頭上一直紅色在閃,說明他很緊張。
頭環使用時間越長,更多秘密就浮現越多。魏思老師從沒想到,班裡數學成績最好的一位學生,上課走神次數最多。有時嘴裡還應和著老師的問題,但頭上卻是綠色。
「太簡單了,有時候覺得沒有必要聽,很容易就溜神了。」這位學生告訴《人物》。一個讓人驚訝的現象是,他在家裡佩戴頭環的數據最高,每次專注力都達到60分以上,「說明在家裡認真學習,不想讓人知道。」
此外,一位平時「老實憨厚」的學生,數據常讓老師也看不懂,他連續好幾天都是綠色,跌破平均值,但去看他課堂上的表現,眼睛緊緊跟著老師走,沒有半點分神。魏思沒有想明白是怎麽回事,樓小燕提示她去看看這位學生平時的作業,不料正好發現他在抄襲。
「人設都崩塌了。」魏思回憶,自此對這位學生有另外一種認識,「總之不那麽純粹了。」

數據隱私
成績提升後,李坤成了賦思頭環的「活體廣告」。
她的媽媽陳夢也成了頭環的代理商,「決定孩子成績和效率的,根本不是努力,是專注。」在招商會上,陳夢已經有一套很有說服力的說辭,「就像舉重,你知道吧,專注力是越練越好,從舉100kg到200kg,專注力從堅持20分鐘到堅持1小時。」
她稱自己最懂「客戶需求」,把女兒成績提升的故事發到朋友圈,立即有家長來打聽,還有人直接打款。「我們是在培養一群超級學霸啊。」她回復對方。
在老師、孩子和家長三者中,最期盼成績提升的永遠是家長。頭環推行過程中,在家長中遇到的阻力最小,《人物》採訪多位家長髮現,他們提到最多的是「有沒有異塵餘生」,「會不會用腦過度」。
一個不被家長注意的問題,是那些涉及每個孩子專注力的信息,到底該如何處置?樓小燕說,北京五十六中的頭環試驗課結束後,專注力數據不會傳到互聯網,而是由學校處置。
但隨著商業化的推進程度加深,腦電數據隱私也將成為新科技帶來的隱患。《腦機穿越》一書就提出了擔憂,「腦聯網」或者「腦機接口」會帶來可怕後果,某個無所不能的「老大哥」,或者技術超群的天才,有朝一日可以控制整個腦機數據世界。
韓璧丞認為擔憂暫時不會出現,公司對數據隱私保護非常嚴格。但他承認,腦波數據具有越來越高的價值,孩子做的每一個事情可以全知曉,打遊戲時是這個波形,看電影時是這個波形,掌握了這些數據,也是控制了大腦的某一部分情況,會知道不該知道的很多的秘密,「實話實說,我覺得這個以後會有壓力。」
臨近學期尾聲,在6月的一堂課上,五十六中學生們的頭環黃色居多,紅色和綠色一樣,是個位數——這顯示大部分人正常,忘我和走神都是極少數。
學生們對於頭環顯示什麽顏色已經不太感興趣了。由於沒有懲罰措施,課堂紀律和以往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數學老師魏思能準確知道一堂課裡什麽時候學生最認真,有一次她敲著黑板喊,這道題錯誤率最高,刷的一下,全班同學的燈大部分紅了。之後這一招常被她使用。
學生們開始把專注力當成遊戲玩,都在爭取排名靠前。有位學生一上課就打開文具盒,把所有的筆一支支排好,擦乾淨,再一支支拿起來轉,一堂課下來,頭上都是紅色,專注力值全班最高。還有學生發現,如果想要分數快速提高,「你就盯著一條裂縫看。」
頭環實驗的最後一天,長期駐扎學校的樓小燕準備了哈佛大學的文化衫、耳機等禮物,獎勵給注意力排名靠前的孩子。當孩子們上台領獎品時,她發現,頭環一個個由黃色、綠色,都變成了紅色。

(應受訪者要求,卞玲、李坤、陳夢、魏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