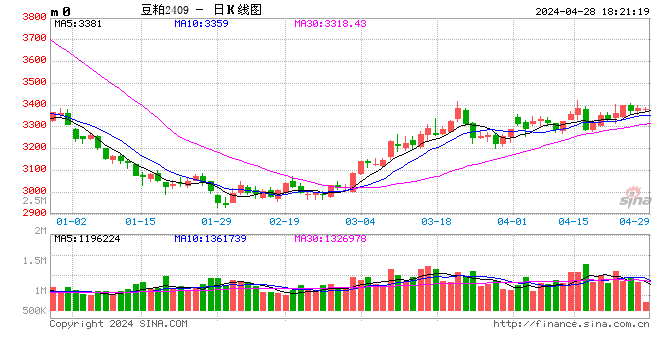丁戊奇荒:
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
郝平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313頁,42.00元
文︱馮志陽
丁戊奇荒(1877-1878年)剛剛過去,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便開始著手編撰《山西通志》。《通志》中的第八十二卷名為《荒政記》,絕大部分篇幅用於記錄這場被時人稱之為“二百年未遇”的“奇災”。“二百年未遇”顯示了丁戊奇荒的嚴重程度,但《荒政記》卻認為,丁戊年間的災情,“略與道光丙午(1846年)相仿”,“即陝豫並歉,亦無甚異”。兩者的差別在於,丙午年間“但借倉緩賦,不煩公家之賑,並無大傷”;而丁戊年間雖“發帑截漕至竭天下之財,幾於不救”。說到底,丁戊奇荒關鍵不在於氣候異常帶來的災情本身,而在於災荒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因災致死人數的多寡上。據災荒期間先後供職於天津海關與北京總稅務司署的馬士估計,整個中國直接死於饑荒的人數“不會少於一千萬人”。這種規模的死亡,在中國乃至世界有文字記載的災荒史上,可謂空前。
丁戊奇荒為什麽會奪走如此之多的生命,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核心問題。《荒政記》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只是歎道“豈非時使然歟”?李文海、夏明方等學者認為,這個“時”應該是近代以來國內封建主義日趨腐敗的政治制度和殘酷的經濟剝削,是國外資本主義日趨加深的經濟侵略。所謂“天災造成了人禍,人禍加劇了天災”的解釋模式,長期以來是學界解讀丁戊奇荒的主流觀點。這種帶有強烈時代印記與濃烈意識形態色彩的觀點,與歷史事實之間可能存在著不小的距離。主持山西賑災的曾國荃曾於災中致信友人表示,晉省“統府、廳、州、縣各班,本僅二百餘人”,而先後身故的“正佐教職已逾百二十餘員,多半歿於差次,率皆無以為殮”。楊國強先生在論述丁戊奇荒的文章中認為,這些歿於“不避艱難”的地方官做到了死而後已,折射了儒學民本主義的最後一點余暉。郝平博士的最新專著《丁戊奇荒:光緒初年山西災荒與救濟研究》(下文簡稱《丁戊奇荒》)用更為詳盡的史料(各府、州、縣地方志與郝平通過田野考察收集到的竹枝詞《丁醜大祲清官譜》等),通過對上自巡撫、下自基層官員群體的考察,呼應了楊國強先生的論述。這表明從吏治造成的“人禍”是無法解釋丁戊奇荒的悲劇的。
《丁戊奇荒》是大陸史學界關於丁戊奇荒研究的第一本專著。在作者看來,清政府的財政空虛和社會動員乏力是賑濟最終失敗的主要原因。這種觀點似乎更具解釋力,但我們無法否認,儘管國庫極度空虛,清政府仍然通過各種方式籌措了大筆資金、糧食用於賑災,尤其是對山西省。據不完全統計,清廷共向山西調撥漕糧七十餘萬石,直接劃撥的各類款項共三百十七萬兩,此外還允許山西在各省設賑捐局勸捐,又籌得一千零二十九萬兩,即《荒政記》所言“發帑截漕至竭天下之財”。就此而言,也很難說國庫空虛和清廷的社會動員乏力是賑濟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不管怎樣,國家權力畢竟通過各種管道向山西注入了上千萬兩的賑災資金。
丁戊奇荒又被稱為“晉豫大饑”,表明山西與河南是受災最為嚴重的兩個省份,但從人口損失情況來看,山西則遠甚於河南。河南在饑荒中餓死的人數有一百八十多萬,而山西餓死的人數則有五百五十多萬,是河南的三倍多。當時山西的總人口是一千六百多萬,即每三個人中便有一個餓死。在重災區,致死的比率更是驚人,所謂“民死十之七八”、“戶口損三分之二”、“戶口已減十分之六七”等記載在這些重災區的方志中比比皆是。為什麽國家向山西提供了最多的救災資源,而山西的人口損失卻是最為嚴重的?《丁戊奇荒》重點不在於回答這個問題,但該書提供的豐富細節卻不斷提醒我們注意這個大量存在卻很容易被我們忽視的簡單事實:交通運輸。作者幾乎在論述每位救災官員時,都會以相當的篇幅述說他們面對運輸困境的措施與無奈;在記錄李提摩太對於災荒的反思時,更是首先提到“糟得不能再糟”的交通運輸。遺憾的是,他並沒有辟專章討論交通運輸對賑災的影響。
山西災民的大批死亡,最直接原因即在於山西惡劣的交通條件。河南的人口損失之所以遠小於山西,也是因為賑糧運抵河南比運抵山西要容易得多。且不說將兩湖稻米運送到河南災區較為方便,即使是朝廷調撥的山東漕糧,運往山西的費用至少是河南的四倍。山東漕糧運往河南,有水運可走,而運往山西,不但水運較少,平坦的大道也少。由於天乾久旱,河道多乾涸,水運時斷時續,嚴重影響了轉運效率。但河南多屬平原,大道平坦,陸運較山西方便。山西群山環繞,無論是朝廷調撥的漕糧,還是官府或民間採購的賑糧,都必須穿越重重山路才能入晉,入晉之後,大半仍還是崎嶇山路,不得不主要依靠牲畜馱運、手推小車乃至肩挑背扛,這些都導致運糧抵達災區的成本非常高。曾國荃曾在奏折中表示,“漕米十二萬石分運晉南災區,共需運費在百萬兩以外。”以此估算,則七十餘萬石漕糧便需銀六百萬兩。時人的諸多記錄也都顯示,惡劣的交通條件導致國家權力籌得的上千萬兩賑銀只有少部分用於購買糧食,大部分均充作運費。
高昂的運費還在其次,更致命的是大量的賑糧由於極其惡劣的交通條件根本無法及時運抵災區!災荒發生後,官方、民間調撥、採購了大批糧食,但“米至天津竟為止境”,即糧食的來源不是問題,問題是交通運輸的艱難使得賑糧“往往滯於中途,萬難速到饑民之口”。襄助山西賑務的李用清在《大荒記》中寫道:“汾州之永寧、臨縣、寧鄉,春月分撥賑糧,八月尚未運到,而陝西韓城縣之賑糧,三年八月初四日在河南陝州之會興鎮裝船,四年正月十三日始運到永濟縣之小裡鎮(距會興鎮不過二百餘裡)。”遠水救不了近渴,以這種速度運送救命的糧食,對於賑災而言,根本是緩不濟急,起不了多大作用。學者王金香指出,清政府給山西調撥的數十萬石漕糧,從光緒三年夏調撥後,直到光緒四年春才有少量運到,大批賑糧運到災區則是當年冬天的事了,此時災民已大批凍餓而死。
在鐵路修進山西之前,山西與外界的交通困難是一直存在的,那丁戊奇荒之前的山西又是如何度過災荒歲月的?《荒政記》提到的災情與丁戊奇荒“相仿”的道光丙午年間的旱災,因為“並無大傷”,幾乎被歷史淹沒。山西人怎樣度過丙午旱災,《荒政記》用“但借倉緩賦,不煩公家之賑”一筆帶過。話雖簡單,卻可能是問題的關鍵。這裡的“倉”,應該指倉儲。中國古代社會的倉儲主要有三種形式:常平倉、社倉和義倉,其中最重要的是常平倉,屬於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官倉,規模最大也最普遍。究其本意,常平倉的主要功能是穩定糧價,即“谷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一旦遇到災荒,常平倉則又有了賑濟的功能,即“小歉平糶、中歉出借、大歉賑濟”。常平倉制度正式創立於西漢,為此後大多數王朝統治者所承續和發展,至清乾隆初年達至頂峰。
王朝統治者對於糧食儲備的重視,充分體現了傳統時代中國社會的治理邏輯。在一個沒有“發展”、“增長”等概念的時代,天下太平是一個王朝的治理者所有施政行為的最終目的,而要達到天下太平,最根本的一點,便是以天下土地之所產,養活天下芸芸之眾生。《清實錄》對於每一年軍國大事的記載,都以“會計天下民數、谷數”作結,原因即在於此。傳統中國又是一個靠天吃飯的農耕國家,風調雨順則國泰民安,天災頻頻則民乏食,民乏食則國不安!倉儲以豐年之糧調劑災年之食,是一個王朝長治久安的物質基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此都十分重視。一般而言,中央政府對於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儲備要求。以清朝為例,乾隆以來糧食儲額較多的地區有華北平原、長江中下遊平原、陝甘地區等;儲額較少的地區則主要集中在兩湖地區。影響糧食儲額的因素有人口數量、交通條件、受災情況、區域脆弱性以及特殊的政治、軍事考慮。山西交通不便、災害頻繁、糧食產量低,其儲額標準是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兩倍。
就制度設計而言,建立在兩千多年治理得失基礎上的備荒制度可謂完備,但這種制度的完備經不起人心在時光流逝中日漸疲遝的消磨。嘉慶以後,倉糧“多有缺額,實貯倉者十無二三”。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及長達十數年的內戰消耗之後,全國的常平倉儲備幾乎已名存實亡。除了人心疲遝、管理不善和戰爭消耗之外,積錢不積谷的風氣也是嘉道以後倉儲逐漸衰敗的重要原因。當然,從積極的一面講,積錢不積谷的風氣體現了商品經濟的繁榮,意味著中國的傳統經濟有可能發展到一個新的水準。
據李伯重的研究,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以江南為中心的全國性的整合的市場,糧食的長途貿易佔有最大的比重,超過六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必須通過市場來獲得口糧。山西並非產糧大省,即使是豐收之年,山西之糧亦難養活山西之人,不足的部分主要依靠陝西、河南等周邊省份的市場解決。不過,這只能構成一個區域市場。郝平曾對十九世紀下半葉山西與直隸、上海的糧價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山西糧價與上海糧價幾乎沒有相關性,而直隸與山西的糧價波動雖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兩地的波動幅度相差甚巨。直隸糧價大都在每石一至三兩範圍內波動,而山西糧價的波動範圍在每石一點三至五十七兩之間。於此可見,山西的糧食市場幾乎是與全國性的糧食市場脫節的,具體表現為極度脆弱,一有風吹草動,便會出現相應的大波動。
山西糧價之所以波動劇烈,郝平認為主要與自然環境、政府效力、市場供求關係和銀錢比價等有關,其中尤以自然環境為根本。所謂自然環境,即造成糧價波動的旱災、水澇、蟲災等自然災害。糧價隨自然環境變化而波動是很容易理解的,但這不僅山西如此,其他地區也如此。據王業鍵的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華東地區與華北地區自然災害的出現頻率相差無幾,而長江三角洲的糧價僅在每石一點七六至二點八九兩的範圍內波動。江南與山西在糧價波動上的這種差別,不在於江南擁有巨大的糧食生產能力,能夠很快彌補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事實上,從清代前中期開始,江南便同山西一樣,自產的糧食不夠自用,需要從外地,主要是從長江中上遊輸入糧食以補不足。兩者的區別實質在於,糧食運至江南極為便利,而運至山西殊為不易。在鐵路大規模出現之前,糧食等大宗商品的貿易主要依賴水路,而十九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三條水路是長江、大運河與沿海,江南正處於這三條水路的交匯處,因而成為全國市場的中心。由於這種中心地位,江南糧價很難因為本地區的自然災害而出現劇烈的波動。同理反推,山西糧價之所以經常出現劇烈波動,正是由於山西極為糟糕的交通環境,使得市場上很難有大批糧食可以隨時隨地進入山西。
對於一個在地理條件上很難支持糧食長途貿易的省份,要保證糧食安全,唯一的出路就是重倉儲。但如前文所述,倉儲在嘉慶以後每況愈下,再加上積錢不積谷的風氣,政府的常平倉儲備幾乎形同虛設。更可怕的是,不僅官方糧儲如此,民間更是如此。李用清寫道:“二十年前,積粟之家以千石計,近以花田之故,數十石之家亦不多見矣。”所謂“花田”,是指罌粟種植。可以看出社會的變遷:一是民間重利不重積谷的風氣日盛,二是山西的罌粟種植日漸泛濫。據統計,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積約為五百三十萬畝,其中有六十萬畝好地在種植鴉片。清末,種植鴉片每畝所得可交換大米近兩千斤,兩相比較,種植鴉片的動力遠甚於種植糧食作物。顯然,鴉片種植泛濫同樣也是市場邏輯的必然。
然而,就在晉人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越來越托付於市場之時,丁戊奇荒降臨了,帶來了山西人此前從未見過的饑餓與死亡。當時,《申報》的一篇社論如此表示:“中國之富首推山西,然至今日,其全家餓殍,異地流離之苦,亦首推山西”,其原因“大抵晉人平日僅重銀錢,人人收藏以圖利息,至於糧食無人積儲,故一旦遇災,以至困苦如此耳”。實際上,正在步入“商業革命”時代的中國,“平日僅重銀錢者”絕不會只有晉人。晉人的不幸在於,在現代交通技術將山西融入全國性糧食市場之前,他們的糧食安全便已過於依賴市場。正是基於這種慘痛的經驗,這場令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都束手無策的奇荒過後,山西各地的地方志與災荒碑中一再強調、反覆叮囑的都是“耕三余一備災荒”。對於災後幸存的山西人而言,這句話的分量是再怎麽強調也不為過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