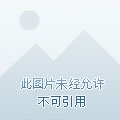在唐代數以千計的詩人中,對佛教的尊崇幾乎達到頂禮膜拜之程度者,大約只有兩人,其一為王維,其二即白居易。如果將王維與白居易的崇佛略作比較,又可知二人的情況乃是頗具區別的,其中最為明顯者,是王維的崇佛乃始自其青年時代,而白居易則虔誠於其中晚年之際。對於王維崇佛的時間之始,其集中的《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一文乃有明確記載,雲:“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綿州巴西人……遇五台寶鑒禪師……遂密授頓教。……(禪師)以大唐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入般湼槃於薦福僧坊。……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 以開元二十七年上推“維十年座下”,為開元十七年,亦即王維從道光禪師學“頓教”乃始於是年。王維的生年,雖然有多種說法(具體詳下),但核之有關史實,知唯有“武後延載元年(公元694年)”說[1]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以此計之,則王維開元十七年乃為36歲。而綜王維一生,又可知他自開元十七年從道光禪師習學頓教後,直至晚年因“疾甚”而病卒長安時止,其間雖有近30年的時間,卻從不曾與佛教疏遠離分,而是崇尚之心之情乃日愈一日。王維之所以被後人稱為“詩佛”,而與“詩仙”(李白)、“詩聖”(杜甫)相鼎足者,固然與他融佛理於詩歌創作中的關係密切,但其近30年的禮佛生涯,也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最為引人注目的原因。
作為自少年時就極具入仕之心的王維,作為“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2]的詩人兼畫家的王維,為什麽會在開元十七年就置身於“佛教徒”的行列,並且對佛教的熱衷與尊崇乃是日篤一日呢?為什麽他所選擇的是“頓教”而不是“漸教”呢?本文將對此作一具體探討,或有助於對王維思想的全面把握與認識。
一、尊崇佛教為時尚的社會風氣
在盛唐詩人中,人們對於王維生年的說法乃是眾說非一的,因為迄今為止,已有公元692年(武後如意元年)、694年(延載元年)、695年(證聖元年)、699年(聖歷二年)、700年(久視元年)、701年(長安元年)等多種說法存在。這些說法,顯然是不可能都成為王維的確切生年的,但其中卻涉及到了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事實,這就是王維之生,乃是在武則天執政的時期。據兩《唐書·則天皇后紀》可知,武則天正式稱帝並改國號為“周”者,事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至長安四年(公元704年)駕崩,其即皇帝位正好為整15年。若以此加上武則天即皇帝位前執掌大唐政權的6年(始於光宅元年即公元684年,止於永初元年即公元689年,翌年為載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則其前後主宰當時的政治舞台共21年(其“垂簾聽政”於唐高宗時期的時間未計)。
武則天在初唐後期之所以能夠主宰當時的政治舞台並最終成為一位女皇帝,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佛教徒之鼎力支持,則不能不視之為最關鍵者之一。眾所周知,武則天不僅自小就崇信佛教,而且還曾大興佛寺,廣造佛像,並與一些佛教人物打得火熱,如她曾將神秀迎入宮中,奉為國師,即為典型的一例。對此,《宋高僧傳》之《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一文乃有記載:“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3]在唐高宗即位期間,武則天還於鹹亨三年在洛陽龍門建造了一組著名的石窟佛像,佚名氏的《奉先寺像龕記》對此載之甚詳,其有雲:“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奉。”[4]其中的盧舍那大佛,據說就是以武則天為模特兒鐫刻的,這尊佛像面容嬌好,氣勢磅礴,至今仍屹立於龍門石窟。武則天與佛教之所以具有如此密切的關係,乃是有其明顯的政治目的與意圖的,對此,《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中的一則記載,即可幫助我們有所認識與把握。該《紀》於載初元年內說:“秋七月……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製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5]所謂“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雲雲,指的是載初元年(公元690年),洛陽白馬寺僧人懷義與東魏寺僧人法明等十位和尚偽造《大雲經》四卷,稱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當代唐作閆浮提主(即皇帝—筆者注)”之事。懷義其人,《資治通鑒·垂拱元年》乃有載:“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為寺主。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命與附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6]其後,這位“本姓馮”的薛懷義,即視大臣“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並曾任新平軍大總管等職。由於懷義、法明等十僧人在偽造的《大雲經》中,“盛言神皇受命之事”,所以在此之未久後的“九月九日壬午”,武則天即“革唐命,改國號為周”,正式登上了她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並“改元為天授,大赦天下”。《資治通鑒》中所謂的“釋教開革命之階”,即因此而言。
佛教從輿論的角度襄助武則天登上了皇帝寶座,為了對其予以報答,當上了皇帝的武則天,即向全國頒布了一道《釋教在道法上製》的詔書,欽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從而以強權政治的手段抬高了佛教的社會地位。《製》雲:“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偈之文,歷教表於當今,本願標於曩劫。大雲闡奧,明王國之禎符;方等發揚,顯自在之丕業。馭一境而教化,宏五戒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方啟維新之運。宜葉隨時之義,以申自我之規。……布告遐邇,知朕意焉。”[7]其中所謂“蒙金口之記”雲雲,指的就是懷義與法明等人偽造《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之事”,而“又承寶偈之文”之載,則是指武承嗣“偽造瑞石”並刻“聖母臨人,永昌帝業”的所謂“寶圖”文字,兩《唐書·則天皇后紀》對此均有記載,茲不具述。政治與宗教的相互勾結,最後雖然是各得其所,但佛教卻因此而在華夏蔚成大國,並千年不息。
而在武則天之前的唐代帝王中,如唐太宗、唐高宗等,亦幾乎都與佛教打得火熱,以至於在皇宮乃至全國上下形成了一種以崇佛為時尚的風氣。《舊唐書·神秀傳》有雲:“開元十三年,敕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製弟子之服。……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於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閭裡為之空焉。”[8]這只是當時“都城士庶”崇佛的一個縮影。這種風氣的形成,若追根溯源,應與唐太宗李世民未當皇帝前曾得到過僧人的援助大相關聯。《全唐文》卷十《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卷九《佛遺教經施行敕》二文,即就此事進行了記載。據前文,知秦王李世民為王世充所圍攻時,曾得到少林寺僧的大力救助,故其中乃有“法師等並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凶孽”[9]之載。後文則記載了李世民即皇帝位後,下詔書讓“官宦五品已上,及諸州刺史”以《遺教經》為準繩,進行“護持佛法”[10]的決定。由是而觀,可知武則天的禮僧敬佛,乃絕非偶然,而是與唐太宗等人一樣,都是在利用佛教為其“皇圖永固”之政治目的服務。而作為中國文化史上“西學東漸”之一者的佛教,則即因此獲得了一個既巨大又長久的政治靠山,並在其發展史的王國裡,首次凌駕於純屬“東學”的道教之上。
正是由於以上的原因,所以初盛唐時期的諸多詩人如陳子昂、盧藏用、張說、孟浩然、王昌齡,以及李白、杜甫等,即都與當時的佛教徒有過不同程度之交往。以與王維同享“山水詩人”盛名的孟浩然為例,他不僅在家鄉襄陽時經常出入“蘭若”(佛寺、僧舍)並與其主人打得火熱,而且在幾次出遊越剡之際,還曾與駐錫於當地的一些僧人交往密切,並先後寫下了約20首左右的“佛教山水詩”。孟浩然的禮佛,雖然未能給王維以任何影響(至今未發現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但與孟浩然生活於同一時期的王維,與孟浩然等人一樣受當時以崇佛為時尚的社會風氣之影響,則是可以論斷的。而且,上引《舊唐書》記載普寂開元十三年為唐玄宗詔令“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的那種盛大場面,王維應是親眼目睹了的,因為據拙文《王維早期行事探究》[11]之所考可知,開元十三年的春天,王維已由濟州遇赦西歸長安了。即是說,發生於京城的這種狂熱的崇佛場面,對於當時的王維而言,應是頗具影響的。
二、遭受政治打擊後的自我消沉
作為“政府官員”一份子的王維,在唐玄宗執政的開元時期,於政治上曾遭受過兩次嚴重打擊,其一為被貶濟州,其二即出使河西,其中,前者的打擊又尤甚。據兩《唐書·王維傳》、《舊唐書·劉子玄傳》,以及薛用弱《集異記》、王讜《唐語林》等材料的記載,可知王維在開元九年曾因“黃獅子”一案,而被“坐累為濟州司倉入伍”。兩《唐書》中的所謂 “坐累”,其實就是唐代官製中的左遷,對此,拙作《王維生平與唐代制度考論》[12]一文乃有詳考,此不具述。唐代官員左遷,其裡程一般為2000裡,若情節嚴重者則更遠,合勘《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兩《唐書·地理志》之所載,知王維所“坐累”的濟州,在唐代由長安經洛陽、陳留、鄆州而至,其全程為1920裡,與唐廷所規定的左遷裡程正相符合。
王維之所以被貶濟州,雖然是因“黃獅子”而使然,但潛藏於其內的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則是唐玄宗為防止宗室諸王對其政權的反對而進行的一次嚴厲打擊。《資治通鑒》卷二一二於開元八年內對此有所記載,其雲:“冬十月辛巳……上禁約諸王,不便與群臣交結。光祿少卿附馬都尉裴虛己與岐王范遊宴,仍私挾纖緯,戊子,流虛己於新州,離其公主。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數與范飲酒賦詩,貶庭琦雅州司戶,諤山茬丞。……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上……令複位。”[13]這條材料說得很明白,在開元八年冬十月前,凡與諸王往來者,都受到了唐玄宗最為嚴厲的懲治,所以,附馬都尉裴虛己、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以及薛王業妃之弟韋賓等人,即均因此而遭受到了不應有的打擊。另據王讜《唐語林》記載,王維之所以犯“黃獅子”案者,主要是為他人慫恿所致。是書卷五《補遺》載雲:“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14]所謂“被人嗾令”,就是受人指使的意思,即王維的擅“舞黃獅子”者,乃並非出自其本意。此“嗾令”者為誰?勘之王維集中的《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諸詩,知其乃是非岐王李范莫屬的。萬年尉劉庭琦與太祝張諤既然皆因“數與范飲酒賦詩”,而一被貶為雅州司戶,一被貶為山茬丞,則王維的擅“舞黃獅子”者,也就自會在唐玄宗的打擊之列。正因此,所以王維才被左遷至遠離京師長安2000裡路途的濟州。
此次的左遷濟州,對於剛剛步入仕途的王維而言,其打擊之大乃是不言而喻的,對此,我們從其寫於此行即將離別長安之際的《被出濟州》一詩中,即略可窺獲之。詩雲:“微官易得罪,謫去濟川陰。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閭閶河潤上,井邑海雲深。縱有歸來日,多愁年鬢侵。”最後兩句之所寫,充分反映了王維對此次打擊的心有余悸,以及其對仕途的感慨良多乃至於意冷心灰。所以,開元十三年春遇赦西還長安後的王維,對於仕途幾乎是完全失去了信心,但出於全家的生計問題,王維又不得不繼續到為他所厭惡的“塵網”中去討生活,因而才有了任職“淇上”之舉。王維因遭受“黃獅子”案打擊後的這種思想變化,在他寫於此期前後的一系列詩作中,乃是具有明顯之反映的。如其集中的《濟上四賢詠三首》、《寓言二首》其二、《偶然作六首》其一、其二、其三、其四、《淇上即事田園》、《不遇詠》、《送孟六歸襄陽》等詩,即皆為其代表。總體而言,這些詩之所寫,或讚美古今隱者,或歌頌田園生活,或寫作者自己“久與世情疏”,或勸其友人“醉歌田舍酒”,其動機其意旨,與“黃獅子”案發之前的王維的“少年精神”相比較,可以說完全是兩種面目。這時的王維,無論他是如何的風流蘊藉,也無論他具有怎樣的橫溢才華,他是再也寫不出如《夷門歌》、《老將行》、《李陵詠》這樣具有“少年精神”的詩歌的。而事實證明,王維不僅在此期,而且是直至晚年病卒長安之時,他也不曾創作出“縱死猶聞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這樣充滿著盛唐天氣的作品的。也就是說,我們從王維遭受“黃獅子”案打擊後的一系列詩歌中,所看到的只是詩人的畏懼與沮喪,詩人的消沉與厭世,總之,“塵網”中的一切於詩人而言,似乎都是那樣的遙遠,都是那樣的永不可及!正因此,所以任職淇上未久的王維,在回到長安後即“杜門不欲出”了。不僅如此,回到長安後的王維,還對滿懷希望專程入京求取功名的孟浩然,也寫詩勸其回歸襄陽,以“醉歌田舍酒”而“無勞獻子虛”。而王維寫詩勸慰孟浩然之時,據拙著《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二節[15]之所考,乃為開元十八年的秋天,即這時的王維師從道光禪師學“頓教”已一年有余,所以他才勸孟浩然“無勞獻子虛”。
以上所述表明,發生於唐玄宗開元九年的“黃獅子”案,不僅使王維被貶謫到距京師長安2000裡路遠的濟州去任司倉入伍,而且也使王維對於仕途的認識產生了一個帶根本性的轉變,即其由早年的極積尋求入仕機會,一變而為此期的“久與世情疏”了。其所反映的,是在政治上遭受了打擊的王維,由於對仕途的冷寞而轉向了其生活的另一面,這就是儒家思想中與“入世”相對而存在的“出仕”。而在以崇佛為社會時尚的盛唐初期,“出仕”者最理想的選擇,自然就是非禮佛莫屬了。更何況,在王維師從道光之前,王維的母親已作了普寂多年的世俗弟子。
三、“禮佛之家”的家庭影響
《舊唐書·王維傳》雲:“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徒家於蒲,遂為河東人。”這一記載表明,王維的父輩本為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因其父任職的緣由,全家乃搬遷於蒲州(今山西永濟),並遂為蒲州人。唐蒲州又名河東郡,不僅是當時著名的“四輔”之一(其余“三輔”分別為同州、華州、岐州),還於開元九年被升格為河中府,而且其地處京、洛之間,交通極為方便。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所載,河中府“西南至上都三百二十裡,東至東都五百八十五裡”[16],這一裡程表明,由蒲州往來於長安或者洛陽,均只需要幾天的時間即可到達,則其在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受長安與洛陽的影響,自是無可懷疑的。而僅就佛教方面言,蒲州在當時就足以成為全國佛教徒們的矚目之所,這是因為,蒲州的崇佛者不僅人數眾多,而且還在王維生活的當時誕生了一位領袖級的著名佛教人物。
據宋代僧人讚寧所撰《宋高僧傳》一書的檢索可知,在該書所記載的520位僧人(此指正傳僧人,附見者未計其內)的生平事跡中,其籍貫為蒲州或者蒲州一帶的僧人乃有20餘人之多,且不乏聞名全國者,如普寂、良秀、寰中等,即皆為其代表。其中,又尤以普寂為最。普寂是神秀的謫傳弟子,神秀既為禪學北宗最早的一位領袖,又曾為武則天奉為國師(說詳上),名傾天下,因而被尊之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17]。而作為神秀弟子的普寂,則更是不讓乃師。《宋高僧傳》卷九《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一文,較為具體地記載了普寂一生的事佛之況,其中有雲:“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及(神)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鹹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製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眾。開元二十三年,敕普寂於東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二十七年,終於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製弟子之服。有製賜諡曰大慧禪師。”[18]文中的“大慧禪師”,據李邕《大照禪師塔銘》[19]一文,知乃為“大照禪師”之誤。在神秀“高年”之際,唐中宗既然“特下製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眾”,則普寂自然就是代神秀以為北宗的領袖了。普寂被唐中宗欽定為佛教禪宗的北宗領袖這一事實,在當時於普寂的家鄉蒲州而言,顯然是具有一種無上的榮光與驕傲的,其結果則是吸引了更多的故鄉人走向崇佛與禮佛的行列,《宋高僧傳》中所謂“天下好釋氏者,鹹師事之”雲雲,自然是應包含著蒲州的一些“好釋氏者”於其內的。而王維的母親師從普寂者,大約即是在此之際。
關於王維母親的生平概況,由於資料缺乏的緣故,雖然均不可確考,但其師從普寂禮佛之事,卻為王維的親筆之文所記載,此即王維集中的《請施莊為寺表》一文。是文有雲:“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年,褐衣疏食,持戒安禪,樂在山林,志求寂靜。”[20]文中的“大照禪師”,為普寂園寂後的諡號。上引《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一文,明確記載普寂於開元二十七年“終於上都興唐寺”,王維母親既師事其“三十餘年”,若“三十餘年”以三十六年計之(從行文的角度言,若過了三十六年,就應稱“近四十年”,而不得雲“三十餘年”了),則其始師之年應乃為唐中宗景龍元年,亦即公元707年。又據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神秀)碑銘》一文,知神秀乃卒於“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21],神龍二年為公元706年,則唐中宗下詔“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眾”者,當即在是年之前的神龍元年。即是說,合勘《宋高僧傳·普寂傳》與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之所載可知,王維母親師從普寂者,應乃在武則天神龍元年前後,也即唐中宗下詔令普寂代神秀為北宗領袖的當年或者翌年。
而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王維母親師事普寂後,王維、王縉兄弟即與普寂或其弟子的關係甚為密切。為便於述說,先看王縉。按王縉有《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一文,其中有雲:“(宏)傳大通(神秀),大通傳大照(普寂),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大證)。……縉尚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為知友。大德(大證)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視縉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為之強述。”[22]據此文,知王縉既曾師從於大照(普寂),又曾與大照的弟子廣德,以及廣德之再傳弟子正順(即大證弟子),均過從甚密。王縉“尚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度其時,自當在大照之卒的開元二十七年前,而其之“因學於大照”者,顯然是受其母親的影響所致。王縉母子二人,均以普寂為師而禮佛的這一事實,正是京洛士人以禪學北宗為尊的崇佛思想的具體反映。
再看王維。綜王維一生,可知他雖然不曾與普寂進行過直接的交往,但卻與普寂的同門師弟或弟子頗具關係。《舊唐書·神秀傳》有雲:“神秀卒後,弟子普寂、義福,並為時人所重。”王維集中有《過福禪師蘭若》一詩,其中的“福禪師”即為義福。據《宋高僧傳·義福傳》所載, 義福為潞州銅鞮(今山西沁縣)人,其於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時,曾“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禮拜紛紛,瞻望無厭”。義福與普寂既為同門弟子,二人又皆為當時的“河東道”人,且其在途經蒲州時又為“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幡花迎之”,則王維與其相識,當和其母親及王縉皆為普寂的世俗弟子不無關係。或以為王維此詩中的“福禪師”為惠福者,不確。又王維集中有《為舜闍黎謝禦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一文,其中的大通為神秀,大照為普寂,舜闍黎則為普寂的弟子,王維既代舜闍黎寫了這篇“謝禦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表明王維與舜闍黎的關係乃非同一般。普寂另有弟子名璿禪師者,曾長期駐錫於潤州江寧(今江蘇南京)瓦官寺,王維集中有《謁璿上人》一詩,紀與其之交遊。另據《宋高僧傳·元崇傳》載,璿禪師曾與其弟子元崇於唐肅宗至德初年“並謝人事”後,“杖錫去郡,歷於上京”,並且“於輞川得右丞王公維之另業”,而王維則與元崇“神交”一時。王維集中又有《留別山中溫古上人兄》一詩,表明了王維與溫古上人是頗具交誼的,而這位溫古上人,據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23]的考察,知其與儲光羲《至嶽寺即大通大照禪塔上溫上人》之溫上人為同一人,即其亦乃普寂的弟子。
王維的父親是否禮佛,因資料所限難以考知,但從王維的名(維)與字(摩詰)均取至《維摩詰所說經》(簡稱《維摩詰經》)來看,其父與佛教應是不無關係的。這是因為,以精通佛學的維摩詰居士之名來作為王維的名與字的事實,充分表明了替王維取其名及字者,乃為一位頗具佛學修養的禮佛居士。此為其一。其二,從傳統文化或者民俗學的角度言,中國古代給子女取名或字者,大都為男姓即乃為子女之父所為,如《離騷》中的“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即可為證。這樣看來,則為王維“肇錫余以嘉名”者,是可肯定為其父而非其母的。綜此二者,是知王維之父極有可能也是一位篤誠的禮佛者。準此,則王維受其父母或者大弟王縉的影響而加入到禮佛的行列,也就勢所必然。
四、王維與謝靈運及“頓教”
王維雖然在社會風氣、自身經歷、家庭環境三大因素的驅駛下,而成為了當時浩浩蕩蕩崇佛大軍中的一份子,但他卻並未如其母其弟那樣去師從於大照禪師普寂,而是選擇了道光和尚並主要向其習學“頓教”。這一事實表明,在禮佛的對象或者說宗派方面,王維與其母其弟乃是大有差異的,而於其前輩詩人謝運靈的崇佛則是一脈相承的。
從佛教史的角度言,佛教之於劉宋時期,因其發展的迅猛,而形成了當時鼎足而立的三大僧團,這就是著名的洛陽僧團、建康僧團與廬山僧團。這三大僧團又因其地理方位的緣故,而為佛教史家們將其分為北方僧團(洛陽僧團)與南方僧團(建康僧團、廬山僧團)兩大陣營,其中的南方僧團,則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又分別被演變為兩大派,即一為漸悟派,一為頓悟派。漸悟派屬於傳統的佛教範疇,頓悟派則因建康僧團中竺道生的佛學主張而形成。據慧皎《高僧傳》、僧佑《出三藏記集》所載,竺道生俗姓魏,原籍钜鹿,寓居彭城,在建康瓦官寺從竺法汰出家,並曾師學於天竺僧鳩摩羅什。又據慧琳《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一文所載,竺道生因“轉益多師”的緣故,而對小乘佛教中的“說一切有部”理論與大乘佛教中的“般若中觀”學說等,都曾有所涉獵與探究。之後,竺道生便提出了著名的“佛性說”與“頓悟成佛論”,唐人所謂的“頓教”,即因此而始。“頓悟成佛論”又稱“大頓悟”,如《高僧傳》載僧慧達《肇論疏》引竺道生語曰:“大頓悟雲:夫稱頓者,明理不可分,悟語照極。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忘釋,謂之頓悟。‘[24]“頓悟成佛論”的要義,簡而言之,是指奉佛者在一時間內於佛學要義可全部悟理。也即竺道生認為,悟理證體不需要過渡階段,凡修行者皆可因頓悟而成佛。竺道生的這一佛學主張,主要是折中儒、佛二家而各取其長,即棄佛教之漸悟而取其能“聖”之說,去儒家之不可成聖而取其理不可分之說,從而提出了著名的“頓悟論”。因此,“頓悟成佛論”之所指,實際上就是一種快速成佛法。這種成佛法,對於傳統的“漸悟成佛論”自然是一種挑戰,故其在當時即受到了眾多僧人的排斥與反對。但竺道生的這一佛學主張,不僅為謝靈運所全盤接受,而且謝運靈還撰寫了著名的《辯宗論》一文,以從理論的角度旗幟鮮明地支持“頓悟成佛論”。由於謝靈運《辯宗論》的問世,一場發生於佛學界因“漸悟”與“頓悟”的大論戰,即由此而全面展開。因此之故,謝靈運又先後撰寫了《答王衛軍書》、《答王衛軍問》、《答法勖問》、《答僧維問》、《答慧驎問》、《答驎維問》、《答法綱問》、《答慧琳問》、《答綱琳二法師書》(以上諸文,《廣弘明集》卷十五皆著錄,但統作一文以待之)等文,以進行答辯。這些文章,既對“頓悟論”所持反對意見者進行了有力辨駁,又宣揚與發展了“頓悟”新說,因而在當時影響甚大。由是而觀,可知生當劉宋之際的謝靈運,其之於佛教乃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頓悟論”者。
謝靈運對“頓悟論”的公然支持,其觀點其學說,有認者認為乃“標誌著魏晉思想的一大轉變,而下開隋唐禪學先河”[25]。所言甚確。於是,由竺道生所倡說、謝靈運所支持的“頓悟成佛論”,即成為了其後佛教禪宗之“南宗頓門”的淵源。王維師從道光禪師學“頓教”者,雖然不能說是直接受到了謝運靈的影響所致,但其之所學與“頓悟成佛”關係密切,則是可以肯定的。而“頓教”於唐代的佛教禪宗而言,乃屬於南宗的範疇,普寂則系北宗的領袖,所以王維之禮佛,乃與其母其弟相區別而於謝靈運為近的。謝靈運涉足佛教,據拙作《謝靈運與佛教人物交往考》[26]一文之所考,知乃在義熙八年(公元412年)他26歲之際,此則表明,謝靈運在崇佛的時間方面乃是要比王維早許多的。謝運靈崇尚佛教,除了如上所言,大張旗鼓地公然支持竺道生的“頓悟論”外,他還與慧嚴等人改編北本《大般涅槃經》,為《金剛般若經》作注,在始寧建石壁精舍聘請名僧講經說法,而成為了一位“真真正正”的佛學居士。而王維一生,雖然不曾從事過佛教文獻資料方面的研究與整理,但他自從隨道光禪師習學“頓教”後,即與義福、璿禪師、元崇、淨覺、神會、溫古上人、燕子龕禪師等眾多僧人交往密切,因而對佛學理論乃有著極為深厚的修養。而且,王維之於佛學,乃是愈老情愈濃、愈老志愈篤的,對此,《舊唐書·王維傳》已有所載:“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談玄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京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晚年的王維,就是這樣於其所營構的宋之問的終南別業中,終日談禪論詩,以至於終老的。
王維與謝靈運,都是其各自時代的詩國驕子,二人所處的文化背景,所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其生活經歷、創作經驗、審美趣味等雖然均不盡相同,但他們對於佛教的傾心與尊崇,則是甚為一致的。而且,二人都是自與佛教結緣之日始,即再也不曾與之疏遠或分離過,以至於佛教在也們的思想行為、日常生活等方面,均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印記。正因此,他們才以各自非凡的文學才華,創作出了許多精致而又韻味無窮的“佛教山水詩”,從而增加了山水詩審美的新品種,並拓寬了中國山水文學的題材領域。對於謝靈運的“佛教山水詩”,拙作《論玄學與謝靈運的山水詩》[27]一文中已有所涉及,而王維的此類詩歌,我將另撰專文對其進行具體討論,故在此就不予贅述了。
注釋:
[1]王勳成《王維進士及第與出生年月考》載《文史哲》2003年2期。第153頁—第157頁。
[2]王維《偶然作六首》其六,《王右丞集箋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75頁。
[3]讚寧《宋高僧傳》卷八,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77頁。
[4]王昶《金石萃編》卷七十三,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7頁。
[5]劉昫《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21頁。
[6]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三《唐紀》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1頁。
[7]武則天《釋教在道法上製》,《全唐文》卷九十五,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981頁。
[8]劉昫《舊唐書》卷一九一《普寂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111頁。
[9]唐太宗《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全唐文》卷十,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115頁。
[10]唐太宗《佛遺教經施行敕》,《全唐文》卷十,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109頁。
[11]王輝斌《王維早期行事探究》,《唐代詩人探頤》第二章第一節,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頁—46頁。
[12]王輝斌《王維生平與唐代制度考論》,載《貴州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3期。
[13]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436頁。
[14]王讜,唐語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7頁。
[15]王輝斌《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二節,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第14頁。
[16]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二《河東道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5頁。
[17]“兩京法主,三帝門師”,語出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二三一)一文,為時人對神秀的一種高度評價。陳鐵民《王維新論·王維與僧人的交往》一文,認為此八字系時人對神秀弟子普寂、義福的評價(該書第116頁),實乃因未讀張說是文而致誤。而林繼中《王維小傳》第一章第一節從陳說者(該書第6頁),亦誤。
[18]讚寧《宋高僧傳》卷九,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98頁。
[19]李邕《大照禪師塔銘》,《全唐文》卷二六二,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2657頁—第2658頁。
[20]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320頁。
[21]張說《唐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全唐文》卷二三一,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2334頁。
[22]王縉《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全唐文》卷三七,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3757頁—第3758頁。
[23]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頁。
[24]以上所述論的內容,及所引僧慧達《肇論疏》文,均乃據拙作《論謝靈運與佛教的關係》一文而為,以下所言者亦同,不另注。該文載《貴州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又見拙著《先唐詩人考論》第六章第二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25]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頁。
[26]王輝斌《謝靈運與佛教人物交往考》,載《襄樊學院學報》2006年3期。第45頁—第49頁。
[27]王輝斌《論玄學與謝靈運山水詩》,載《北京化工大學學報》2006年4期。第36頁—第41頁。
(本文節選自黃山書社2008年版《王維新考論》第三章第四節)
本文系網易新聞·網易號“各有態度”特色內容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