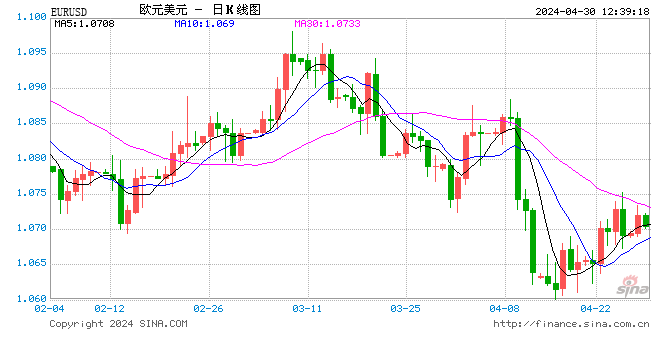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後的數年間,哈貝馬斯發表了一系列訪談和論文,談及美國的單邊政策、歐洲一體化乃至聯合國的改革和未來等問題。這些文章以《分裂的西方》為題結集出版,書的標題恰如其分地傳達了他對世界局勢的看法。
西方的分裂不僅存在於歐美之間,裂痕甚至貫穿整個世界。恐怖主義及其引發的反恐戰爭,大有引發文明衝突之勢,美國單邊主義挑戰國際法,歐盟內部也因發展的差異矛盾重重。哈貝馬斯在書中既對美國分裂世界的外交政策表示失望,同時也對歐洲不願推進更深層次的聯盟感到不滿。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作為一項設計,承載了自啟蒙運動以來的諸多美好願景,如自由、平等、博愛、科學、進步等等,並相信人類最終會建構起一幅世界永久和平的圖景。但西方愈演愈烈的分裂局面,似乎在言說現代性作為一項設計,不但沒有完成,反而遭遇更多困境。
撰文 | 曹金羽
“斷根化”與世界的不確定性
世界為何走向分裂?這是哈貝馬斯試圖在《分裂的西方》一書中回答的問題。在他看來,分裂不僅僅是現實政治和理想政治相互衝突的結果,其根源在於社會缺乏統一的規範性基礎。在統一的世界觀(如宗教)崩潰之後,社會變得更加多元,一種更為不確定的境況成為個人乃至國家共同的體驗,哈貝馬斯將其稱為“斷根化”(Entwurzelung)。
他在書中寫道,“在劇烈加速的現代化進程中,人民與其文化傳統發生了撕裂。在歐洲,有幸的是在有利的條件下,這表現為一個創造性的摧毀過程,在其他國家卻展現為既往生活方式的解體,而且在幾代人中都沒有可能的補充方式。”
因此,“斷根化”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的解體,而新的生活方式又無法在短期重建,隨之而來的是個人體驗到的失序和不確定感,焦慮、恐懼成為普遍的生存心態。在這種背景下,原教旨主義的複興,可以被視作對傳統生活方式劇烈“斷根化”之恐懼的一個反應。在本書第一章《原教旨主義與恐怖》的訪談中,哈貝馬斯將原教旨主義稱為一種特殊的現代現象,它是一種固執的精神態度,即當自己的信念和理由不能被普遍接受時,仍然要堅持以政治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實現它們。
原教旨主義對於理性的交往提出了挑戰,它拒絕承認一個共同的信念背景、文化自明性和相互的期待,這也就意味著拒絕溝通與協商,而是以一種排他性的前現代信仰之形式,製造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衝突。
對於民族國家來說,“斷根化”同樣意味著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增加。例如隨著交通、信息、經濟、生產、金融、技術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別是生態風險、軍事風險、國際恐怖主義等問題,民族國家也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單個國家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往往顯得捉襟見肘;另一方面,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增加又給了超級大國推行單邊主義霸權政策的時機。
全球化時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分化更為嚴重,哈貝馬斯認為,隨著市場全球化和國家的乾預,世界社會分裂為獲利國家、受益國家和失敗國家。國家之間的分化加劇了矛盾與衝突,例如,美國以其壓倒性的技術、經濟、政治和軍事優勢,在全球強行推行霸權策略,挑戰國際法的某些理念。它不僅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製造了對立,也在西方世界內部製造了矛盾。哈貝馬斯提到,正是伊拉克戰爭期間,歐洲發生了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從而在國際範圍內突顯了兩股力量,一方是美國,另一方則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公共輿論。
在哈貝馬斯看來,在一個“斷根化”的時代,個人的求定不應該是走向原教旨主義的封閉,國家更不應該去推行單邊主義策略。“斷根化”意味著我們被拋進了充滿無名關係的複雜世界裡,但這個世界也充滿了無數可以自我再生和自我調控的功能系統,統一的規範性基礎是需要我們從中去創造的。

難民問題,成為加劇歐洲內部分裂的重要因素。圖/視覺中國
從歐盟到國際法憲法化
面對西方的分裂,以及美國的單邊主義,哈貝馬斯將希望放在了歐洲。在《分裂的西方》的第二部分,哈貝馬斯重點論述了歐洲統一的挑戰和“核心歐洲”作為抗衡美國的可能性。分裂的西方更加呼籲建立一個統一的歐洲,能夠在國際層面上“施加影響力”。與此同時,對歐洲公民來說,建構起同舟共濟的政治命運意識,能夠使歐盟免於從內部被撕裂,淪為歐洲列強逐鹿的平台。
儘管對歐盟寄予厚望,哈貝馬斯也意識到歐洲內部存在的分裂,例如新老歐洲之間的衝突,歐洲內部發展不平衡導致的斷裂等。他認為,“核心歐洲”應該在統一進程中發揮帶頭作用,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國防政策,深化統一合作。
正是基於此,他認為歐洲應該加快立憲進程,在憲法愛國主義的框架下建立歐洲認同,促使公民從對國家的情感歸屬轉向對憲法的情感歸屬,用對憲法的認同取代對國家的認同。哈貝馬斯認為,歐盟立憲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它能夠促成歐洲公民社會的完善,建立歐洲範圍內的政治公共領域,同時創造一種所有歐盟公民都能參與的政治文化。這是一種真正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實踐,民族局限不再是彼此對話的障礙,內與外、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衝突,被一種更為普遍的理念消解。
歐盟憲法化進程,為理解一種多層次的超國家治理體系提供了模型,哈貝馬斯進而展開了對世界公民憲法可能性的分析,這是通向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狀態的途徑,他希望通過國家法的憲法化去重建康德的世界主義計劃。
在對國際法的分析上,他認為,古典國際法仍然建立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之上,因而會受製於主權國家,法律呈現出“軟”特徵,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政治會代替法律。因此,規範國家之間交往行為必須訴諸一部超國家的憲法,即哈貝馬斯所提倡的萬民法(cosmopolitan law)模式,它直接授予個體合法行動的權利,並授權創建超民族國家的政治代理機構與政治機構以確保全球範圍內人權的落實。
正是基於此,哈貝馬斯支持超民族國家的機構獲得更大的行政及司法權力,其目的是建立國際法律體系,將公民和人權的位置也從民族國家層面提升到國際層面。這樣才能促使單個政府尊重其公民的基本權利,必要時也可以實施製裁來達成此目的。哈貝馬斯這一理念所展示的是對聯合國和其他地區性組織的期待,聯合國應在全世界範圍內對保障和平、捍衛人權擔負起主要責任,同時也與民族國家和地區同盟保持著在憲法框架下的職責分工,從而建立一個新的更加和平也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為此,哈貝馬斯號召賦予聯合國更大的乾預權,讓它為世界社會的建構提供一個框架,只有這樣才能為那些高尚的計劃和政治制度的實現提供擔保。

作者:(德)哈貝馬斯
譯者:鬱喆雋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9年3月
走向團結,還是更加分裂?
《分裂的西方》中的文章大多寫於十多年前,時至今日,世界是走向了團結,還是更加分裂?答案似乎是後者,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哈貝馬斯2018年在接受《西班牙國家報》採訪時所說:“我仍舊對世界上正發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憤怒……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有一種刺耳的喧囂讓我感到絕望。”
言辭中流露出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失望,時代似乎並沒有為他準備一份“合格”的禮物。十多年過去了,分裂沒有減弱,反倒是更加撕裂。英國脫歐使得歐盟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對哈貝馬斯來說是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加上愈演愈烈的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債務危機,歐洲的政治局勢陷入嚴重的危機,出現了各國各自為戰的局面。在他看來,歐洲的理想正在被無能的政客和市場力量摧毀,而要真正地、長遠地維持歐洲的理想,必須放棄精英模式、克服技術官僚政治,重新建立歐洲共同的政治命運意識。
而全球右翼保守勢力的興起,同樣挑戰了哈貝馬斯超民族國家治理體系的理念。例如美國川普的上台,政策轉向保守,一系列政策具有強烈的本土主義色彩,而不是承擔國際責任,例如關閉移民口岸、退出《巴黎協定》、與各國展開貿易戰、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這些措施放棄了美國自由主義傳統中的普世主義理念,甚至回到一種前現代的“部落主義”,對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戰。
相比十多年前,世界的分裂有增無減,但這並不意味著哈貝馬斯為我們指錯了方向。事實上,我們比任何一個時代更加需要他,因為這個時代更加需要溝通。全球化意味著任何孤芳自賞或者自鳴得意都是狹隘的,只有在交往的實踐中,開放的心態和自由的關係才能夠開啟。時代越是緊張,越需要人去堅守這樣的原則,對於哈貝馬斯這樣的啟蒙知識分子來說更是如此。在個人層面,交往的實踐需要我們學會用他者的眼光來進行關照,在相互期待中構成普遍主義的道德形式。在國家層面,同樣需要一種超然的普遍主義,以破除民族的狹隘情結,為人們的共同生活造就一個開放包容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