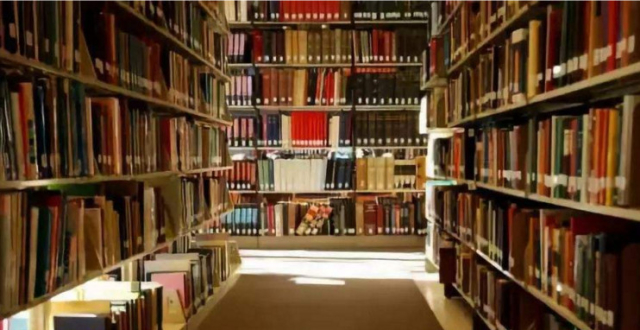第一次看到“小鎮做題家”這個詞的時候,余沛感覺被戳中了。
這個帶有自嘲意味的概念誕生於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意指“出身小城,埋頭苦讀,擅長應試,缺乏一定視野和資源的青年學子”。
余沛今年26歲,記憶的細節淡忘了,但她仍然清楚地記得縣城高中的宿舍冬天濕冷,她做題的手凍得腫成蘿卜一樣。通過高考優異的分數,她從貧困的廣西沿海小鎮來到上海的名校,卻在文化衝擊和繁難的學業中陷入自責和懷疑。
這些過去,余沛很少和他人傾吐,而“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是一個安全的角落——小組成立於5月10日,經歷了人數的急速攀升,從建立時的個位數到如今的8萬人,像一個漂流於大眾視野之外的小島,收納著許多和余沛相似的痛苦與困惑。
在組內,余沛敲下自述的帖子,最終命名“寫給小鎮做題家們的一封信”。
她寫道,“個人奮鬥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資源、社會時局和運氣也在一個人的人生軌跡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她勉勵和她一樣的小鎮青年,既然能考出來,一定會有“乘風破浪的機會”,“以後人生得意之時,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出身,不要去嘲笑那些深陷窘境的人是因為他們不努力。”
“夢被扎破了”
來大學報到一周了,余沛不敢坐地鐵。她擔心出醜,等到周末,她讓另一個先來上海讀書的廣西同學來接,才感到安心。她在老家廣西乘大巴走盤山公路,她常常暈車,地鐵穩當多了。
剛到上海讀大學,她經歷了許多第一次:被朋友帶去吃薩莉亞,第一次吃蝸牛,發在人人網上;在校園裡的全家第一次買了日式咖喱飯,激動地拍下照片。
“那時候站在馬路上就覺得有無限的希望”,余沛回憶。
落差很快掩蓋了希望。余沛想要交朋友,和一個同班女生出去吃飯,女生請客,點了五六個菜,第二頓飯余沛自然地回請,一下花掉300塊,她沒有說什麽,默默地選擇不再約飯。在寢室,她提起初高中宿舍裡沒有空調,來自城市家庭的室友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怎麽會有人住在沒有空調的房子裡?”

更多的時刻敏感而尷尬。老師上課不時蹦出上海話,余沛聽不懂,只能跟著同學大笑;聽同學說“pre”(課堂展示),不知道這是什麽,站在講台上,她有時膝蓋發抖。
小組的另一個角落,在廣東農村長大的梁凡最初也為pre感到困惑。上大學前,他沒有手機和電腦,第一次面對PPT的空白文檔,遇到不懂的地方查百度,彈出來各種病毒、廣告,把螢幕全部佔滿,一下子很挫敗,“後來發現人家做一個pre都比你好一萬倍,展示、審美、內容、引經據典。”
參加社團面試,他自我介紹都講得磕磕絆絆,進入社團要通過三面,他參加一面後就放棄了。“在很多場合我都不知道怎麽表達自己的心思”,梁凡很苦惱。
大一時的局促,在山西朔州小鎮長大的組員杜依苓也記得。9月開學參加中秋晚會,同學自信地上台展示才藝,她在底下沉默不語。那時候她對形象自卑,高考前,她穿的都是褲子,一有打扮的苗頭父母會教導:“你現在不是美的時候,等你上了大學愛怎麽美怎麽美。”大學裡,她學著減肥、燙頭,在社交媒體上搜索“女生搭配衣服有什麽建議”。
和大城市的孩子交流,杜依苓感到他們在表達觀點時很堅定,而她老是懷疑自己,不敢說出真實的想法,她想了想,那可能是因為“他們的世界沒有否定過他們”。
對來自湖南株洲的小組成員胡婧瑜來說,更為險峻的挑戰來源於和同學們在規劃上的起步差別。胡婧瑜在一所985大學讀英文系,很多學生大一、甚至高中就報考了托福雅思,學校在大一有英國牛津大學的交換項目,胡婧瑜沒有考過雅思,“注定要錯過。”
同輩壓力像一塊壓在心上的石頭。許多深夜,她躺在宿捨的床上回想自己的人生,難受得睡不著覺。握著手機,她不知不覺刷起別人辦的公眾號、同學的朋友圈,翻看他人高中的經歷。沒有讀過的書,沒有做過的事,她列成一張小單子,想要一個個彌補。
“發現之前活在一個巨大的幻夢裡面,現在夢被扎破了”,胡婧瑜形容這種感覺。
她曾加入過學生會,當學長學姐在群裡發了搬磚的任務,她不想回復,“覺得他們在佔用我的時間,毫無意義。”回想起來,胡婧瑜反思,“延續了高中的心態和思維。”小城的應試教育競爭激烈,她和年級第一的同學去辦公室問老師問題,對方會搶在她前面先問,5分鐘也要節省。
“我們班的很多人都像是一座座孤島。”胡婧瑜和“年級第一”的女孩在大學後再次見面,才有了更真誠的交流,終於知道對方當年喜歡哪個男生,開始重新分享青春期的秘密。
在胡婧瑜看來,這也影響了自己的戀愛觀。大學時,初戀男友接她下課,室友和男友聊起來,她插不上話。回宿舍之後,胡婧瑜窩在被子裡哭了很久。“我覺得室友漂亮性格好,當時就一心就在想,我應該把男朋友讓給更好的人”,胡婧瑜坦言,“那時候會認為我一定要優過你,你才會願意來跟我交往。”
她想學會怎樣去愛人,大二之後,她有意識的去讀一些書,才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合作和為對方著想的。
“怎麽辦,又掛科了”
高數課上,余沛早早地來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間,期待今天能聽懂課程的內容。
然而,回去面對空白的試題,余沛還是茫然。過去的題海戰術失敗了,交作業的前一天晚上,她熬夜把參考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到作業本上,情緒慢慢崩塌,怕打擾到室友休息,她蹲在陽台上哭,數對面宿舍樓還有幾盞燈亮著。
進入這個專業之前,她不知道要學習大量的數學課程。
余沛高考時是市狀元,填志願前,父親拿來一本厚厚的歷年高考報院校、專業資料,她和父親對此沒經驗,依據分數填報了學校最熱門的經濟管理大類專業。
“怎麽辦,又掛科了。”大學在課業上挫敗,她以看似搞笑自嘲的方式發在人人網上。
因為成績墊底,大二,余沛被分到人數最少的公共衛生管理專業。她發現,一道分流的同學也大多來自貧困地區。他們穿著洗到褪色的衣服,內向沉默,互相一聊,都只是本分讀書,選了一些“給分比較可怕”的課程,結果分數慘烈。
在小組發的帖子裡,余沛記錄,三年後,19個學生裡如期畢業的只有5人,其他人因為掛科太多不得不延畢。

在四川縣城長大的組員伍曉冬也一度陷在大學高數課裡,早起、佔座、記筆記……卻找不到學習的方法。身邊的人開始尋找別的出路,例如只是通過考試、聯繫實習、轉換研究生的專業或者準備出國,可他不甘心。
一次伍曉冬給母親打電話訴苦,母親以樸素的方式給出建議,“你只要把書攤在面前一句一句地看,總有辦法的。”伍曉冬突然崩潰了,“那句話聽上去其實挺殘忍的,那一刻就知道她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理解我面臨的是什麽。”
最頹喪的時候,他會想起少年時期,親戚長輩在無意中流露出對那些成績不夠好的孩子未來的擔憂,“現在都讀不好,以後能幹啥?”當時,他看不見他們,他是被表揚的那一個,“沉浸在被誇的喜悅中。”
大一大二,伍曉冬也逼著自己去聽專業和留學方面的講座,感覺渾身不自在,來參加的其他學生迫切地提問,看上去目標明確,他依舊迷茫,不知道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麽。一個人背著書包來,一個人離開。
幾乎每個受訪者都能說出一段關於孤獨的經驗。一次梁凡下課,和同班一個女生聊完問題一起走出教室,他想著趕緊回宿舍看小說,同學叫住他。當時他才發現,原來自己走路這麽快,因為一直是獨自一人。
大學頭兩年,他嘗試過投入課業和科研項目,碰壁後躲進小說。大二,他退了社團,逃了些課,待在寢室,鬍子不刮,有一個月隻點外賣。“好像一種破窗效應,不是討厭,是接納了自己,容許自己這麽墮落”,梁凡說。
大學裡,梁凡不斷地想,為什麽會變成這樣?
“你很難想象我能考上一個大學”
梁凡把自己一路向前的生活歸為“幸運”,村子裡每隔兩三年才出一個考入他後來就讀的985院校的孩子。
回顧過往,他的童年時光常在書裡度過,“我就是他們口中的留守兒童”,梁凡笑著說。
偶然得到一本《鋼鐵是怎麽煉成的》,冬妮婭和保爾柯察金的故事給了他情感的啟蒙。他喜歡的另一本書是《平凡的世界》,爺爺規定了睡覺時間,梁凡買了手電筒,蓋著被子偷偷看書。這兩本書,他看了十幾遍。
多年後,梁凡複習考研英語時看到一篇閱讀,說出身富裕家庭,父母會關心孩子的全面發展,報興趣班,放假時帶去各個國家旅遊,一點點了解世界。他憶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偶爾打電話,主要內容是囑咐他不要犯罪,不要玩水。
到小學三年級,他都不知道冬天要添衣,去鎮上參加比賽,穿著單薄的長袖,坐在老師摩托車後座吹了一路風,下了車牙齒發抖,嘴唇也發白了。
“看我的小學,你很難想象我能考上一個大學”,梁凡感慨道。
在村小讀五六年級時,一次下大雨,學校的圍牆年久失修,倒了。學校要求學生每個人帶工具去上學,“勞動課的內容就從以前的拔草變成了修磚。”一二年級,一個學期換了四個班主任,偏遠地區沒有老師願意來教,老師上課拿著棍子在課室的前面趕,後面的同學四處跑。
與梁凡不同,伍曉冬至今感謝母親創造的學習環境,在他放學回家做作業時,母親會關掉電視,不發出聲音。他的同學家裡很多開商店,放學趴在店鋪外一張矮小的桌子上做功課,身邊人來人往。
到初中,學校把他和一些成績好的同學叫到一起開會,用省會高中的升學率和學習氛圍鼓勵他們。伍曉冬說,當地條件稍好一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成都或綿陽去讀高中,“本地的升學率很難看,優質生源都在流失。”
杜依苓也記得,母親很早就開始打聽省會城市太原的就學機會。
她對童年的記憶是火力發電廠家屬區,體育館、電影院、職工俱樂部一應俱全,很多職工在那裡生活了一輩子,“所有的人都互相認識,互相幫助,互相指責,互相八卦”。現在,她偶爾會懷念那個桃花源一樣的地方。

學習緊張,父母幫她緩解壓力時會說,“你不要有壓力啊,如果你沒考上大學,爸爸媽媽還可以安排你回來當工人。”
但杜依苓渴望冒險。初中,她每天騎車去上學,遇到很大的風沙,道路顛簸,身上會覆蓋一層塵土,心裡隱隱煩躁。
她想著,有一天要離開這裡。
“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達最遠的地方了”
很多個高中備考的夜晚,杜依苓寫完作業,不想睡覺,她在語文筆電上寫小說,塑造了一個叫“尚北大”的主人公:“尚北大”胖胖的,臉孔像一個白麵團,戳了五個點,是他的五官,說話細聲細氣。他只知道學習,不參與運動,因為身體差,生了一場大病,錯過了高考,他跟母親一直念叨“我要去上北大”。杜依苓從後往前寫,滿滿幾頁紙,和課上的筆記交匯,“會有一種宣泄感。”
杜依苓不喜歡做題,但那時,高考是她唯一能期待的準線。她所在的高中倡導學衡水中學,口號是“提高一分,甩掉千人”,和衡水做同樣的試卷。高三後,每周有一節心理課,心理老師帶同學做遊戲,教一些消除焦慮的方法,但台下仍有學生在埋頭做題。
余沛就是那個“無時無刻”不在做題的人,學校發一本練習題,她會再買兩本。高考結束後把東西搬回家,發現做過的卷子疊起來和她人一樣高。
初三的暑假,余沛和老家的初中老師走在足球場上聊天。老師告訴余沛,“你很幸運,馬上就要去讀高中了。”
老師從初一帶到初三的班裡,女學生一年比一年少,“要麽輟學回家結婚生孩子,要麽被送去護校,或者去東莞打工。”余沛初中畢業那年,當地還沒有建高中。

余沛沒什麽朋友,享受獨自在空教室刷題的感覺。她不擅長數學,但能夠記住題型,考試看到一道題就知道原型是什麽。
那是她的得意之時,成績好是一種特權:原來12個人一間宿舍,高三時她可以住3人一間;晚自習會到辦公樓裡的空辦公室自習,獲得更加安靜的環境;食堂會專門準備排骨粥這樣的宵夜,平時根本吃不到。
伴隨做題的是以成績為中心的坐標系。一次港中文深圳校區來學校宣講,胡婧瑜參加完回到班級,歷史老師正好開始上課,幽幽地說了一句,“去聽這些有什麽用,高考考得好,分數上去了,好學校任你選擇”,她頓時覺得羞愧。
她被成績和名次牽動著,胡婧瑜高三偶爾回家,有天玩手機到12點,母親沒說什麽;另一天在家學習到11點15,母親不停催她早點睡。
胡婧瑜很生氣,“我覺得她在拖我後腿”,她在日記本上寫:
“……我所有的努力和改變都沒有價值了。……你以為我考了第二名,我下次還能輕鬆考第二名嗎?每天11點準時睡覺,輕鬆快樂地和你一起看電視玩手機,我的高考就能成功嗎? ……”
現在回憶起來,“她(母親)其實是密不透風的高壓氛圍的對立面”,胡婧瑜笑當年的自己。
念高中時,伍曉冬也對一個和成績有關的場面特別敏感:考完試後,班主任會把成績單放到講台上讓大家看,一窩蜂人在三秒之內把講台圍得水泄不通,“特別在意自己在那張紙上是什麽位置。”
“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達最遠的地方了”,伍曉冬說。
進入大學校園,來自小鎮的學生們回望過去,意識到不平等在更早的時候已經出現了。伍曉冬注意到,初中在縣城開家長會,很多父母面對班主任非常靦腆,像個犯了錯誤的孩子,老師說什麽就答應。而在省會城市的高中,同學的家長大多是大學老師或商界人士,會主動地和老師交流孩子的情況,在QQ群也發言積極,家長之間熟悉,彼此會交流信息,面對老師和學校顯得強勢。
對於杜依苓而言,差距也在高中時就產生了。
去太原上學,她第一次去了博物館、圖書館,“對城市有了概念。”她到太原的朋友家做客,發現孩子和父母會對話,在飯桌上談文化、時政、人生價值和美。杜依苓有滿腔的東西要表達,但是不知道和誰說。在家,父母聊的是八卦和廠裡的人事問題。
研究生畢業後,杜依苓去一所上海知名的重點高中應聘,在讀書角看到高中生寫的讀福柯的英文讀後感,學校展覽著社團海報,“那時候就有劇社、模擬聯合國。”
她上了一節公開課,除了倒數幾排,個個都仰著頭,願意參與討論,思維也比較發散。她不由自主地回憶起當年的班級,同學們一個個低著頭,很怕老師提問。
杜依苓記得,高考所有科目考完的晚上,下著大暴雨,她和全班同學回學校拿答案,提前預估成績。
那時的場景歷歷在目:她濕透了,穿著雨衣進學校,跟同學打招呼。老師發下答案,她倒吸一口冷氣,翻看起冊子。整個教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杜依苓開始計算文綜錯了幾道單選題。
過了一會兒,教室某個角落響起哭聲。
“認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麽”
梁凡總結,高考前,學習是他生活中唯一的關鍵詞,上了大學,他再也找不到新的目標。
在大學,他一度瘋迷做性格測試,想了解自己是誰,擅長什麽,看各種心理書,但“沒什麽用”。
“好像小學去到鎮上,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學,都會有一次突變”,一步步往外走,他時常迷茫。
梁凡記不清,他是在哪一刻開始試圖對抗那種“廢柴感”。
某一天,熬夜到特別晚,第二天六點醒了,他突然對自己說,我不想這麽下去了。他起床刮鬍子,搞衛生,想過一段新的生活。
大三那年,他參加比賽拿到獎狀,過了六級,也獲得獎學金名額,覺得生活終於出現了一點變化。
在胡婧瑜的觀察中,很多小組成員的矛盾感集中爆發在大一大二,“想從頭再來的感覺特別強烈,之後會有一個過渡。”
杜依苓試圖改變自卑的自己,她參加辯論隊,和同學一起搜集資料、討論,雖然還會怯場,但她發現知識面在拓寬,不同的觀點對撞,“很快樂。”
大三,她進了劇社,第一次演女主角,對著觀眾念一段充滿情欲的獨白,10分鐘不到的時間裡,她聽見自己的聲音講出來,心裡的一塊放鬆了,“能放下以前那個端著的、充滿優越感又清高的好學生形象。”
余沛也在大三重新找到狀態。分專業後,需要學習醫學院的課程,依靠刷題,她的成績不再全是末尾。
余沛說,過去她有點“社會達爾文主義”,高中時看到成績不那麽好的農村學生上課打瞌睡,隻認為他們不努力。
來到城市,余沛忍不住思考,為什麽自己從小地方的強者變成了一個弱者?
想法是慢慢轉變的。在人人網,她一直關注的一位學長常常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講述環衛工人的艱難處境,她開始意識到,社會有一些結構性的不公平。某種意義上,她覺得自己和環衛工人是相似的。
和余沛一樣,伍曉冬嘗試審視自我,“認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麽。”
因為決定跨專業考研,他在兩個校區往返上課,在地鐵上刷新聞,偶然看到北大數學系學生柳智宇退學出家的消息,伍曉冬內心有些震動。
“柳智宇已經拿到普林斯頓的offer,按照世俗的意義,他非常成功,但數學給不了他想要的東西,他最大的願望是去幫助別人”,伍曉冬記得很清晰,他在手機裡發了一條微博:他沒有辦法為了完成父母、學校還有社會對他的期待,去忽視內心真正的需求。
他也反思,大學裡很多人求學似乎只是為了學歷以及背後的地位與資源。
考完研,在辦公室,他坐在導師對面,說出了許久以來的困惑:“大學4年好像什麽也沒學到……”導師告訴他,這個不能隻怪學生,大學老師有錯,高中、初中老師的教育也有問題,“高考前,老師只是把東西嚼碎了以後吐出來喂給學生吃,學生不知道對知識的渴望是怎麽樣的”,導師說。
走出辦公室,伍曉冬感到開闊了不少。
“自己”、“沒有”、“工作”
一些小鎮學生沒有意識到,衝破的網的縫隙,會在畢業的當口再次閉合。
畢業以後,因為考研沒有成功,梁凡開始找工作。
錯過了秋招,春招就業形勢嚴峻,面試中要求一分鐘演講、無領導小組討論,梁凡看著其他人侃侃而談,“而我乏善可陳”;第一次戴領帶、穿西裝去坐地鐵,總覺得別扭。
經師兄介紹,他進入一家深圳的設計院。那時,梁凡的基本工資是3500元,每個星期會有通宵,加班到12點是常事,他和同事座位邊都放著折疊床。透過辦公室的窗紗,看不到外面的晴雨,公司像一個大型的網咖,都是黑黑的桌面,壓抑的感覺又浮現上來。
三個月後,梁凡辭職了,決定回到學校“二戰”,打算考計算機,因為“前景比較好”。然而,這次考研還是失敗了。
疫情期間,他回到老家重新在線上求職,找工作更加困難,投了100多份簡歷,“很多知道不會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他自嘲成了“家裡蹲”。
怕父母擔憂,梁凡每天表現得積極向上,激情澎湃地說,“今天又投了一個簡歷。”焦慮時,白天黑夜混在一起。
畢業那會兒,余沛想保研到哲學系,她閱讀學術材料,旁聽一些教授的課,但性格害羞,她眼睜睜看著老師下課走人,沒有勇氣上前搭話,把材料提交後,便沒了下文。
到了大四,余沛找不到工作,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看窗外從天亮到天黑,有時候沒有理由大哭。
她去看學校的心理谘詢中心,去精神衛生中心開藥。
快要畢業的那一學期,余沛瘋狂投簡歷,一家比特幣公司給了她回應,“好像抓住了救生圈”。
從學校搬出後,她租住在上海郊區的隔斷房。洗澡水熱五分鐘,下一秒冷水會劈頭蓋臉澆下來,馬桶經常堵,她常常憋到公司才上廁所。每天坐兩個小時的公車去上班,在晚高峰公車站,有一個人專門把乘客推上車才能關上車門,那一刻她總是很害怕。
在比特幣公司,她從秘書做到市場專員,和老闆一起去吃飯,事後被罵不會來事。
跳槽幾次,她加入現在這家留學中介,領導知道她不善於跟別人打交道,安排她做翻譯的工作。而“廢”的感覺難以消散,疫情導致減薪,坐在辦公室,她時常想,工作“沒什麽意義”。 有留學經歷的同事在午飯討論怎麽在上海買房,她插不上嘴。
翻譯的留學案例中,余沛能看到九年級的學生在美國大學教授的帶領下讀女權主義的作品;有學生對經濟學感興趣,中介會安排大學老師交流在大學學經濟是什麽樣的,這些不停地提醒她成長中缺失的那一部分。
“都是一點一點自己琢磨”,在大學接觸戲劇後,杜依苓打算投身影視行業。想象某個人物的可能性讓她非常投入,她一度後悔沒有進入藝術院校。
做中學老師的母親希望她能有份穩定的工作,“不然想炒你就炒你。”杜依苓很傷心,“這個選擇超出了她的生活經驗”,她感到和媽媽不再是高中一心要高考時“同心同德”的狀態。
今年,她原本找到了影視製作的工作,但因為疫情,崗位縮水,實習無法轉正,她不知道何去何從。
“自己”、“沒有”、“工作”。
一位早期的小組成員對組內70多篇長文數據抓取,這是提到最多的三個詞。
今年3月前後,梁凡在失業時加入了一個聚集了很多失意高校學生的QQ群,“互相打氣,晚上連麥,聽各自的故事,唱歌、起外號,很溫馨。”
分享的過程中,有人提議建立豆瓣小組,梁凡回憶,“‘小鎮做題家’有可能就是當時大家隨口起外號叫出來的。”
豆瓣小組很快誕生了,起名“985廢物引進計劃”,廢物,也是985中的five(5)諧音。點進小組,抬頭的介紹中寫著這樣的標語——“985.211失學失業者的新校園,分享失敗故事,討論如何脫困”。

“很多加入小組的985學生都是在迷茫中陷入一種習得性無助”,梁凡一下子感到“並不孤單”,他在組內發帖講述自己的經歷,“很想拉TA(們)一把。”
也是在失業時,小組進入杜依苓的視線,第一眼看到小組名字,985和廢物放在一起,杜依苓覺得“有一種衝突感”,但“一下子就get到了這個點”。
“世界上另一個我”,很多回復中能看到這樣的字眼。短短兩個月,在這個類似“樹洞”的地方,每天數以千計的人湧入,記錄下相似的故事。
“找到了組織!”加入小組那一陣,伍曉冬驚呼,考研剛出了成績,他確定“上不了岸”了。
他發了長文,“決心鼓起勇氣直面過去,也算是記錄一下這幾年的成長和轉變。”
“只是一言不發,檸檬會源源不斷地發給後面的孩子”
面對過去,余沛開始思索,雖然高考代表著某種公平和上升的渠道,“但這只是創口貼,把傷口蓋起來了,沒有真正解決發炎的問題。”
現在,她仍然有“冒名頂替綜合征”,覺得自己是因為太過好運才上了名牌大學,有了這份工作,因為“家境在小鎮算是中等偏上,所以才有機會到另外一個城市去讀書”。她會想起那些留在小鎮的人,重新拾起對故土的關注。
她有意留心聽身邊是否有廣西口音的人,有在肯德基嚼著漢堡、講述輾轉打工經歷的黑瘦女工,地鐵上扛著麻袋的年輕人,還有在老友粉店的研究生。余沛好奇他們背後的經歷,為什麽來到上海,“因為這種經驗非常稀少。”
原先焦慮著的梁凡現在進入了一家國企,準備同時考在職研究生,他打算“先讓生活熱起來”。
梁凡說,身邊有來自小鎮的同學陷入“讀書無用論”,甚至責怪父母拖累自己,他看不慣。
大學時他在廣州的CBD做家教,下課後想找便宜的地方吃飯。臨近傍晚,他看到地鐵工人從地下鑽出來,帶著疲憊的神色。梁凡就跟著他們走,穿過城中村,巷道滴著水,道路有些坑坑窪窪,樓房沒有窗,都是黑黑的大洞,住著人,電線胡亂地拉扯。
這些工人讓他感到親切。餐館裡,他們直接問老闆哪個最便宜,飯加一點鹹菜或清湯面就對付了。梁凡總會念起做過泥水工的父親,這個壞脾氣的男人踏踏實實用一年多蓋了三層樓的房子。
他試圖往回看,關注工人和農村。一個做快遞的朋友夜班、早班輪著上,有時會吐血;村裡一些人家生了大病,往往家裡的錢就會被掏空。梁凡直接在手機裡幫助他們辦理社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還能做什麽。
來自家庭的壓力仍然影響著他,他已經從父親手中接過二三十萬的房貸。但對未來,他抱有樂觀。在新的部門打辯論賽,他還是會手抖,“但是我的聲音已經可以發出來了,還是挺有突破的”,梁凡爽朗地笑著。
大學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杜依苓。她懷念各個學科的課程,“如果大學沒有,我們這一生可能都沒有機會接受人文通識教育。”
她偶爾還會寫作,記錄家鄉那個企業型社會的消失。小鎮的兄弟電廠早在5年前開始衰退,電廠的機組因為不用,在圍觀下,轟隆一聲,被炸倒了。店鋪和菜場在變少,年輕的住戶也搬走了。
如今她回到老家,反而有一種異鄉感,穿衣上會特意保守一些,擔心被問到工作和婚育,“說上海都是用‘回’,雖然回家也是回。”

她琢磨,以後要寫一寫從電廠小鎮裡出來的孩子到大城市的心態變化。她還希望記述小鎮裡的中年人,他們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文藝阿姨寫古詩送別友人,健身大叔鍛煉肌肉……
“‘小鎮做題家’曾經目睹過另外一種生活”,杜依苓認為,“一個人有在底層或者弱勢群體裡的生存經驗,可能比一直生活優渥的人多一重(反思)。”
她明白,城市中產家庭的孩子也會被一些東西困住,“他們的高中同學都是富二代,很多本科去美國讀書。”有朋友跟她吐槽,每次出去玩,大家穿的背的都是奢侈品,這位朋友不禁也開始買。
杜依苓仍然在尋找影視行業的工作機會,她也想過,安穩的工作或許是更好的出路,“但我總覺得,做題家也要有勇氣做點不一樣的,用身份把自己的出路框死,那就是真的屈服於這個標簽了。”
胡婧瑜同樣是被改變的那一個,從交換學校回來後找到了方向,考研法律專業,在今年進入了理想的學校。
雖然“脫坑”,她依然感覺小組內坦誠的交流值得珍重,大學時她就在朋友圈發過相似的吐槽,害怕異樣的眼光,她設置為“僅高中同學可見”,還加了一句“個人意見,不喜勿噴”。
大三時,她在學校辦了“解憂雜貨鋪”的活動,設立面對面談心和問題信箱,發現學弟學妹的迷茫和當年的她一樣多:有人因為減肥患上了暴食症;有人在高考後得知爸爸患上尿毒症,不知道要還債還是繼續讀研……
這一次,她看到有媒體評論小組成員“只會怨天尤人,吐槽社會”。胡婧瑜則想說,“在我們努力把檸檬製成檸檬水的時候,是不是也允許說一句檸檬真酸?只是一言不發的話,檸檬會源源不斷地發給後面的孩子。”
6月,伍曉冬畢業了。他沒去參加畢業典禮,留在寢室看書,不願想起那些“失敗”的記憶。
大一大二的作業本,他丟得差不多了,隻留下一本記錄想法的本子,封面上,灰藍色的海浪漂流,岸邊,燈塔的光映照著天空。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澎湃新聞記者王蓮張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