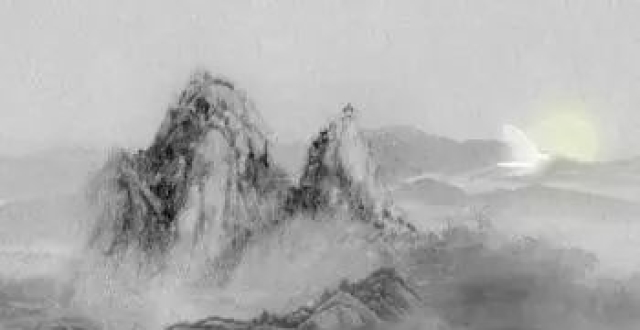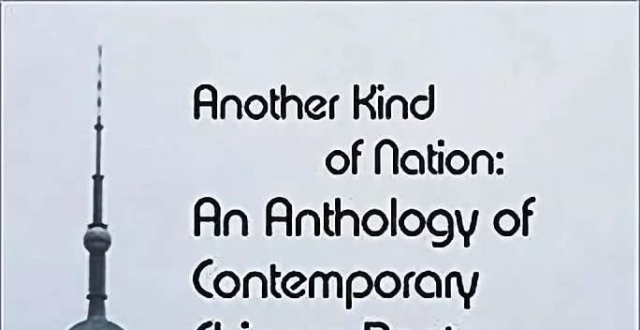1985年6月,在昆明青年路一間從別人那裡借來的小屋中,於堅寫下《尚義街六號》,從此走進了大眾的視野。詩人於堅折桂“2016年度傑出作家”。
於堅說:“在永恆的流動中也有一種最基本的東西,是不動。人類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愛情、都需要朋友、都需要春天、也都需要詩歌。”
那麽,詩如何在?
1.於堅在他的詩歌手記中如是說
詩是無法轉述的

詩就像某種自然之物,在關於它的命名中我們無法感覺、知道到它,我們說什麽是詩的時候,我們必要進入一個詩的場。我們指著一首詩說,這就是詩。
談論詩必須知行合一。我的意思是我們只能在路過一首詩的時候指著它說,這就是詩。就像指著一棵蘋果樹說,這就是蘋果樹一樣。關於蘋果樹的一切描述都與蘋果樹無關,而且越精確距離蘋果樹越遠。
有些關於詩的定義解釋說,詩就是特殊的語言。或者比普通語言更有力量的語言。依然令人茫然,我們知道所有專業術語都是特殊的語言。而比普通語言更有力量的東西包括標語口號。
我們可以在一部小說不在場的情況下描述一部小說。情節、人物、主題……但我們無法描述一首詩。
詩是無法轉述的。
其實談論詩是什麽的人,最終只有舉出詩本身來回答。詩就像中國哲學中的“心”“仁”這些思想一樣,無法概念化。牟宗三先生說,中國文化的開端處著眼點是在生命。這個著眼點也是漢語詩歌的著眼點。詩歌是語言的寺廟,就是最高的語言,但它不是上帝的語言,是活的,生命的語言。克爾凱郭爾說“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動”。有人否定詩歌的生命性,這是受西方詩歌概念的影響,把詩歌理解為對世界的理解。而中國傳統是對世界的感悟。“詩”就像“仁”“心”這些思想一樣無法定義,只能在知行合一中去妙悟,在具體的作品中去格物致知。古代中國的詩論非常清楚這一點,古代詩論從來不說好詩是什麽,隻說詩如何才是好。“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莊子)
2.世間一切皆詩

《歲寒堂詩話》中說:“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世間一切皆詩。這是廣義的說法,包含著中國古人對世界的理解,與古代中國萬物有靈的思想有關。詩,不僅僅意味著分行的文字。詩,也意味人們對世界的形而上的感受。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大音稀聲”是對這種感受的注解。老子的理論通常在傑出的詩人那裡,被理解為詩的基本道理。在中國,詩總是更傾向於道家的思想。“世間一切皆詩”是詩人們的一個出發點,但不僅僅是詩人的出發點,也是古代中國人理解世界的基本點。李白說“大塊假我以文章”。“世間一切皆詩”來自“道法自然”的思想。與西方的天堂地獄的劃分不同。有了“世間一切皆詩”的認識,才有天人合一。如果對世界持的是否定的,改造的、拯救者、解放者,革命、救世主的態度,人是不可能與天合一的。世間一切皆詩是中國詩人的一個寫作立場,也是中國文明的基本立場。在此立場上,我們才出發作為詩人。
“世間一切皆詩”,是說,詩意是存在的本質。“天地無德”,這個“無德”就是詩意。詩意是無,詩是有。
大地、世界、人生本來就是詩意的,詩意是先驗的。沒有詩歌它們也存在於詩意中。但這個詩意是被隱匿在自然中的,語言把詩意敞開。
詩就是文化,以文去化。天人合一,如何一,通過文來“道法自然”,化為一。
今天的大多數詩歌寫得很便宜,語言成了把口水變成文字的工具,表面上很有活力,其實與過去時代將語言當成意識形態的工具一樣。
詩是激活詩意的語言,當然也可以說是詩意的載體,但載體這個詞,聽起來像是卡車拉著水泥一樣,而詩意是融化在語言之水的中的鹽巴,已經天人合一了。
詩意是天然的,先於世界存在的,“世間一切皆詩”這個“詩”就是指詩意。只有語言出現了,把詩意“文化”,詩才誕生。
3.讀一首詩就是被擊中
而不是被教育

一首詩是一個場。它在召喚。
古代判斷好詩的方式是依靠經驗和時間。依據閱讀經驗,因為漢語詩歌不是“一窮二白”的。古典詩歌與白話詩歌形式不同,但普遍經驗是一致的,否則今日的人就不要說他們會被古代詩歌感動。我相信只要排除偏見,尊重感覺和經驗,就像我們總是被已經成為經典的詩歌感動一樣,(在那裡我們當然知道什麽是好詩)我們可以同樣在當代詩歌中感覺甚至認知到同樣傑出的詩歌,與這種感覺和認知的可靠性比較起來,所謂“詩歌標準”——尤其是當它被詩歌的正式發表、詩歌評獎、詩歌選本、詩歌史、詩歌評論僅僅作為維持話語權力的遊標卡尺去利用時——是完全不能信任的。
普遍經驗其實是某種叫作“無”的東西。詩歌的持久性不在於它的語言形式,而在於它通過它時代的語言表達的那種普遍性的不可言傳的“無”。永恆魅力來自詩所傳達的“無”,而不是“有”。我們是被那種言已盡而意無窮的“無”所動。
我們還是可以依據閱讀經驗辨別出什麽是好詩。好詩的要素已經約定俗成。對好詩的感覺已經積澱在我們關於語言的經驗中。詩就是那些就是可以蠱惑人心的語詞。當你被蠱惑的時候,你就進入了一首詩。那些語詞經過詩人的組合,具有返魅的力量。
狄金森說:“它令我全身冰冷,連火焰也無法使我溫暖。我知道那就是詩。假如我肉體上感到天靈蓋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詩。”說得好,詩是一種可以喚起感覺,令人心動並體驗到的語言。
讀一首詩就是被擊中。而不是被教育。
4.好的詩歌是七級浮屠

最得人心的詩是最具魅力的詩。是為天地立心的詩。
而什麽語言會構成一個得人心的具有魅力的場,這是無法確定的。任何語言都存在這個可能,任何組合方式都存在著這個可能。在詩歌上,詩人必須承認不可知,詩歌具有巫術的特徵。今天,世界上的一切都在量化,而詩也許是最後的無法量化的。這也是詩歌得以在技術時代獨立並高踞於精神生活之巔的原因。
一首魅力四射的詩是一個塔。塔的基礎部分人人可進可懂。個人的修養(心靈、感覺、閱讀積澱、知識結構)決定你可以進入詩的哪一層。詩最核心的塔頂部分,只有少數人可以進入。但如果只有這個高處不勝寒的少數沒有下面的基礎,塔就飄在天上。
齊白石說:“太似則媚俗,不似則欺世”,媚俗的詩只有一層,欺世的詩只有飄在天上的尖。
好詩是,其最大的一圈是引車賣漿者流都明白的漢語。其最小的一圈,是禪。好的詩歌是七級浮屠。深度屬於最小最核心的一圈,最基礎的部分,那個外沿只要懂漢語都可以進去。
一座塔是一個立體的場,也可以用佛教的“壇城”來比喻。“漢魏古詩,天氣混沌,難以句摘。”王國維所謂“有篇無句”,是新詩天氣。
一首詩就是一個語言的場,“篇終接渾茫”。就是語言已經被創造成為一個場,進入“意有所隨,不可以言傳”的境界。主題、意義、情緒、修辭、深度……都是小於場的東西,而這個場是心的在場,語言在這裡已經消失。所謂得意忘言。又說到玄學了,確實,心是什麽,在中國經驗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無法定義。《論語》講的就是心,但孔子始終只是在說心在人生中的不同狀態。“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詩是語言創造的一個存在之場,離開了這個場,詩就不存在。
場創造天氣。有天氣的詩就是王國維說的那種有篇無句的詩用意境、意象來說現代詩太小,白話詩的語言是比古典詩歌的語言更豐富、更深入細節、更具體的語言。因為在1840 年以後,中國已經不是古典的中國,漢語已經不是古典的漢語,漢語的太空被巨大地釋放出來,這個太空過去被遮蔽在典雅的字文化中。
5.詩如何在
我只可以像一個巫師那樣說話

在這個一切都平台化的時代,民主蠱惑人心。但我以為詩歌是貴族氣質的藝術,為天地立心是天才、王者、巫師的事業,而不是“怎麽都行的”大眾化民主運動。於是我們時代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求詩歌編輯以及其他擁有權力傳播詩歌的人們的良知——因為他們佔據著一個平台以外的傳統高地,這是一個事實,並非迷信。別假裝著不知道你們擔負著詩歌傳播和守護的重任,讀者把詩歌刊物視為詩歌水準而不是平台上的化裝舞會——必須具有良知、清潔的精神、必須尊重經驗、保持著感覺和激情,在平台的狂歡之外保持著冷靜,你們並非權威,但你們至少要向讀者繼續這樣的經驗,他們沒有時間的去瀏覽那個遼闊的平台,跋涉沼澤,他們只能信任有限的高地。高地比平台更危險的是,如果它一旦墮落,它的海拔會低於海平面,比沼澤地更黑暗。
詩歌是語言的如何說的歷史,而不是說什麽的歷史。“什麽”, 其實自人類出現以後,再沒有進步過,將來也不大可能進步多少,因為“什麽”的進步在20 世紀的種種實驗中已經一再被證明是災難性的。人類關於“什麽”的在權力驅使下的探索、革命,一旦稍停,人類就重返故道。詩歌上的石破天驚總是在如何說上,它令已經趨於沉悶的“什麽”再次活過來,成為我們時代的最通順的感受。“如何說”實際上總是“石破天驚”地重返“說什麽”的歷史,就像大海,總是嶄新的波浪,總是陳舊的大陸。我的意思是,所謂好的詩歌,是那種在人類的閱讀歷史中,能夠以原創的言說方式、鮮明的個人風感應心靈、激活感覺和普遍經驗的詩歌,所謂“具體的普遍性”,它與過去詩歌傳統之間的關係是活力復活的通順而不是標新立異的斷裂。
沒有比詩歌寫作更困難的事了,每個詩人都知道,他不是在白紙上寫作,他是在語言的歷史中寫作,你寫每一行,都有已經寫下的幾千行在睥睨著你呢。詩人永遠不可能從第一行寫起,他總是從過去已經開始的第某行繼續寫下去。因此你的寫作總是與過去的寫作有一個上下文的關係,通順的關係。在我看來,那些通順的詩歌,必然是可以繼續下去延續時間的詩歌。
詩如何在,我只可以像一個巫師那樣說話。
本文節選自《還鄉的可能性》,於堅/著
尋回日常生活的神性
完整呈現詩人過去十年對詩歌的思考和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