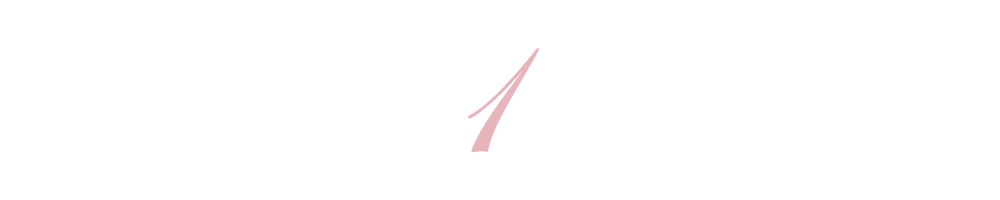作者:秦寬;口述:何冉
四小時的高速列車旅程之後,柏亮(化名)回到了北京。這個14歲的孩子,個子又長高了,大圓臉,一頭茂密的黑發。但是,看起來還是內斂、沉默,不愛說話。
問及返鄉的情況,他停頓了十幾秒,認真地掰了掰手指說:“我被老師打了三次。”去年,他回河南駐馬店,在陌生的老家獨自開始了學習和生活。
這個暑假,和柏亮一同來北京的還有11個孩子,他們來自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11個地方。一年前,為了順利升學,他們告別了北京,從流動兒童變為留守兒童。
過去一年,“新公民計劃”(關注流動兒童教育的倡導機構)發起了一項追蹤流動兒童返鄉的計劃。一年來,項目主管何冉與同事們追訪這些被回流的孩子,跟他們下鄉、調查,與他們的父母和老師對話。何冉說,他們記錄下的,是在時代變革下被迫返鄉的孩子的個體遭遇,這遭遇中有在新生活裡的不適與消沉,尷尬與沉默,以及他們對自身命運轉變後的思考。

以下是何冉的口述:
這次暑假,我們追蹤的25個返鄉的孩子當中,有一批回到北京和父母團聚。為此我們做了一個“Summer Fun”的活動。
我發現他們真的是長大了,都進入了青春期。男生女生見面,開始靦腆,一些孩子很大人式地和我問好:“老師,你好嗎?”
但一年前,我給他們帶班的時候,他們還追著打呢,有同學做錯事,他們還要告老師。現在,這些都變化了。
過去一年,我做返鄉追蹤,到孩子們家裡去家訪、問卷調查,或者直接打電話,雖然次數不少,但看到的都是很窄的面。聊天記錄裡清一色是與成績、考試有關的內容。
借助這次活動,我想把觀察範圍擴展一些,了解他們返鄉後的生活。沒想到的是,原來背後的故事是如此複雜、沉重。
回流後,如何跨過應試教育的大橋
其中一個孩子叫王笑語(化名)。她14歲,安徽籍,聽話、乖巧,說話時總是笑眯眯的。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她學習很好,經常能在班裡排到第一,英語、語文也常年排前。
她是和媽媽一同回老家的。爸爸在北京工地上做小包工頭,以前媽媽就跟著,給工友做飯。為了照顧王笑語,媽媽放棄了北京的工作,家裡的收入也變少了。
父母的陪伴,是我們把她作為追蹤對象的原因——我們希望能在追蹤中,看到父母一方在孩子回流後的作用。我們追蹤的25個孩子中,有20個都是獨自返鄉的,父母留在北京,在老家由爺爺奶奶照顧,個別一些是獨自生活。從這個層面看,王笑語是幸運的。
然而,回到老家的日子也並不好過。
一個首當其衝的困境是找學校。王笑語的媽媽在返鄉之前,拚命為女兒找學校。
她想把女兒轉去當地最好的公立初中去。由於她們老家的房子在農村,按照學區房政策,女兒是無法上這所初中的。為了讀這個初中,媽媽在附近找了一個學區房,和別人簽了一年的租住合約。回去的一年前,她就做了很多的準備。
為了轉學籍,她前前後後找過校長三次。最開始,她以為女兒的學籍在北京,因為學校是北京的。但在轉學籍的過程中,問題發生了。由於北京這所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學校就把孩子們的學籍統一掛靠到河南的一所學校。她媽媽為了這個事,特意跑到河南,去辦轉學籍手續,托人、蓋章、開證明。
與此同時,成績下滑和學業壓力的增長也立竿見影。回到安徽後,王笑語上的那所學校的教育質量還不錯,但第一次模擬考,她的數學成績就不及格。
王笑語的媽媽很強勢,非常緊張女兒的學習。那次模擬考後,她經常著急地給我們打電話:“哎呀,她(王笑語)還每次對自己的成績滿意”,“她就是不努力啊”……隔著話筒都能感受到她的焦慮。
這樣的焦慮也一直壓迫著王笑語。這個暑假前的期末考,笑語的數學還是沒有考得很好。她和媽媽說,這是教材的原因,在安徽老家,用的不是她熟悉的北京那套人教版教材,而是滬教版的。回去後的這一年,她一直對教材感到不適應。
這不得不提到北京打工子弟的教育情況。要知道,在北京,很多打工子弟學校,質量真的很差。一方面,老師大多是沒有教師資質的,高職、大專畢業的老師很多。
另一方面,很多北京的打工子弟學校實行“包班製”,即一個老師承包一個班級的所有課程,有的還會跨學年教學,教育質量真的很差。所以回流後,學生的成績普遍下降也就不奇怪了。跨入應試教育的大橋裡,他們的起點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在北京沒有得到有質量的教育。

以我們追蹤的這25個回流學生為例,回到老家後,沒有一個人的名次是進步的。就連曾經在北京排名第一的王笑語,最好時,也才能排到班裡的13名。
另一個問題就是體罰。幾乎每一個被追蹤的孩子都向我們報告過,在學校,他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體罰和虐待。王笑語就曾遭到過數學、英語老師的多次體罰。
去年7月,我去王笑語的老家做家訪,得知一個驚人的現象。當時,她所在的班級有個規定,每個月的月考都會對學生實施體罰。舉例來說,一科的總成績是100分,60分及格,但老師會把那個目標定得高一些,比如80分以上。以這個分數為基準線,差多少分,就會被用戒尺或者棍子打多少次手。英文科目的懲罰尤其嚴厲——由於單詞是英文教學中非常重要的內容,老師會經常抽查學生默單詞。但如果默寫出了錯,學生就經常被打耳光,錯一個,打一個。
這不是老師打,而是同桌之間相互打。他錯了,你打他。你錯了,他也打你,相互之間扇巴掌。王笑語和她的同桌總是打得輕。但老師說,如果聽不到響聲,老師會親自動手。面對體罰,班裡的同學幾乎無一幸免。
接受體罰的心態是一點點培養起來的。有一次電話訪談,我問她在學校遭遇的暴力。她說,最開始,也會覺得被老師打很難堪,而且特別疼。但因為她們班成績最好的同學也被打過,這讓她覺得,自己的遭遇也不算什麽了。這非常可怕,暴力已經在他們的學習中獲得了合理性,他們會習以為常。
不僅如此,暴力還得到了家長的默許和加持。去年,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我和她的媽媽做過一次長時間的訪談,提到過女兒遭受的暴力。她媽媽聽到後,就在視頻裡一直笑,一直笑,說女兒被打也沒什麽,老師也是為她好啊。

無法交流的孤獨感
除了學習上的困境,融入當地社會環境也成為一重障礙,他們甚至無法融入那個“老家”。
王笑語和妹妹出生在北京,成長也在北京。媽媽是江西的,所以當她們返鄉時,只是回到了一個屬於爸爸的地方,非常陌生。這就是大部分流動兒童家庭的寫照。
語言成為融入新環境的第一重障礙。王笑語和媽媽完全不會說當地方言,奶奶和她交流,用的是很蹩腳的國語,她經常聽不懂。大多的日常交流是吃飯、寫作業,完全沒有親人間那種深度的情感交談。
環境的孤僻也體現在當地的物理空間上。去年7月中旬,在她返鄉後的十多天,我去她家探訪。她住在奶奶家,那是一個很典型鄉村二層樓房,後面是山坡,坡上種滿了奇異果,下面就是碧綠的池塘和菜園。
在她的老家,房子之間至少相隔十幾米。這裡一戶,那裡一戶,零零散散。在這種顯性的孤僻環境下,她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朋友。“一個朋友都沒有。”她這樣告訴我。
好在笑語有媽媽陪同,老家還有親人——有熟悉的人陪伴,這在流動兒童回流時非常重要。
為什麽我們會在回流過程中特別關注王笑語的媽媽?因為,她在心理上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她是江西人,語言的尷尬讓她在老家無法找到工作。在老家,婆婆和其他親人也沒辦法和她溝通。現在過年了,她也不回北京了,因為沒工作,還要花路費。她就一直待在村子裡。為了女兒上學,她就在學校旁邊租了個房子陪讀。
她沒有朋友。以前在北京,會經常在朋友圈轉發一些很正能量的東西,“要努力啊”,“今天又是很美好的一天啊”,“只有付出才會有收獲”這類文章。
回去一段時間後,朋友圈的內容全變了。去年過年,她三天兩頭髮一些對婚姻的理解:男人對我不好,我就怎麽怎麽樣。不要變心……我想,或許是聚少離多,她的婚姻出現問題了,而她也不知道,該怎麽辦。
由父母陪伴的流動兒童情況尚且如此,那些獨自返鄉生活的孩子,就更不容樂觀了。
在我們追蹤的25個孩子中,還有一個典型案例是柏亮,他和另外4個孩子都是獨自返鄉的,在老家,他們獨自生活。柏亮長得清秀,包子臉,個子高,性格沉默。或許是繼承了爸爸的性格,他和他哥哥都很敏感,不善表達。
柏亮的爸爸在北京的麥當勞做外賣員,初中沒讀完就去打工了。媽媽也沒上過學,不識字。
小升初的時候,爸爸托關係,讓他一個人回河南老家念中學了。那時候,哥哥還在老家,爸爸想著,弟弟回去了,可以由哥哥照看著。但回去不久,因為工作調動,哥哥也走了,家裡就剩下了柏亮一個。
平時,我和他爸爸通話比較多,我們聊柏亮的學習、成長上的困惑。最近最頻繁的話題,是柏亮找學校的問題,因為他被退學了。
其實回流後,柏亮一直無法在新學校裡安頓。去年9月20號,學校剛剛開學一個月,我們對這些回流學生適應環境的狀況做過一個跟蹤記錄。
柏亮的成績很差,排名倒數的那種,他很沉迷遊戲。在北京的時候,玩他爸的手機就很瘋狂,一打遊戲就停不下來。他是那種典型的嵌入到科技和遊戲環境裡的農三代,就像“三和大神”裡的那些人,這是這一代打工子弟的特徵。

但回到老家,手機就成了老師的“階級敵人”——所有學生都不能帶手機。在一次搜查中,柏亮的手機被老師沒收了。
當時,他們宿舍同學湊錢去買電子煙,結果被老師抓了個現行,遭到當場責罵,還在全校公告。宿舍老師搜他們的房間,所有角落都沒放過,最終在床底下搜出柏亮的手機,收繳了。
事發那一周,我剛好去他河南老家調研。我問他手機被收走後的心境。他說自己特別不開心,雖然平時和父母打電話也不說什麽話,但還是特別不適應。原來除了玩遊戲,手機也是他和父母交流的工具,是情感的紐帶。他感到那個扭斷被切斷了,特別孤獨。
後來的日子也不理想。他被老師安排坐在教室最後一個位置,下課時也不許出去,周圍的人都在說話,但他跟那些孩子不熟悉,很少和他們說話。他其實意識到自己的困境,也和父母提過。在返鄉之前,他明確地跟他媽媽說,可不可以回去陪他。媽媽的回答是,不可以,因為媽媽要掙錢,如果沒有錢,就沒有生活來源了。
這些兒童回到老家的日子就能很好嗎?不見得。在老家,柏亮完全是一個人生活。一個星期四,我去他家家訪,和他生活了兩天,完整地觀察了他的生活。
那也是一套兩層樓的房子,附帶一個大院子。進去時,要穿過一棵大樹,樹枝亂叉,幾乎都垂到地下了,附近全部是雜草。人從樹的縫隙裡穿過去,感覺進入了一個叢林。小草高得沒過了我的小腿。
把生鏽的們推開,柏亮家的院子裡都是磚頭,雜草就從磚頭裡迸出來,像一排排稻田。
在柏亮的老家,除了電以外,沒有通水,沒通燃氣。要吃水,必須在外面的龍頭接。廚房裡除了鹽,什麽都沒有。周末他從學校回家,就煮速凍水餃解決。
他的房間有個床,但床上沒有褥子。冬天,他鋪上床單,一個蓋被,就這麽睡下去,陰濕濕的。後來,他也不睡這個房間了,因為積的灰很厚,他開始睡客廳沙發。
其實也不是因為客廳的環境,而是房間裡沒有的wifi。睡客廳,他能蹭到鄰居家的wifi。“搬家”以後,他經常躺在客廳的沙發上,墊一個褥子,瘋狂地打遊戲,打到三更半夜。
在這個環境裡,你無時無刻都會感到害怕。
有天晚上九點多,他洗漱完畢,我要到附近的賓館落腳了,請他帶我離開。
沒有路燈,月光下是朦朧的樹影,環境確實陰森。我問他,你怕嗎?這是以前我從沒想過的問題。他說,其實他也怕,但玩手機特別累了,就能睡著了。因為長年陪伴他的是手機而不是親人。所以現在,他跟手機比較親。面臨失學後,他曾一度不想來北京,因為害怕媽媽會繳了他的手機——“我離得開父母,但離不開手機了”。這已經變成他生活情感的剛需。
但現在,他沒有選擇了。
7月3號,他爸爸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說要來北京給他找學校,他被老師勸退了。老師的理由是,他不聽話,學習不好,也經常不寫作業,管不了他。學校明文規定不準帶手機,但他帶頭在寢室裡玩遊戲,犯了規。
他的爸爸現在正焦頭爛額地找學校。他給了柏亮三個選擇:要麽回到北京上初中,但他非常不甘心,當時能夠回老家上學非常不容易,找了好多層關係。另一個,就是在縣城的一個鎮裡,找個關係送進鎮上的初中。還有,由於柏亮當時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學籍是掛靠在河南固始縣的一所學校,他現在也想把孩子送到固始縣去上學。

我當時聽到這個就蒙了。我問他,您知不知道固始縣在哪裡?他說知道,就在距他家500公里的地方。我心想,好歹還知道。那個地方,他爸爸從來都沒去過,就決定把孩子一個人丟在固始。我又問,那他放假怎麽辦呢?他爸說,想辦法唄,把孩子丟在老師家或者住學校。
我還震驚的是,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怎麽有權力勸退一個孩子?
我讓他先關注孩子的心理。因為被學校退學後,孩子出現任何問題,任何反常的事,一點兒都不出乎意料的……這個環境真的是要把人逼死。
不過,正當我們都焦頭爛額的時候,這件事很戲劇性地作罷了。因為我特地去查了他掛靠學籍的那個學校,原來人家那裡根本沒初中,這條路也堵了。
退學,其實是柏亮過去一年狀態的縮影。
柏亮一直處於被安排的狀態。在情感表達和交流中,他從來沒有對父親的提議表達過異議,包括這次回北京。我問他,你一點都不想回來嗎?但他對這種問題沒有太多表達欲,沒有回答。
我問過他一次,願不願意回老家。他說,我父親告訴我,下個星期我必須自己回去。所以,你會發現,這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知的,他的內心從來沒有被關照過。
他是一個敏感的孩子。得知被退學後,我給他打電話,但關於為什麽會被學校退學這種問題,是不太能問的。所以我換了個問法,問他什麽時候來北京。“還不知道,但肯定來。”我說,那你什麽時候來,帶多少東西,坐什麽車來?“坐火車,東西的話,會把衣服都帶過來。”因為,他其實知道自己可能要來北京上學了。
你會發現,在這個回流的過程中,孩子基本被當成了一個問題、包袱、工具,從來沒有被當成一個有尊嚴的人。
父母的意識
在追蹤的過程中,我們還非常關注一個部分——父母的意識。
返鄉前的一個月,我就開始關注父母對這個變化的看法。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我問過一個媽媽。她有兩個孩子,女兒是姐姐,兒子是弟弟,也是我追蹤的對象。
姐姐也是在北京出生、長大的。但讀到五年級時,她所念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被拆了。被拆後,有比較前衛的家長會去區教育局表達意見,讓政府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當時,政策還很寬鬆,區政府很快解決了問題——把孩子派到一個比較近的公立學校。所以五六年級,姐姐是在公立學校上的,並且有北京學籍。當她從北京轉回老家時,程序非常簡單,很容易就被接收。但現在回流的弟弟完全得不到這樣的待遇。
我問他的父母,為什麽姐姐的學校被拆,政府就開了一個口子?媽媽和爸爸就一直在強調,這是姐姐趕上好時候,運氣好。但其實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拆”其實不是主要的,政府願不願意接受這些孩子才是主要的。她回答,道理他們都懂,他們明白這種變化,會默默接受。
不過,也有一些敏感的父母,尤其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媽媽。被回流的,往往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而這批父母大約在30多歲。如果和他們聊政策,他們就會吐槽:“憑什麽啊, 我們也納了稅的”;“為什麽不讓人上啊?”......會吐槽這些話。
但是父母年紀越大,越多的態度就是“沒辦法”——政策就是這樣的,沒辦法。但這些父母其實也不知道那個政策是什麽。這和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有關。

北京,那個曾經被當作家的地方
這次回來,我覺得他們真的發生了很大變化。那天,我在亮馬橋地鐵站接他們。我很久沒有見他們了,有的兩個月,有的超過一年。一些男生長高了,長身體了。從地鐵口出來看到我的時候,他們遠遠地揮手。靠近時,很主動地舉起手,和我擊掌。以前小學的時候,完全不這樣的。
那個瞬間,讓我覺得,原來北京的所有的東西,不管是曾經的住所,還是我們這些老師、同學,都是被他們記得的,是他們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了。
前一段時間,我還和孩子們聊過關於北京印象。我問柏亮,你還想來北京上學嗎?他說,我願意。我馬上又問他,將來你工作了,擇一個城市定居,你會去哪?
他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