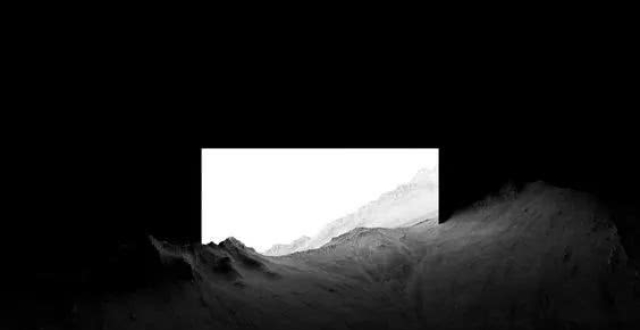由北京演出公司和天橋藝術中心聯合推出的第二屆“老舍國際戲劇節”9月7日就要以《老舍趕集》開幕了。提起老舍與戲劇,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茶館》《龍須溝》這些老舍約60年前創作的經典劇目;其次則是近年從老舍文學作品中改編的新京味兒戲劇,如林兆華的《老舍五則》,方旭的《我這一輩子》《二馬》《離婚》《老舍趕集》等。其實,老舍與戲劇的關係遠不止此。北京曲劇這個地方劇種,就是老舍在1952年為之正式命名的。北京曲劇團演出的第一部戲就是老舍1952年創作的《柳樹井》。近年來,由老舍作品改編的曲劇《茶館》《正紅旗下》一直是北京曲劇團的重要演出劇目。老舍還創作過京劇《十五貫》,寫過大量的鼓詞、相聲。
以老捨的名字來為北京本地的戲劇節冠名,並不僅僅因為老舍是一個戲劇家,還因為老捨的整個文學創作,小說、戲劇、散文、詩歌合在一起,共同奠定了一種既有鮮明京味兒特色、又有深沉的民族之思、還有廣闊國際文化視野的現代北京精神。
8月下旬是最宜於到老舍故居——燈市口豐富胡同19號的丹柿小院坐一坐、想一想的日子。站在那四合院稀疏的樹影下,想象著老舍先生當年在院裡澆花、打太極拳的情景,老舍筆下那些車夫、巡警、小商人、職員仿佛仍在外面的胡同、馬路上來來往往,老北京的況味也就自然撲進你的心頭。你也便不能不去深思老捨的文學精神到底是什麽。

安恬的故園之思
“面向著積水潭,背後是城牆,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無所求也無可怕,像小兒安睡在搖籃裡。”老舍對北京的情感是一個人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鄉土的眷戀。在他心中,北京不是彰顯皇權或施展政治謀略之地,而是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安寧的溫馨家園。故土北京給他的審美感受,不是由陌生化所產生的震驚感,而是因熟悉所滋養出的親切感。“我的最初的知識與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裡,我的性格與脾氣裡有許多地方是這古城所賜給的。”正是這城與人和諧共生的關係,奠定了老舍生命的安寧感。
老舍還說別人可能喜歡北平的“書多古物多”,而他自己則隻“喜愛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從日常起居、瓜果蔬菜中尋找“詩似的美麗”、體驗人生的“清福”,老捨的北京風物書寫中透出對普通人生活方式的詩意闡發。這種詩意沒有出塵避世的意味,而與平凡人生密不可分。老舍審視北京風物的本地居民視角還具有平民特色,而不同於鍾鳴鼎食的王公貴族的視角或全然不問柴米油鹽的文人墨客的視角。同時,老舍筆下的北京詩情,是都市平民日常生活與鄉土田園詩意的融合,也絕然不同於海派文學中的都市摩登、西洋風味。
對故土的熱愛,也成全了老捨的文學成就。故鄉能在心裡扎根,真是有福!無論是漂泊在倫敦、在新加坡、在美國,還是輾轉於青島、武漢、重慶,他都是那帶線的風箏,心有所系,心有所歸。

老舍趕集之《理想家庭》
荒涼的生命悲感
讀老捨的作品,我既感動於他對筆下人物的熱愛之情,也震懾於他那悲劇性的生命體驗。他是那麽喜歡自己創造的洋車夫祥子,敘述起祥子的故事,他就像一個慈愛的父親在向左鄰右舍絮叨獨子的種種行狀。但是,老捨的故事走向從來都不是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而總是好人沒有善終。他最痛恨的就是大眾文化“光明尾巴”中的精神麻醉。他讓心愛的祥子最終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他痛心地告訴讀者,這不是祥子自己的過錯,而是不公平的社會沒有給祥子生路。“壞尜尜是好人削成的。”他代祥子向社會發出了沉痛的控訴。凡貼著老捨的心而生長出來的小說人物,他總是無奈地認定著他們無地生存的命運。《駱駝祥子》中的祥子最終“不知道何時何地會埋起他自己來”,《月牙兒》中的母女倆除了賣淫沒有別的生存之路,《我這一輩子》中的巡警老景一片黯淡,《茶館》中的王利發在絕望中上吊自盡。是多麽沉重的生命悲感,才能營造出這一系列荒涼的景象?!
這種骨子裡的荒涼感來自何處?是投射了早年父亡家貧的困窘生活印跡?還是感應了旗人在清末歷史劇變中的悲劇命運?抑或是體驗了中華民族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屢遭強權踐凌的恥辱?或者說,只是基於天賦的個性氣質?也許準確的判斷應該是來自於這四種因素的合力。
豪橫中的道德堅守
儘管老舍代祥子們對社會不公發出了最沉痛的控訴,但是,他從來都不願意社會走向動蕩,而十分擔心人的道德敗壞。他盼望有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秩序,能讓勤勉的車夫、本分的商人、負責任的巡警靠自己的本事吃上飯、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但是,由什麽樣的路徑能建成這樣的社會,他不知道。

老舍趕集之《黑白李》
他痛恨各種投機取巧、恃強凌弱、不負責任。他讚賞不計名利的埋頭苦乾、自律自為。他常用“豪橫”這個詞讚美在貧困中自尊自愛、剛強而有骨氣的人。“肚子裡可是只有點稀粥與窩窩頭,身上到冬天沒有一件厚實的棉襖,我不求人白給點什麽,還講仗著力氣與本事掙飯吃,豪橫了一輩子,到死我還不能輸這口氣。”這是小說《我這一輩子》中那個失業老巡警的自白。豪橫的人,硬氣是對自己的,不是對別人的。散文《我的母親》不僅寫了母子深情,還寫出了母親“軟而硬”的個性。這軟便是不與人較勁,凡事讓別人,有委屈自己受;這硬便是勇於承擔責任,從容應對生活的種種艱辛。
老舍繼承了母親這種肯吃虧、有擔當的品質,他一輩子也是那樣的內方外圓、孤高豪橫。所以,他受辱的時候,只能選擇走向那一條決絕的自我了結之路。生命的尊嚴感,使得他不能忍辱偷生。他是良民,但也必須是良序社會才配得上他。可事實上,他一生的多數時光都是在亂世中度過。
幽默中無望的自我救贖
老舍先生生於亂世,雖然親近過佛教,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但最終還是以非教徒的方式來探尋人的救贖之路。他以兩種方法來為自己和自己筆下的不幸者尋找精神支撐。一種是內心中的道德堅守,那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另一種是戲謔與幽默,這在別人看來也許不如倫理道德那麽重要,但對他來說卻絕不是可有可無。

老舍趕集之《鄰居們》
他笑一切可笑之事,被人戲封為“笑王”。他的幽默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悲鬱為內核”的幽默,另一種是純粹輕鬆戲謔的幽默。他有時含著眼淚笑生活中的矛盾。“張大哥的全身整個兒是顯微鏡兼天平……在天平上,麻子與近視眼恰好兩相抵消,上等婚姻。”長篇小說《離婚》以幽默的態度諷刺張大哥做媒中的庸俗標準,傳達的是老舍對市民庸常生命狀態的深刻反思。“改良!改良!越改越涼,冰涼!”話劇《茶館》中夥計李三的這句台詞,讓觀眾忍俊不禁,卻也讓人覺得心酸。直面亂世中荒涼無望的生命體驗,老舍往往只能從自己的幽默中求一絲無奈的達觀。他並沒有像魯迅那樣去建構反抗絕望的生命哲學,而是常常把悲情抒發與幽默戲謔的敘述態度結合起來,建構起悲喜交融的獨特的美學風格。有時,老舍並沒有那麽沉重,純然只是為了輕鬆的愉悅而會心地笑著。長篇小說《牛天賜傳》,一直以“英雄”稱謂調侃普通孩子牛天賜,以“換毛的雞”“隱士賣梨”“狗長犄角”對牛天賜進行善意的嘲笑。《牛天賜傳》這些輕鬆戲謔,往往與情節渾然一體,並不像老舍最早的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那樣戲謔常常因與情節脫節而造成小說結構的拖遝。
老捨的幽默語言充滿民間諧趣,其格調不同於林語堂所倡導的紳士階層的衝淡式的幽默,而更多語言狂歡的意味。他要用笑聲為那蕭索的世界點上一串炮仗,為自己、為筆下的苦人製造一點生命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