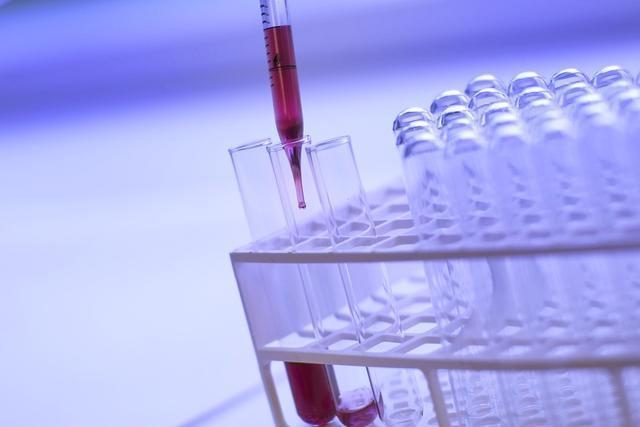【天才精選】是天才捕手的故事分享欄目
由陳拙搜尋已被記錄,但大多未被看過的好故事
以謹慎的態度甄選
以達到續命和長見識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陳拙。
之前有個遊戲特別火,叫《瘟疫公司》,是一款以傳染病為題材的策略遊戲。要求玩家將所選定的病原體不斷改良優化,散布到世界各地,從而製造一場超級瘟疫,最終讓全人類死於該傳染病。
遊戲裡充滿了虛擬和假設,但創意的內核,是人類對傳染病毒大面積擴散的真實恐慌。
這兩天趕上換季,時而咳嗽,正在看的一本書《血疫》就顯得尤其應景。這本書講了一種讓人談之色變的傳染病毒“埃博拉”,它的症狀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沾上它,你就行屍走肉了。
對這種病毒,不光我慫,就連史蒂芬金和奧巴馬都覺得害怕,因為這不是小說,而是真實。
在現實裡遭遇一場末日災難會是怎樣的場景?
看完今天的故事,你會知道,文明與病毒之間,有時隻隔了一個班機的距離。
故事名稱:嗜血病毒
故事編號:天才精選014
故事來源:《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事件時間:1980年1月
嗜血病毒
理查德·普雷斯頓/文
航空線路將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連成網絡。
只要沿著這個網絡,來自熱帶雨林的危險病毒,能在二十四小時內,乘飛機抵達地球上的任何城市。
本來,夏爾·莫內只是這個網絡中,一名普通乘客,但在他的體內,隱藏著無比致命的病毒——埃博拉。
暈機的乘客
莫內搭乘的是螺旋槳驅動的小飛機,可以容納35名乘客。在非洲,這種通勤班機總能做得滿滿當當,莫內這趟也不例外。
飛機發動引擎,飛過維多利亞湖。湛藍的湖水波光閃爍,湖面上有幾隻漁民的獨木舟。
然後轉向東方,越過遍布茶園和小農莊的綠色丘陵。
飛機飛過森林條帶,飛過扎堆修建的圓形茅草屋,飛過鐵皮屋頂的村莊。地勢陡降,變成岩架和溝壑,顏色也從綠色變成棕色。
此刻正越過東非大裂谷。機上的人望著窗外,一圈圈的刺灌叢裡有星星點點的茅草屋,牛踏出的小徑從茅草屋向外輻射。
螺旋槳隆隆轟鳴,飛機經過裂谷上空的蓬松積雲,機身隨之抖動搖晃。
莫內暈機了。
機艙密閉,空氣循環流通。要是有什麽異味,立刻就會被覺察。而且通勤班機的座位狹小而擁擠,機艙裡有點響動都會被注意到。
這個病懨懨的男人蜷縮在座位上。他有點不對勁,但在場的人說不清究竟出了什麽問題。
他用暈機袋捂著嘴,從肺部深處咳嗽,把某些東西吐進袋子。
袋子漸漸鼓起來。他面無表情地環顧四周,嘴唇上沾著混有黑色斑塊的紅色粘液,就像在嚼咖啡渣。
他的眼睛顏色像紅寶石,臉上都是瘀傷。
症狀在幾天前就開始出現了。最初的星狀紅斑已經擴散,合並成了大片的紫色團塊,整個頭部幾乎都變成了黑色和青色。
面部肌肉在下垂,結締組織在消融,一張臉像掛在骨頭上似的,仿佛皮肉正逐漸脫離顱骨。
他張開嘴,向袋子裡嘔吐,吐個沒完沒了。他的胃早就空了,但他還在不停吐出液體。
脹滿暈機袋的東西名叫“黑色嘔吐物”。這些東西並不完全是黑的,液體有兩種顏色:猶如瀝青的黑色顆粒,混在鮮紅色的動脈血裡。
這是內出血,嘔吐物的氣味彌漫在機艙裡,讓人想起屠宰場。
黑色嘔吐物滿載病毒,感染性極強,並且高度致命,能嚇得軍方的生物危害專家魂不附體。
暈機袋裝滿了,莫內合上袋子,把袋邊卷了起來。口袋鼓鼓囊囊的,泡得發軟,隨時可能被撐破,他把口袋遞給了乘務員。
莫內整個人顯得硬邦邦的,像是動一動就會扯斷體內的什麽東西。他的血液正在凝結,血流載著血液凝塊,淤積在身體各處。
肝髒、腎髒、肺部、雙手、雙腳、大腦裡全塞滿了凝固的血塊。簡而言之,他的整個身體都在中風。
凝塊在腸平滑肌內堆積,切斷了腸子的供血。腸平滑肌逐漸壞死,腸子開始變黑。他不再能完全感覺到疼痛了,因為在大腦內堆積的血液凝塊正在阻斷血流。
腦損傷抹除了他的人格——這是所謂的“人格解體”。生命活力和性格特質正漸漸消失,他慢慢變成了機器人。
大腦裡的小塊組織正在液化,意識的高級功能先喪失了,只剩下腦乾深處的區域還在工作。
不妨這麽說:夏爾·莫內的靈魂已經死了,只有他的肉身依然活著。
嘔吐發作似乎掙破了鼻腔血管,他開始流鼻血。
沒有凝塊的鮮紅色動脈血淌出兩側鼻孔,滴在牙齒和下巴上。血怎麽都止不住,因為凝血因子已經耗盡。
乘務員遞給他一把紙巾,他抓過來堵住鼻孔,但血液無法凝結,紙巾很快被泡透了。
溶化的內髒
坐飛機的時候,鄰座若是突然發病,通常情況下,我們不會招呼別人來看,免得害他難堪。只會在心裡叨鼓,過會兒就好了,他只是不習慣坐飛機,暈機了而已。再說飛機上經常有人流鼻血, 空氣乾又稀薄……
鄰座的人壓低聲音問他要不要幫忙。他嘟囔了幾個聽不懂的字眼,鄰座決定視而不見。
乘務員也問了他要不要幫忙,但感染了這類致命病毒,患者的行為會出現變化,他們無法對好意做出合理的反應。他們變得充滿敵意,不願意被人觸碰。
他們似乎沒法好好說話。他們報得出自己的姓名,但說不出今天是星期幾,也無法說清自己究竟怎麽了。
螺旋槳飛機穿過雲層,順著大裂谷翱翔,莫內癱坐在座位裡,似乎在打瞌睡……
有乘客懷疑,他是不是死了。
突然,紅色的眼睛睜開了,眼珠稍微轉了轉。他沒死。
時間到了傍晚,太陽落在大裂谷以西的山嶺背後,向四面八方投射光束,仿佛太陽在赤道上撞得粉碎。
飛機緩緩轉彎,朝著裂谷東側的峭壁飛去。地勢越來越高,顏色從棕色回到綠色。恩貢山出現在右側機翼下,飛機開始降落,掠過能看見斑馬和長頸鹿的稀樹草原。
一分鐘後,飛機在喬莫·肯雅塔國際機場降落。

莫內動了動,他還能走路。
他站起身,幾滴血滴下來。
襯衫上染滿血漬,他走下舷梯,踏上停機坪。
他沒帶行李,如果有行李的話,也是他體內無數增殖後的危險病毒。
莫內已經變成了人體病毒炸彈。
他慢慢走出航站樓,穿過建築物,來到計程車聚集的彎道上。
計程車司機圍過去——“要車嗎?要車嗎?”
“內羅畢……醫院。”他喃喃道。司機攙扶他上了車。
內羅畢的計程車司機喜歡和顧客攀談,這位司機問他是不是不舒服。答案顯而易見。
莫內覺得自己的胃沉甸甸的,感覺又麻又脹,仿佛剛吃了一頓大餐。
計程車開上烏呼魯高速公路,駛向內羅畢城區。穿過點綴著刺槐樹的草原,經過廠房,開過環形交叉路,進人內羅畢熙熙攘攘的街道。
女人走在土路上,男人在閑逛,小孩在騎自行車,路邊有個男人在修鞋,一輛拖拉機載著一車木炭。
計程車左轉上了恩貢路,經過一片市區公園,爬上一段斜坡,駛過成排的藍桉樹,拐進一條窄路,開進有崗亭的大門,內羅畢醫院終於到了。
車停進賣花小鋪旁的計程車停車位,玻璃門上有個“門診部”的標記。
莫內拿出錢給司機,下車,打開玻璃門,他走向接診台,打著手勢表示自己病得厲害。他說話已經很困難了。
他在流血,但必須等醫生騰出手來,於是他走進候診室坐下。
候診室是個小房間,擺著帶軟墊的長椅。
清澈、強烈而古老的東非光線穿透一排窗戶,落在堆放著髒兮兮的雜誌的桌子上,將方形亮斑投在灰色地面上,地上鋪著石子,正中央是個排水口。
房間隱約有煙熏味和汗味,坐滿了眼神呆滯的患者,非洲人和歐洲人肩並肩坐著。
門診部常有割傷等待縫針的人。他們很耐心,用毛巾捂著頭皮,用繃帶纏著手指,你能看見布料底下透出的血色。
就這樣,夏爾·莫內坐在門診部的長椅上,他看起來和候診室裡其他病人沒什麽區別,除了一張毫無表情的青紫色面孔和一雙紅眼睛。
牆上的告示提醒患者當心小偷,還有一張告示寫著:請保持安靜,感謝您的配合。請注意,這裡是門診部,急救病人優先處理,遇到這種情況,您需要耐心等候通知
莫內很安靜,等待著通知。
突然,他進入了最終階段:人體病毒炸彈爆炸了。
軍方生物危害專家對這種情況有個說法,他們說患者“崩潰並流血至死”,稍有禮貌些的說法是患者,“倒下了”。
他感到眩暈,極度虛弱,他的脊梁塌下來,松弛無力,他失去了所有平衡感。房間不停旋轉,他進入休克狀態。
他俯下身,頭部擱在膝蓋上,隨著一聲痙攣般的呻吟,胃裡湧出巨量血液,潑灑在地上。
他失去知覺,向前倒在地上。
房間裡只聽得見他喉嚨裡的哽咽聲,他已經昏迷,但還在繼續嘔出血液和黑色物質。
這時響起了床單撕裂的聲音,那是大腸完全打開,血液在從肛門向外噴射。
血液裡混著腸壁組織,他排泄出自己的內髒,腸壁組織脫落了,隨大量鮮血一同被排出體外。
莫內已經崩潰,血液趨於流盡。
候診室的其他病人慌忙起身,避開地上的男人,大聲呼叫醫生。
他周圍的血泊迅速擴張。
致命病毒摧毀了宿主,此刻忙著鑽出他身體的每一個孔穴,正“試圖”找到新的主人。
無人生還
1980年1月15日。
護士和護工推著病床跑過來,將莫內抬上床,推進內羅畢醫院的重症監護病房。
廣播裡響起召喚醫生的通知:ICU有一名患者流血不止。
一位名叫謝姆·穆索凱的年輕醫生趕到現場。他是醫院裡公認最優秀的內科醫生,熱情、幽默、精力充沛,經常連續工作許多個小時,對急診有很好的直覺。
他看見莫內躺在病床上,不清楚這個人出了什麽事,只知道患者在大出血。
患者呼吸困難——隨即停頓,那是血液被吸入肺部引發的呼吸驟停。沒時間研究出血的原因了。
穆索凱醫生摸了摸他的脈搏:心跳微弱。
護士跑去取來喉鏡,那是一根導管,可用於疏通患者的氣管。
穆索凱醫生扯開莫內的襯衫,觀察胸部的起伏情況,他站在病床頂端,俯身對著莫內的面部,上下顛倒地直視著莫內的雙眼。
莫內通紅的眼睛望著穆索凱醫生,但眼球一動不動,瞳孔已經放大。
這是腦損傷的征兆,意識在消失。
莫內的鼻部和口腔都沾滿血液。穆索凱將莫內的頭部向後抬起,打開氣管開口,以便插人喉鏡。
他沒來得及戴橡膠手套,用手指在莫內的舌頭四周掃了一圈,清理死細胞、粘液和血液。滑溜溜的黑色凝血沾上了他的雙手。
莫內散發出嘔吐物和血汙的氣味,但這對穆索凱來說並不稀奇,他集中精神繼續工作。
他低下頭,面部離莫內的面部只有幾厘米,他望進莫內的口腔,以確定喉鏡的位置。
喉鏡滑過莫內的舌頭,他推開舌頭,望向氣管深處,這個黑窟窿通向肺部。他將喉鏡插進洞口,湊近目鏡查看。
莫內突然一抖,身體抬了起來。
他再次嘔吐,黑色嘔吐物湧過喉鏡,從莫內的嘴裡噴了出來。黑色與紅色的液體濺到半空中,落在穆索凱的身上。
液體灑在白色製服和他的胸口上,留下幾道夾雜著黑色斑塊的紅色粘液。還鑽進他的眼睛,落進他的嘴裡。
穆索凱擺正莫內的頭部,用手指清理他口腔內的血汙。那些東西沾滿了他的雙手、手腕和前臂。
血汙到處都是:病床上、他的身上、地上。重症監護病房的護士不敢相信她們的眼睛。
穆索凱醫生順著氣管朝下看,將喉鏡向肺部插得更深,他見到氣管裡也在出血。
空氣嘶嘶地進人莫內的肺部,他終於又能呼吸了。
看起來,莫內由於失血陷入了休克。他失去的血液太多,甚至開始脫水。
血液從身體的每一處孔竅向外噴湧。體內剩下的血液不足以維持循環,因此心跳才那麽虛弱,血壓也快降到了零。他需要輸血。
護士取來一袋全血。穆索凱醫生將血袋掛在點滴架上,拿起針頭插進莫內的手臂。
他的血管似乎有問題,血液在針頭周圍湧了出來。穆索凱再次嘗試,將針頭插進莫內手臂另一個位置的血管。
失敗。依然血如泉湧。無論他把針頭扎進患者手臂的什麽地方,血管都會像煮熟的通心粉那樣破裂,湧出血液。
血液從患者手臂上的針孔向外冒,無法凝結。他的血液顯然有問題,穆索凱害怕莫內會因為手臂上的針孔冒血而失血死亡,最後放棄了輸血的念頭。
莫內的內髒還在出血,而且黑得像瀝青。
莫內陷入更深的昏迷,再也沒有恢復知覺。
第二天凌晨,他在重症監護病房死去。穆索凱醫生始終陪在病床邊。
誰也不清楚是什麽殺死了他,死因不明。

榮獲2011最佳科學攝影資訊圖形類鼓勵獎的埃博拉病毒插圖,圖片來自《國家地理》
醫生解剖遺體,發現腎髒已經損壞,肝髒也一樣,是黃色的,有些地方甚至液化了——就像死屍的肝髒,仿佛莫內還沒死就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黏膜腐脫,也就是腸壁組織脫落,同樣常見於陳放幾天后的屍體。
死因究竟是什麽?說不清楚,因為可能性實在太多,患者體內的一切都不對勁,說是“一切”一點不誇張,因為其中任何一項都足以致命:血液凝塊、大量內出血、肝髒變成糊狀物、腸子灌滿血液……
沒有詞匯、分類法甚至語言可以形容他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醫生最後稱之為“爆發性肝功能衰竭”。
他的遺體被裝進防水袋——根據一名當事人的描述,就在當地落葬。
多年後,我拜訪內羅畢的時候,沒有人記得莫內的墳墓在哪裡。
鮮血泡到了胳膊肘
1980年1月24日。
莫內的嘔吐物濺人了謝姆·穆索凱醫生的眼睛和口腔,九天后,他的背部漸漸感到酸痛。
他之前可不太會背痛,但他畢竟快三十歲了,覺得自己也快到腰背損傷的年紀。
過去幾周他非常辛苦:先是徹夜陪伴一位心髒有問題的患者,第二天又陪著一個內陸來的大出血病人熬了一宿,因此他一連幾天沒睡覺。
他沒把嘔吐物的事情放在心上,疼痛漸漸向全身蔓延,但他依然未曾多想。緊接著,他照鏡子的時候,發現眼球變紅了。
眼球變紅,他懷疑自己染上了瘧疾。隨後又開始發燒,他察覺到肯定是感染了什麽東西。
背痛持續蔓延,全身肌肉都痛得厲害。他服用抗瘧疾的藥物,但毫無用處,於是他請護士給他注射抗瘧藥劑。
護士在他手臂上做肌肉注射,針刺的疼痛異常劇烈。區區一針,讓他感覺到了可怕的疼痛,這種情況很反常,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開始琢磨,為什麽一次普通的注射就能帶來那種級別的劇痛。
接下來,他的腹部開始疼痛,他懷疑自己感染了傷寒,於是吃了一個療程的抗生素,但病情沒有緩解。
另一方面,患者需要他,所以他還是在醫院裡奔忙。
胃部和肌肉的疼痛越來越難以忍受,他開始出現黃疸。
劇痛使得他無法自我診治,工作也只能暫時放下了。
他去找內羅畢醫院的內科醫生安托妮亞·巴格肖。她為他做完檢查,確認了發燒、紅眼睛、黃疸和腹痛,但得不出明確的結論,隻懷疑他患上了膽結石或肝膿腫。
膽結石急性發作或肝膿腫都可能導致發燒、黃疸和腹痛(但無法解釋眼球發紅)。醫生給他的肝髒做了超聲波檢查,從成像上能看出肝髒有些腫大,但除此之外也沒有什麽異常。
這時的穆索凱已經病得很嚴重了,醫生將他安置進私人病房,護士二十四小時輪流照看他。他的臉變得毫無表情。
膽結石急性發作有可能致命,巴格肖醫生建議給穆索凱醫生做探查手術。由伊姆雷·洛夫勒醫生帶隊的外科醫生小組在內羅畢醫院的主手術室打開了他的身體。
切口位於肝髒上方,醫生拉開腹部肌肉,在穆索凱體內見到的怪異景象令人震驚,誰也解釋不了:肝髒腫脹發紅,呈現出病態,但醫生找不到膽結石的症兆。另一方面,他流血不止。
外科手術肯定會切斷血管,被切斷的血管會出血一段時間,隨即凝結。要是出血不止,醫生會用明膠海綿止血。
穆索凱的血管不停出血,他的血液無法凝結,就像得了血友病。
醫生把明膠海綿敷在他的整個肝髒上,但血液繼續滲出,醫生不得不從切口吸掉大量血液,但清理乾淨之後,血液又會積滿切口。就像在積水線下挖洞,積水的速度和排水一樣快。
一名外科醫生後來告訴別人,手術團隊“被鮮血泡到了胳膊肘”。
他們從肝髒上切下一小塊用以活檢,將組織泡進固定液,以最快速度縫合了刀口。
手術後,穆索凱的病情迅速惡化,腎髒開始衰竭,他似乎就快死了。一位名叫戴維·希爾佛斯坦的醫生接管了他。
穆索凱有可能會腎衰竭,只能靠透析維持生命,這給醫院染上了非常時期的色彩:同事都很喜愛他,大家絕對不想失去這位夥伴。
希爾佛斯坦給他上了維持療法,他後來對我說:“我只能做到這麽多。我盡量給他輸入營養,體溫過高時幫他退燒。我是在束手無措的情況下照顧一個病人。”
他懷疑穆索凱醫生感染了某種罕見的病毒,於是采集了穆索凱的血樣,提取了血清。將幾試管冷凍血清提交給各大實驗室進行化驗,其中有南非桑德林漢姆的國家病毒學研究所,有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疾病控制中心。
他開始等待結果。
人命的黑板擦
凌晨兩點,希爾佛斯坦家裡的電話響了。
打電話的是一名駐扎肯亞的美國研究人員,說南非方面在穆索凱的血樣裡發現了非常可怕的東西。
“血樣對馬爾堡病毒呈陽性,情況很嚴重。我們對馬爾堡病毒沒什麽了解。”
希爾佛斯坦根本沒聽說過馬爾堡病毒,放下電話,他睡不著了。
像是醒著做夢一樣,他一直在琢磨馬爾堡病毒是什麽。他躺在床上,想著朋友和同事穆索凱醫生,害怕這種病原體已經在醫護人員中擴散了。
“我們對馬爾堡病毒沒什麽了解,”這句話始終回蕩在他的耳邊,他再無一丁點兒睡意,索性起來穿衣服,開車趕往醫院,天沒亮就衝進了辦公室。
他翻出一本教科書,開始查找馬爾堡病毒的相關資訊。條目很簡略,馬爾堡病毒來自非洲,卻有個德國名字,是根據第一次發現的地點命名的。
1967年,病毒在一家名叫“貝林製藥”的工廠爆發,他們使用非洲綠猴的腎髒細胞生產疫苗,定期從烏乾達進口猴子。
病毒潛伏在前後空運來的五六百隻猴子的體內來到德國,其中只有兩三隻攜帶病毒,但多半根本看不出病症。
它們來到貝林製藥後不久,病毒開始在猴群中蔓延,其中有幾隻“崩潰並流血至死”。
很快,馬爾堡病毒跨越物種傳播,突然在城區人口中顯形。

已知第一個感染馬爾堡病毒的人類名叫克勞斯·F,他是貝林製藥負責餵養猴子和清洗鐵籠的工作人員。
1967年8月8日,他表現出症狀,兩周後死去。
被馬爾堡病毒感染的患者會像遭受了核輻射,幾乎所有組織都會受到損傷。它對內髒器官、結締組織、腸道和皮膚的攻擊尤其凶猛。
在德國,所有僥幸逃學生者都失去了頭髮:他們變成禿頭或斑禿。毛囊組織壞死,頭髮大把脫落,就好像遭受了輻射傷害。
身體的所有孔竅都在出血。我見過死於馬爾堡病毒的患者照片,拍攝於這名患者過世前幾小時,患者躺在床上,上半身沒穿衣服,臉上毫無表情,胸部、雙臂和面部布滿紅疹和瘀斑,乳頭淌血。
在康復期間,存活者的皮膚會從面部、雙手、雙腳和生殖器上脫落。有些男人遭遇了睾丸腫脹、發炎和部分腐爛。
睾丸感染最嚴重的病例出現在一名停屍房的工作人員身上,他負責處理感染者的屍體。病毒會在部分患者的眼球液體裡存活許多個月,他從屍體身上感染了病毒。
誰也不清楚馬爾堡病毒為何鍾情於睾丸和眼球,一名男子曾因為性交將病毒傳給了妻子。
醫生還注意到馬爾堡病毒對大腦的獨特作用。大多數患者顯得很陰鬱,行為略帶攻擊性或抗拒性。
一名患者精神錯亂,顯然是腦損傷的後果。另一位患者沒有任何精神失常的症兆,他的高燒退去,病情似乎漸漸穩定,但突然間,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血壓急劇下降——身體很快垮了,他隨即死去。
醫生解剖屍體,打開顱骨後發現腦部中央出現了嚴重的內出血。他的“大出血”流進了大腦。
1970年在馬爾堡大學召開過關於這種病毒的研討會,事後論文被匯集出版。除了這本書,人類對馬爾堡病毒沒什麽了解。
書裡記載了病毒傳入的大致經過:1967年8月13日,猴群管理員海因裡希度假歸來,14日到23日上班宰殺猴子。他最初的感染症狀出現在8月21日。8月28日,實驗室助理雷娜塔·L打破了一支等待消毒的試管,試管裝有被感染的組織。1967年9月4日,她病倒了。
患者在暴露於病毒之下的七天左右開始頭痛,然後病情迅速惡化,高燒、凝血、噴吐鮮血和臨終休克。
短短幾天內,馬爾堡市的醫生以為世界末日降臨了。
最後統計,病毒的感染者共有三十一人,其中七人死在血泊中。

馬爾堡病毒的致死率約為四分之一,因此屬於極度致命的病原體,哪怕在最現代化的醫院裡,患者連上生命支持機器,馬爾堡病毒也能殺死四分之一的被感染者。
而這一“絲狀病毒”家族中最為凶悍的扎伊爾埃博拉病毒,致死率達到了驚人的十分之九,一百名感染者有九十名難逃一死。
扎伊爾埃博拉病毒就像是人命的黑板擦。
要人命的猴子
國際衛生機構迫切希望找到猴子的確切來源,以便搞清楚馬爾堡病毒在自然界的活動地點。
病毒在德國爆發後不久,一組調查人員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讚助下飛往烏乾達,尋找那些猴子的來源地。
結果發現猴子被捕獲的地點遍布整個烏乾達中部地區,調查組無法找到病毒的確切源頭。
這個謎團許多年沒有得到解答,直到1982年,一名英國獸醫主動報告了馬爾堡病猴的新目擊證據。
這位獸醫名叫瓊斯。1967年夏,病毒在德國爆發時,瓊斯先生在恩德培的一家出口機構打零工,專職的獸醫檢驗員外出休假,他暫時負責檢查出口的猴子,馬爾堡病猴就是在那裡來的。
這家公司的老闆是一名富有的猴類商人,每年向歐洲出口一萬三千隻左右的猴子。數量驚人,利潤更是可觀。
染病的那批猴子被送上夜班飛機來到倫敦,然後再飛往德國。
病毒首先在猴群中爆發,然後“企圖”在人類身上站穩腳跟。

打了許多次電話之後,我終於在英國的一個小鎮上找到瓊斯先生,他現在是一名獸醫顧問醫生。
他告訴我:“猴子在運輸之前只有一次肉眼檢查把關。”
“檢查人是誰?”我問。
“就是我。”他答道。
“我檢查猴子,看外觀是否正常。要運輸的動物裡,有時候會碰到一兩隻受傷或有皮膚病變的。”
他的處理手段是挑出看似有病的猴子,將剩下的送上飛機。
幾周之後,猴子在德國鬧出病毒爆發,瓊斯先生感覺很難過。
“我嚇壞了,因為簽署出口證明的是我,”他告訴我,“現在我覺得那些人都是我害死的!這種感覺是因為,我本可以做些什麽,但我當時怎麽可能知道呢?”
他說得沒錯,科學界當時還不知道這種病毒的存在,寥寥兩三隻外表看不出有病的動物卻引起了那樣一場災難。
接下來的故事更令人不安。
他以為那些被剔除的病猴都被宰殺了,但後來他得知實情並非如此。
公司老闆將病猴裝進籠子,送到維多利亞湖上的一座小島放生。所有的病猴都在那裡活動,小島變成了猴類病毒的聚集地,成了高危之島、瘟疫之島。
“然後,要是那家夥缺少猴子了,就會背著我去島上抓幾隻湊數,這些病猴就會被送往歐洲。”

瓊斯先生認為馬爾堡病毒已經在那座高危之島生了根,在那裡的猴群內傳播。而最後出現在德國的某些猴子就來自那個小島。
世界衛生組織的小組前來調查,“老闆命令我,只要不被問,就別說”。
事實上也沒人找過瓊斯先生詢問,他說他沒見過調查組的人。
調查組沒有找他這個猴子檢疫員談話,“對傳染病學是壞事,但對政治是好事”,他這麽告訴我。
假如事實證明,那名商人在疑似疫區的島嶼上,捕捉疑似染病的猴子送往歐洲,他的這門生意就黃了,而烏乾達也將失去一項寶貴的外匯來源。
馬爾堡病毒在德國爆發後不久,瓊斯先生記起一件事,這會兒他覺得這件事很重要——馬爾堡病毒很可能在離奇塔姆洞不遠的烏乾達農村地區肆虐已久。
1962年到1965年間,他駐扎在烏乾達東部埃爾貢山麓地區,檢查牛的疾病。
就在那段時間裡,當地部落的首領說火山北坡,希臘河沿岸有人染上一種怪病,這種病會導致出血、死亡和“怪異的皮疹”,而那片地區的猴子也因為同樣的疾病而死亡。
瓊斯先生沒去研究那些傳聞,他也不可能確定這種疾病的起因。只是,這不禁讓人聯想,在馬爾堡病毒於德國爆發的前幾年,埃爾貢山區很可能已經有過一次不為人知的病毒爆發。
瓊斯先生說,送往馬爾堡的部分猴子,捕獲自維多利亞湖上的瑟瑟群島。那島位於維多利亞湖西北部,地勢不高,覆蓋著森林,從恩德培乘船很容易去。
他不記得高危之島的具體名稱了,隻記得它離恩德培很近。而瓊斯先生當時的老闆與瑟瑟群島的村民達成交易,從他們手上購買猴子。
村民將猴子視為害獸,樂於擺脫它們,又能換錢,再好不過了。
商人就這麽從瑟瑟群島得到野生猴子,假如發現猴子生病,他就到恩德培附近的另一個小島放生。
最後某些來自瘟疫之島的猴子很可能去了歐洲。
馬爾堡病毒爆發的始末,讓我想起照進黑暗洞窟的手電筒光束:我能看見熱帶病毒的源頭與蔓延這場大戲的一角,視野雖有限,但足以令人不安了。
危險的闖入者
戴維·希爾佛斯坦醫生在得知馬爾堡病毒對人類的危害後,說服肯亞衛生部門暫時關閉了內羅畢醫院。
整整一個星期,來看病的患者都吃了閉門羹,67個人在醫院內隔離檢查,其中大部分是醫護人員,包括給莫內做屍檢的醫生,照顧過莫內和穆索凱醫生的護士,為穆索凱做手術的外科醫生,處理過莫內和穆索凱的分泌物的所有護工與技師。
結果發現,醫護人員裡有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接觸過莫內、穆索凱或兩位患者的血樣與體液。
給穆索凱做手術的外科醫生記得分外清楚,他們“被鮮血泡到了胳膊肘”,在隔離檢疫的兩周內每個人都提心吊膽,唯恐馬爾堡病毒發作。
夏爾·莫內就像一顆人類病毒炸彈,他走進醫院的候診室,在那裡爆炸,導致整個醫院癱瘓。

謝姆·穆索凱醫生病倒後十天,看護的醫生注意到好轉的跡象。他不再無聲無息地躺在床上,而是表現出困惑和憤怒,並拒絕服用藥物。
一天,護士想幫他在床上翻身,他揮著拳頭叫道:“老子有棍子,小心我揍你。”
許多天之後,他的高燒終於退了,眼睛也變得透亮,意識和人格重新出現。
康復雖然很慢,但他從這種致命病毒的屠刀下僥幸逃學生,徹底好了。
目前他是內羅畢醫院的一名主任醫師,屬於戴維·希爾佛斯坦的團隊。
訪談他的時候,他說他對感染馬爾堡病毒的那幾周幾乎全無記憶。
“我隻記得一些片段,”他說,“我記得我嚴重意識混亂。在手術前,點滴瓶就掛在我身上。我記得護士一次又一次給我翻身。我不怎麽記得疼痛了,能說得上來的只有肌肉和腰背疼痛。我還記得莫內對我嘔吐。”
醫院裡也沒有其他人確診染上馬爾堡病毒。
在一種病毒試圖“闖人”人類群體之中時,先兆很可能是於不同的時間和地點發生的零星爆發,也就是所謂的“微爆發”。
內羅畢醫院的案例是孤立事件,是這種危險病毒的微爆發,它在人類中啟動致命爆發的能力尚不確定。
穆索凱醫生的血液被裝進試管,送往世界各地的實驗室,為生物庫增加馬爾堡病毒的活體樣本。
今天,馬爾堡病毒的這個毒株被稱為“穆索凱毒株”。其中有一部分被裝進玻璃容器,永遠保存於美國陸軍冷庫。
那裡稱得上是“高危微生物的動物園”。我敢肯定,你不會希望有病毒從裡面泄露。
▲
對埃博拉病毒源頭的調查最後不了了之,我卻一直在想那個猴子檢疫員的話。
隱瞞疫情“對傳染病學是壞事,但對政治是好事”。這樣的“好事”一點也不新鮮,說到底,就是錢的事。
病毒讓人恐慌,但相關人員和地區對疫情的冷處理更讓人心驚。
埃博拉能在看不見摸不著的情況下奪人性命,人類本性裡的自私和貪婪同樣可以殺人於無形。
仔細回顧埃博拉傳播爆發的過程,其中不乏一些先兆和足夠引起警惕並加以阻攔干涉的關鍵節點,只是結果令人失望,把守這些關卡的人無一例外,都松懈了。
猴子檢疫員僅憑肉眼檢測出口猴子的健康狀況;被剔除的病猴沒有被妥善處理而是草率地在附近島上放生,數量有缺口時還會被拿來充當商品;調查組沒有盡到調查職責;相關國家怕失去寶貴的外匯;落後山區肆虐多時的疫情無人問津;感染了病毒的莫內竟順利登上了飛機……
一個環節的失誤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結果,何況是這麽多。
我不敢想,在那些手電筒照不到的黑暗裡,又是怎樣一番景象?
誰該為這場慘烈的“血疫”負責?
1989年美陸軍傳染病研究中心相關負責人說過這樣的一段話:“如果我們當年,能夠早一些發現艾滋病毒,並且及時研究治療,將其控制在原發地,那麽我們將拯救多少人的生命呢?”
可隨後,他也說:“如果艾滋病當初很早就被發現並控制,那麽相關研究部門將會認為它只是偶發於非洲偏僻村落的一罕見病,又怎麽會投入資金進行深入研究呢?最終,它還是會隨著人類的活動而傳遍世界。”
那些“失守”的人們又是否能想明白:與人性有關的劫難,沒有一場是偶然的。
本文選自《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美)理查德·普雷斯頓著,姚向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03月版,有刪節。圖片來自網絡。
▼
往 期 故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