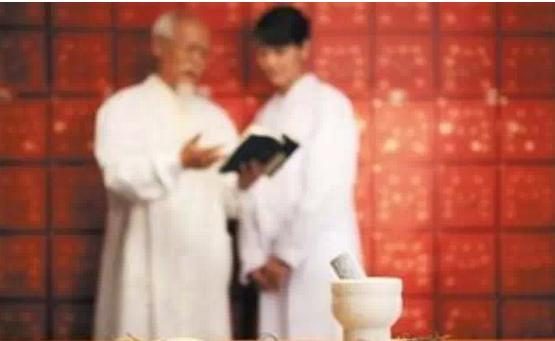導讀熊老十六歲開始行醫,從事中醫臨床五十餘年,中醫高等教育三十多年。對於中醫從什麼書入門學起,師承派和學院派各自優劣,老先生以樸實的語言講解,給予年輕醫生和中醫愛好者諸多啟示,也讓更多人思考如何在學院派的時代洪流中學習和傳承中醫。
★中醫從什麼書讀起
講講中醫從什麼書讀起,這個問題是值得探討的。有人曾採訪過我,問我是什麼派的。我說我既是學徒派,又是學院派。我為什麼這麼講呢?我是學徒派,誰都知道,現在有句笑話,叫「地球人都知道」,因為我講真話,從不隱諱我的出身,講假話我不會的。
問我是什麼文化水準,我說我就是學徒出身。十三歲當學徒,當到十六歲當醫生。當學徒的時候,什麼事我都乾過,給老師提尿壺,那是常事;打洗臉水、倒洗腳水,那也是常事;在藥鋪裡下梭板,打掃衛生,掃廁所,這些事我都搞。
這個學徒派讀書和我們現在科班派讀書有區別。
這就是我要講的核心,這個問題值得探討。我記得二十年前,我校的彭堅教授講過一句話,他說:「我們湖南中醫應該研究熊繼柏現象。」他說應該研究一下我的現象。他說你為什麼會講課,為什麼會看病,為什麼會寫書,他說我們值得研究一下這個現象。
確實是學徒出身,我倒不在乎什麼研究我的現象,也沒有誰研究過我的現象。但是我琢磨,因為我在農村公社衛生院工作了20多年,我對農村的情況特別了解,我在城市又當了30多年醫生,我對城市醫療也很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在高等學府教了30多年書,退休後幾乎跑遍全國,全國許多大的中醫院校我都去過,如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給全國的名醫班講課,所以我對上面的情況很了解,我對基層的情況很了解,像我這樣的人確實不多,所以我就琢磨中醫的教育問題,我在考慮這個問題。我不講規律,我就講講我是怎麼讀書的。
第一本書——《雷公炮炙四大藥性賦》,我四個早上把它背完,一個早晨背一個藥性,寒、熱、溫、平,就四個早上背完了,白天我就玩,沒事乾。
背完了接著就是《藥性歌括四百味》,當時背了,但現在我不一定還記得。四大藥性賦我還能背,要我寫我還能寫下來。《藥性歌括四百味》我就寫不下來了,連接不起來了。這就是第二本書。
第三本書——《醫學三字經》。要說明的是,我讀的書都是抄來的,不是原版的。第一,沒有書買;第二,買不起。都是抄師傅的,抄了有錯別字,師傅給你改正,改過來後再教一遍,讓你去讀,就這樣的。
《四大藥性賦》師傅沒講,《藥性歌括四百味》也沒講,《醫學三字經》講了,講得似懂非懂。「醫之始,本岐黃」,岐伯和黃帝,就這麼講,那時我哪知道岐伯、黃帝是誰啊?「靈樞作,素問詳」,靈樞是什麼,素問又是什麼,那時全不知道。「難經出,更洋洋」,「難經」是什麼不知道,現在知道了。那時《醫學三字經》全背。現在如果誰要我抄,我可以一個晚上給抄出來,不僅不要書本,而且絕對沒錯。這是第三本書。

第四本書是《脈訣》,包括《王叔和脈訣》和《瀕湖脈訣》兩本脈訣,這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診斷學。這是第四本書。
第五本書是《醫宗金鑒·四診心法要訣》,講的是診斷學。現在總結歸類就是中藥學、三字經、診斷學。
之後開始學方劑。首先是《局方》。《湯頭歌訣》讀完了,讀陳修園的《時方歌括》,這兩本書的方劑歌括我全能背,比如藿香正氣湯:「和解藿香正氣湯,蘇葉白芷共藿香,陳半茯苓大腹草,厚樸桔梗引棗薑。」這是《金鑒》的。「藿香正氣白芷蘇,甘桔陳苓術樸俱,夏曲腹皮加薑棗,感傷嵐障並能驅。」這是《時方歌括》的。這兩本方劑書我都能背。
讀完方劑後開始讀內科學的書。內科第一本書是陳修園的《時方妙用》。「中風……風者,主外來之邪風而言也。中者,如矢石之中於人也。」像這樣的話都要背,這就是接觸內科學。
接觸內科學以後,老師就開始跳躍式地教我了,這是我的第一個老師,胡岱峰老師,他是清朝秀才,古文功底好得不得了,他的古文真是學究式的。他說我能讀書,不能跟大家一起讀,要開小灶,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一個班。讓我開小灶就是學習《傷寒論》,讀的是《傷寒論新注》。開始是讀原文,老師的標準就是背。
背的同時也講,比如給我講豬膚湯,我問過一個問題,我問老師:豬膚是不是就是豬皮,老師回答說是,我說:「那是不是隨便哪裡的皮都可以?」「哎呀,你怎麼問這樣的問題呢?」老師說:「你怎麼問這樣的話,你問得出奇呀。」他感到奇怪。
又比如「五苓散,白飲和服」,我問「白飲」是什麼,老師說:「白飲就是米湯啊。」就問這些東西,都是當時讀書的靈感,所以永遠都記得。就這樣《傷寒論》我背下來了,背下來後就覺得這書讀得差不多了,這樣的書都能背下來,而且是搞不懂的書。我為什麼現在始終念念不忘我這個老師,就是因為我這個老師引我入正門。如果沒有這樣的老師,我對經典不可能讀得這麼好。

《傷寒論》讀完了,接著就是《金匱要略》,又是要求背。我一年內把這兩本書背完,半年背一本,其中《金匱要略》好背,就是《傷寒論》不好背,尤其是太陽篇,把人背得暈頭轉向。這兩本書讀完後,趕上1958年開始「大躍進」,我就當醫生去了。
我當時就讀了這麼多書開始去當醫生。那時剛開始當醫生看不好病,當然也可能偶爾看好一兩個,但總是不滿意。人家老醫生看了幾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為看得好啊。
我就問那個老醫生:「你怎麼看得好病,我怎麼就看不好呢?」我問他讀些什麼書,是不是書比我讀得多些。他問我都讀些什麼書,我說讀了《傷寒論》《金匱要略》,他說:「誰讀那樣的書啊,那書有什麼用,那書沒用。那書是講理論的,不是看病的。」我說:「你怎麼知道囉?」他說:"我們都不讀,你看我們哪個讀,一個都不讀。」
這就是說當地的醫生沒一個讀過《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但他們就能看得好病。於是我就問他讀些什麼書,他告訴我隻讀過《醫宗金鑒》,我又問他《醫宗金鑒》怎麼讀,他說就讀《雜病心法要訣》。好,我就找到《醫宗金鑒》,把它借來。我一看,《雜病心法要訣》基本出自《金匱》,但它在《金匱》方基礎上加了一些時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醫生又告訴我,《醫宗金鑒》裡面值錢的是它的婦科學和幼科學。我在讀《醫宗金鑒》時又發現一個問題,《傷寒心法要訣》把龐大複雜的《傷寒論》原文精化精簡了。於是我把《傷寒心法要訣》認真讀了,比內科《雜病心法要訣》讀得要熟得多。這樣,我就花力氣讀了《傷寒心法要訣》《婦科心法要訣》和《幼科心法要訣》。所以我的學生都知道,我經常用《傷寒》方、《金匱》方,用得很熟,婦科、兒科基本上用《醫宗金鑒》的方,這是自學的。
讀完了這些書我才真正開始當醫生。在農村當醫生,你要應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當你出名以後,比如我那時每天要看將近一百個病人。那時候很多怪病就開始遇到了,師傅不在身邊,我沒處去請教,農村那些老醫生我跟他們講《傷寒論》和《金匱》他們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決。
我看病沒人帶,都是自己闖出來的,所以我的經驗都是實踐中反覆摸爬滾打出來的。跟我上門診的這些學生得到我的經驗好像很容易,其實我是吃過大苦的,所以我現在用起來,學生們一下就學到了,好像非常簡單,其實我是經過幾十年磨鍊得來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斷地升華、總結出來的東西,它不光是書本上的東西。
對於一個方,我怎麼加,怎麼減,已經形成了一個規律。某個病一來,我立刻能想到用什麼方,這些經驗是我幾十年積累的東西。病人一來診察之後,我的方就出來了,為什麼這麼快呢?因為我搞了幾十年啊,我看了幾十萬人了。
在這個實踐過程中我又讀了一些書,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讀得很熟,《傅青主女科》裡面的方我經常用,當然是有選擇地用。治婦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醫宗金鑒·婦科心法要訣》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兒科病我基本上就用《醫宗金鑒·幼科心法要訣》的方。
曾經有一本幼科專著叫《幼科鐵鏡》,我讀過,我個人覺得不怎麼樣。還有一本書是陳自明的《婦人大全良方》,這本書過於複雜,把婦科複雜化了。
我經常說我們中醫學本來就夠複雜的了,我們現在有不少的中醫,甚至於號稱中醫學家,他把中醫學人為地複雜化。難道還嫌它複雜不夠嗎?把它人為地搞複雜了,我們的後人還怎麼來學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住後退縮,進一步退三步,他還怎麼學?這人為的複雜給後人帶來的弊病,只能給中醫學術帶來摧殘作用。
我的第一位老師教我通讀了《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師了,他是陳文和老師,日本東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他是在國內學中醫,然後到日本去深造。
陳老師發現我讀書讀得好,但有明顯的缺陷,第一,沒學過溫病學;第二,沒讀《內經》。溫病學和《內經》講些什麼東西,我確實都不知道。我後來見到我第一位老師胡老師時,我就問他為什麼不教我讀《內經》?他說:「你那麼小,讀什麼《內經》,那是你讀的啊?到時候你自然就可以讀。」我問他要到什麼時候?「當幾年醫生以後,到20多歲30歲時再讀吧」,這是胡老師跟我講的,他叫我到二三十歲再讀《內經》。

在陳老師那裡,他就教我讀《內經知要》,其實我原來真正的《內經》功底就是《內經知要》,溫病功底就是《溫病條辨》。《溫病條辨》拿到手以後,我的感覺就不一樣,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溫病條辨》上下了功夫。我對《溫病條辨》是讀得很熟的。我們學校的溫病教研室主任謝鳳英教授,她的溫病學水準是很不錯的,一次偶然的機會她發現了我對溫病也很熟,她說:「你怎麼對《溫病條辨》那麼熟啊?」我開玩笑說:「難道就只允許你一個人熟啊!」
現在我就可以告訴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來自哪些地方。開始不是講了兩本方劑學嗎,這是基礎,然後是《傷寒》方,《金匱》方,《醫宗金鑒》方,程鍾齡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後就是溫病方,就這麼多方,就來自這些地方。當然,以後還有一些雜家的方,比如張景嶽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還有《審視瑤函》的方,那是個別現象,包括《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的方,那都是個別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講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陳老師重點就讀了《溫病條辨》和《內經知要》,陳老師告訴我一個重要的道理:要想當一個好醫生,必須大量讀方劑。他有個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當時他要我抄下來,我那時因為記性好得很,全記得,就沒抄。那時又沒有複印機,否則的話就複印下來了,真可惜啊!
自從跟陳老師學了溫病學後,回去當醫生就大不一樣了。當時我們那裡乙腦、流腦流行,我治好幾個危重病例,在石門縣西北地區的醫名就打開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後,是因為治乙腦、流腦。
上面所談的就是學徒讀書。分析學徒讀書的特點是:
第一,讀的是原著,沒有水分,至少沒有現在的書這麼多水分。我不是讀的現在的書,我讀的是原著,這是第一。現在的教材裡面有很多是人為的錯誤,人為的複雜。
第二,我讀中醫書,並且讀得比較熟。恐怕大部分人雖然讀是讀過,但沒有讀得這麼深,讀得這麼熟,尤其是現在科班出身的,儘管對某一門很熟,比如講《金匱》的對《金匱》很熟,講《傷寒》的對《傷寒》熟,但是講《金匱》的不熟悉《傷寒》,講《傷寒》的不熟悉《金匱》,他還不一定做到了純熟,因為他沒有背書本,僅僅局限於教材的一點點,教材以外的不注意去讀。
當然全部中醫學徒都像我熊某人一樣讀書是不可能的。第一,不可能人人都有很好的記憶力,有很好的悟性;第二即使有這個記憶力,下不了這個決心,不能像我這樣不要命地去讀書,去搞臨床實踐。因為我有一個環境所迫,沒有飯吃,沒有衣服穿。
我學醫時吃什麼?吃蕃薯。我睡什麼?一床棉絮,既沒有被套,也沒有床單。那個時候都是兩個同學一起睡,一個出蓋被,一個出墊被,但是誰都不願意和我睡,為什麼呢?因為我一沒蓋的,二沒墊的,一床破棉絮,並且還有幾個洞,我就一床棉絮一裹,就是這麼睡覺,哪像現在的年青人生活這麼幸福。我當時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讀書。
後來當醫生的時候我連煤油燈都點不起,經常在月光下看書。所以我經常講,一個人要成功,要兩點,第一,要聰明;第二,要勤奮。用我們的土話講就是發狠,不要命地去幹。你說現在的聰明人多不多?像現在的碩士、博士,哪一個不聰明啊?但是你能下這個狠功夫嗎?這一點很難。
有人問我:「您到底讀了多少書啊?」我給大家交個底,其實並沒有讀很多書,只是我讀得比較熟,讀得比較細,理論功底比較紮實,臨床經驗比較老到,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一個中醫學徒學醫的特點。
在這裡我還要提到一點,過去我們的中醫老師有門戶之見,有派別。比如我的兩位老師,第一位老師是典型的溫熱派,他熟讀《傷寒論》和《金匱要略》,也很熟悉《內經》,但他不懂溫病;而我的第二位老師是清涼派,他恰恰注重溫病。因此,現在回頭反思他們的臨床功夫,我第二位老師治療常見病擅長,第一位老師治療怪病功夫厲害。我很幸運恰好得到了這兩位老師的指點,如果我隻跟了第一位老師而沒有跟第二位老師,那我的臨床水準肯定沒有現在高。這就是學徒的偏頗,所以我說學醫者的老師絕不能糊塗。

另外,我們古代老師帶徒較保守,但我不保守。我在課堂上或臨證帶學生什麼都講,如果學生用心就記住了,如果學生不用心或未入門就可能—晃而過,不能體會。跟我的學生都知道我從不保守,只要我有空,問我的問題我都答覆。
我記得初當醫生時,在我們山區遇到了一個病人,他的腦袋腫大,脖子也腫得和腦袋一般粗,又紅又腫,又癢又痛,又發燒。我當時只有十六七歲,有人請出診看病我很高興,看了這個病人之後很自信地判斷是「大頭瘟」,於是很有把握地開了個「普濟消毒飲」。哪曉得病人吃了三付葯,一點都沒好,於是我又給他改了個「防風通聖散」,心想這個病人又癢又痛又發燒,不是風火嗎?防風通聖散既消風又瀉火,應該會好。結果又沒好,我就傻眼了,頓時方寸大亂,跑了三十裡山路去找我的老師。
我老師當時八九十歲了,正在家裡抽一個大煙鬥,我進門後很恭敬地叫師傅,老師見了我就說:「你來了,是不是看病看不好啊?」我說:「是的。」於是把情況告訴了老師,然後問:「您看怎麼辦呢?」師傅慢條斯理地給了我三個字:「翻書去。」我這來回六十裡山路算是白跑了,但是「翻書去」這三個字有好處啊。
回去後我一通宵都在翻書,還要思考,這樣得來的知識比老師講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所以,我後來基本上不再去問老師了,因為問他也就是這三個字,不罵人就算不錯了。現在,有時候我也會跟我的學生開玩笑說:「翻書去。」當然,舊時的老師帶徒弟也是很嚴格的。有一次我治療一個寒實結胸證的病人,用「三物白散」,開了「巴豆霜」一錢,碾粉後沖服。
患者拿處方到醫院藥房去買葯,藥房撿葯的老先生有七八十歲,經驗非常豐富。他拿到處方後直接扣下了處方,送到我師傅那裡,然後打發病家把我叫到師傅那兒去。我知道是因為巴豆霜的緣故,到了師傅那裡,他明知故問說:「巴豆霜是你開的?」我說:「是的。」他說:「巴豆吃了會怎樣啊?」我說:「書上說,不利,進熱粥,利過不止,進冷粥。」他說:「要是吃了拉血怎麼辦?」我聽了就傻眼了,因為張仲景沒講吃了會拉血呀!
師傅就責問了我一句:「你有多大能耐?敢開巴豆霜?」我當時還壯著膽子辯白了一句:「師傅,我是看您經常開。」我很後悔說這個話。後來我再也沒有開過巴豆霜了。所以,我當醫生一輩子都很謹慎,沒有出過醫療事故,砒霜、斑蝥、馬錢子這些有毒的藥物我都不用,老師對徒弟嚴格是有好處的。
在我學葯的時候,有位七十多歲的姓鄭的老師讓我受益匪淺。我做學徒要一大早起床,把門打開,把衛生打掃得乾乾淨淨,晚上下班後要把葯屜一個個整理好、關緊,稱葯的秤、壓紙的木方、沖臼、研缽都要整整齊齊地放在固定的地方,碾槽要收拾乾淨豎起來。切葯的時候,老師規定切一種葯就嘗一種葯,切當歸就嘗當歸,切苦參就嘗苦參,切黃連就嘗黃連。當時我不理解,覺得味道太難忍受了。現在我理解了,這樣做才能知道哪個葯是什麼味道,什麼葯麻口,什麼葯封喉,現在有哪個醫生知道呢?而我卻知道。
因此,我非常感謝這位老師。但這位老師很保守,問他什麼也不講。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中醫從古代傳到現在,有多少好東西由於保守已經失傳了!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有話講不出來,再就是忘記了。
比如,有的東西你不問我,我就沒講,因為每天門診量這麼大,看完病人就精疲力盡了。由此我就聯想到葉天士為什麼寫書不多,他的書都是他講,學生記錄而成的,不是他不會寫,而是沒時間寫。
我現在深有體會,過去一天看一百號病人,沒時間也沒能力寫,現在有能力了但沒時間寫。這也是現在中醫界的一大緊要問題,真的要組織搶救、整理老中醫的經驗,要組織一些懂專業、有水準、有能力的人來整理和寫作。關於學徒方面我就講這麼多。
我已在中醫大學教學30多年,我認為學院派的優勢在於:
第一,學科系統全面,有系統的教材,如中醫基礎理論、診斷、中藥、方劑、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科,等等,分科很細,而我們學徒無所謂分科;
第二,管理規範,隻讀書,不像我們學徒要做各種雜事,包括打掃衛生、上山採藥,等等。
但學院派也存在幾個問題:
第一,不專,學專業不專,心思不專。因為現在的大學生要全面培養,要與世界接軌,做綜合性人才,這當然沒錯。但由此也產生了問題,比如很多學生都把大量精力傾注在學外語上,就不能集中精力學中醫,他們在專業上的深度和廣度就會受影響。
第二,脫離或者說缺乏臨床實踐。學中醫脫離臨床實踐是最大的問題,中醫必須進行臨床實踐。我記得上海中醫藥大學的老院長金壽山教授講過一句話:「脫離實踐講理論,那是空洞的理論,耍的是花腔,好看不頂用。」這話講到點子上了。有些人說理論頭頭是道,著作一本接一本,但連個感冒都看不好,這是什麼中醫呢?這就是學院派的兩大毛病,包括現在的碩士、博士,有的人務實、捨得下功夫,專業可以學得不錯;若稍微一飄,就只剩下外語好,其他都不好。
因此,我們很多高學歷的人缺的恰恰是專業水準,是臨床能力,這也是中醫人才問題的癥結所在。以上就是我關於學徒派與學院派的比較。
本文來源:經典網,由中醫思維+編輯整理

特
別
說
明
⊙版權聲明:文章源於網路,如侵權請聯繫我們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