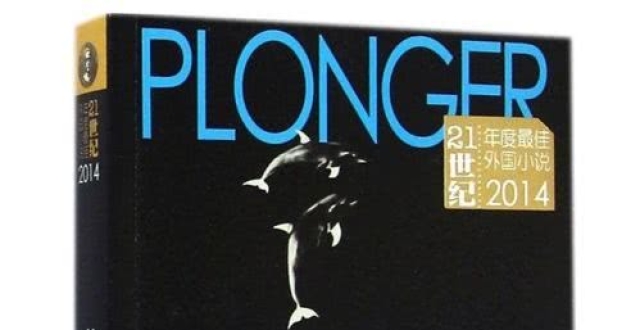穆濤
在陝西省作協主席賈平凹看來,穆濤的文章裡有他的觀念、有他的智慧,同時也有對具體問題的思考。魯迅文學獎給《先前的風氣》頒獎詞是:“穆濤的文字簡潔、機警,寬博而從容,溫和又不失銳見。在《先前的風氣》中,歷史的省思、世相的洞察與思想者話語風度熔於一爐,行文疏密相間,雅俗同賞,無論長文或短章,都交織著散文、隨筆和雜感的筆力與韻味,有鮮明的文體意識。他的寫作,繁複跌宕,儒雅豐贍,貫通著慈恕、善意的情懷。”
《先前的風氣》中有一輯專寫賈平凹。作為同事,穆濤把交往中的種種以詼諧筆墨出之,那些貌似尖刻的文字,畫出一個活生生的賈平凹。《先前的風氣》,由信史的溝與壑、身體裡的風氣、正信、舊磚與新牆、中國文化氣質等九部分組成。穆濤以清醒的現代意識和踏實的筆力,考查傳統典籍,反思當今生活,實現了散文創作的大境界。
有評論認為,“謙謙君子”與“稱物平施”是穆濤其人其文給人的基本印象,但他還有金聖歎的“情”和“俠”的一面,有“棉針泥刺法”“筆墨外,便有利刃直戳進來。”讀他的文章,若體味不出這一點,便是錯會了他。
中華讀書報:1993年去《美文》,是怎樣的一種機緣?
穆濤:細說有點長,我簡單說。1991年時,我在河北的《長城》雜誌做小說編輯。主編交給我一個任務,讓我去約賈平凹的稿子,最好是小說,散文也行。而且說的很嚴重,約到有獎勵。原因是1982年賈平凹在《長城》發表過一個小說《二月杏》,刊發後受到不少批評,之後再沒給《長城》寫過東西。去西安之前,我做了些功課,把兩三年間賈平凹發表的小說找來讀了,還讀了一些評論他的文章,把觀點也梳理了一下。到西安後,一位朋友帶我去的他家裡,他挺客氣,還說對《長城》有感情,批評的事與雜誌無關。但不提給稿子,說以後寫。我知道這是托辭,便把讀過的小說逐一說了我的看法。他聽得特認真。但直到我們告辭,也不明確表態。第二天晚上,我獨自又去了他家裡,開門見是我,還是那種客氣。我說,昨天忘了說幾個評論文章的觀點,今天來補上。我把幾個觀點陳述了一下,也說明了我的看法,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他一下子聊性大開,談了很多他的想法。聊的過程中,我看見牆角有個棋盤,就問,“您也下圍棋?”他說,“偶爾玩玩”。他建議下一盤,我說好呀。我本來是想輸給他的,趁著他贏,我抓緊要文章。下過十幾手之後,我就發現要輸的話,太難了。後來是他主動推開棋盤,“咱還是聊寫作的事吧”。接下來就融洽了,他鋪開宣紙,給我畫了兩幅畫,還寫了一幅書法。我拿著字和畫,說,“其實我就想要您的小說”。他笑著去裡邊的屋子,取出一個大信封,說,“你讀讀這個,咱先說好呀,這個小說是給別人的,我想聽聽你的意見。”我接過來一看,地址是《上海文學》,收信人是金宇澄。記得當天晚上西安下著小雪,我是一路走回我的住處的,四五裡的路程,心情那個爽朗。
這是個中篇小說,名字叫《佛關》,當天晚上我就看了大半,寫得真是好,充沛淋漓的。第二天一早,我先去複印,當時複印還貴,一張一塊多。再到郵局,把原件掛號寄回《長城》,忙完這些,回賓館再看小說。一個下午看完了,晚上我拿複印件再到他家裡,他翻看著厚厚的複印件,看我在稿子邊上寫的讀後記,說,“複印挺貴呢”。我說,“您的手稿我早上寄回《長城》了,打電話跟主編也匯報了,他說發頭條”。他聽過就笑,說,“你是個好編輯,我們西安市文聯正籌備辦一本散文雜誌,創刊時你來吧。”
《佛關》刊登在《長城》1992年第二期。1992年9月《美文》創刊,1993年3月,我到《美文》報到。後來見到金宇澄兄,為《佛關》這個小說向他致歉,他笑著說,“平凹跟我說過了,說被你打劫拿走的。”
中華讀書報:到了西安之後,您的創作和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穆濤:到《美文》後,我把個人寫作的事放下了,一心做編輯。在這之前,我是小說編輯,“轉業”編散文,一切都得學習。《美文》在創刊號上,開宗明義提出“大散文”主張,這個“大”字大在什麽地方,是需要認真研究的。平凹主編是從創作角度提出的這個主張,而作為雜誌如何呈現出來,是不能靠喊口號的。這個時期,《美文》有好幾位好編輯,宋叢敏、王大平、劉亞麗、安黎、陳長吟,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中華讀書報:《先前的風氣》獲“魯迅文學獎”,請具體談談這部作品。
穆濤:這本書獲“魯迅文學獎”後,西安市很重視,專門開過一次祝賀的會。在會上,我向平凹主編致歉,說,“平凹主編把我從河北調過來,是讓我做編輯,我卻得了這個創作的獎。讓我當裁縫,我卻織布去了。今後我要多努力,爭取退休前得個編輯獎。”
《先前的風氣》這本書,嚴格講,是一本讀書劄記。
我1993年到《美文》,1998年主持《美文》具體編刊工作。平凹主編倡導“大散文寫作”,這是《美文》的編輯宗旨。我是負責編刊的副主編,得先弄明白大散文的具體內涵。和平凹主編溝通幾次,逐漸摸到了他這種認識的底線。他認為,當代新文學以來,詩歌和小說,都有幾次思潮,在不斷的出新和突破,散文成了死角,而且越來越瑣碎。他具體用漢代的石雕、畫像磚舉例子,那種藝術手法上的大氣和生動,他還明確地告訴我,你去讀讀司馬遷吧。
我用心讀了《史記》和《漢書》,還有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劉向的《新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漢代的史學和文學著作,兼容著閱讀。通過這些閱讀,對司馬遷的了不起得出了兩點認識:一,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史書寫作方法的革命,包括“紀、傳、書”這種史學著作體例,對後世的文學影響巨大。二,《史記》之前的史書,重紀事,服務於朝廷。“《史記》在紀事的基礎上凸現思想的力量,在指向上是全社會的。用唐代史家劉知幾《史通》的話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顯隱必該(賅),洪纖靡失。”
《先前的風氣》收錄的文章,以我讀這些書的劄記為主。
還有一個細節需要說一下,總有讀者詢問《美文》刊名裡的“美”,以及“大散文”的“大”的具體涵義,我向平凹主編建議,用《孟子》的一句話作釋義,“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他答覆說,“挺好,咱這是和孟子想到一塊兒了”。
中華讀書報:《看畫》在讀者中影響大,可否談談創作起因?過程?有好玩的故事麽?
穆濤:《看畫》,是賈平凹的畫,以及我的添足文案。最初應《十月》雜誌之約,是顧建平兄的創意。後來就移植到《美文》上,做為一個固定欄目,有十幾年了。平凹主編有一次問我,“你寫了幾十篇看我的畫文章,關於我的畫,你怎麽一個字也不寫?你都看哪去了?”我說,“寫您的畫好吧,有人會說媚上。說不好吧,有人會說我抗上,還是不寫為好。”
平凹主編的畫,也是他的文學創作,我行我素,不拘不束,興致而來,興盡忘歸。有時突然而至的一個靈感,他會先畫出來,之後再慢慢寫成文字。最近這幾年,他開始研究技法了,一次他問,什麽最難畫?我說,畫雲。他鋪開一張紙,一團一團的揮毫,之後端詳了一會兒,在邊上題字:羊群走過。畫面上,是雲之下的羊群,還是羊群走過之後的雲團。出奇不意,似是而非。知非詩詩,未為奇奇。
我讀他的畫,是領略他的精神。“看畫”這個欄目,出版過一本書,叫《看左手》,意指他右手為文,左手為畫。
中華讀書報:能談談從事創作以來寫作風格發生的變化麽?
穆濤:讀漢代的史學著作過程中,我對《漢書》和班固越來越偏重,寫了幾十萬字的閱讀劄記,總題目叫《漢代告誡我們的》,也陸續發表了一些。作家出版社讓我寫《班固傳》,也答應了。但我先寫出的是一本《班固生平年表,以及東漢前期社會背景態勢》,從班固一歲,寫到六十一歲去世,班固的生平材料,和六十一年的社會大事記。我們中國人講六十年一輪回,這裡邊確實是藏著太多的東西。這個年表有十三萬字,我覺著,寫《班固傳》,這個功課不用心做好不行。
《漢書》這本史學著作,在史學界地位很高。東漢之後的著史方法,基本上遵循《漢書》的體例,一個朝代一本。《史記》是通史,從黃帝到漢武帝期間。《漢書》因習《史記》,但有自己的創新和發揚,其《地理志》和《藝文誌》開啟了後代幾個重要學科。唐代的劉知幾重視《漢書》,清代的全祖望簡直是著迷,寫過一本《漢書地理志稽疑》,從《地理志》中讀出百餘處疏誤,其實這裡邊有不少是年代變遷造成的。我讀完全祖望這本書,實實在在感觸到了清代學人考據派的硬功夫。
中華讀書報:評論家丁帆將“丁聰體”和“穆濤體”進行比較,認為有相同之處,您怎麽看?
穆濤:丁聰先生是我敬重的大家,他的文章如舍利子,一顆滄桑之心,經緯世態。丁帆先生是我的老師,他這麽說,是鼓勵我,但我真的承受不住。
中華讀書報:您在西安26年了,說說您對這座城市的感情?
穆濤:2018年,西安市給我頒發了一個極大的榮譽,叫“西安之星”,我從市委領導手裡接過證書,貌似平靜著走回座位,但晚上回到家裡,是掉了眼淚的。到西安快30年了,這是西安給我上了精神戶口,我融入這個城市了。如果我是一棵苗,是西安這塊厚土讓我破土的,如果我是一棵樹,是這塊厚土讓我長起來的。謝謝賈平凹,謝謝《美文》,謝謝西安!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舒晉瑜)
編輯丨莫非
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