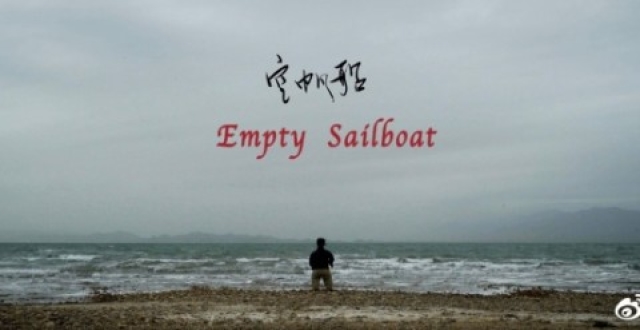最近,有一部叫《大三兒》的紀錄片在全國院線公映。
主人公大三兒姓葉,單字一個雲,1970年出生在內蒙古昭烏達盟。他的頭很大,身高只有1.1米,從這個角度來說,他是個“殘疾人”。為什麽要拍大三兒呢?導演佟晟嘉說,因為他想用影像保留住大三兒那個獨特的精神世界。最初,他只是打算拍大三兒的日常,拍他與老父親相依為命的生活,拍他的處世江湖,沒想到後來拍到了西藏。因為大三兒心裡一直有個想法,想去西藏,看看布達拉宮和珠穆朗瑪峰。
關於這部作品,讚揚者很多,批評者亦不在少數。
許多人對這部片子不滿意,認為這並不是真正的紀錄片:它卡在了二流公路片和電視台偽紀實片之間,設計痕跡明顯,導演乾預太多,配樂剪輯失當,大量的畫外音獨白產生了破壞效果,因此整部片子顯得有些平庸,糟蹋了好人物。而喜歡這部片子的人並沒有過多地去考究紀錄片的呈現形式與技術問題,而是更多地被大三兒其人所折服:
大三兒雖身有殘疾但內心強大,普通而又不普通,這使得這部“紀錄片”得以維持住了它的體溫。

大三兒經常使用的手勢,他稱其為“國際通用手勢”。圖為《大三兒》(2018)劇照。
誠然,大三兒是導演的“大三兒”,因此影片對人物的展現不免充滿了個人化的訴求與局限,但這並沒有遮蔽大三兒本身的光芒。從大三兒的身上,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很難得的品質,一種“有勁兒”的生活狀態,這與當下的“喪”文化是反向的。
如今,不僅90一代的青年人充滿了“喪”的集體焦慮,已步入中年的70後也滿是頹喪的疲態,大家活得都很沒有勁兒。原本無意呈現人物勵志意義的《大三兒》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勵志樣本。從這個角度去看《大三兒》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甚至於《大三兒》界於紀錄片與劇情片之間的矛盾樣態也為這種觀看提供了參考價值。
這不是一篇影評,是關於這部影片一個思考的面向。
撰文 | 風小楊
“我快要睡著了,可還得睜著眼”
我想從兩首歌談起。
第一首是尹吾的《你笑著流出了淚》。這是尹吾2000年的專輯《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場遠行》中的一首歌:
你笑著流出了淚尹吾-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次遠行
我快要睡著了/可還得睜著眼
你說呀說不停/我聽也聽不清
你說活著真沒勁/輕輕歎了口氣
又突然笑哈哈/你傻笑什麽呢
你說你沒情緒/把日子過下去
……
活著就是受罪/活著就是勞累/
活著就是互相折磨/活著就是不對
活著就是受罪/活著就是勞累/
活著還得互相安慰/活著就會憔悴
活著就是受罪/活著就是勞累/
活著就得拚命掙扎/活著就得乾脆
初聽起來,這首歌有些壓抑有些喪,但聽完整首後又有一種得到發泄的感覺,很痛快。所有關於活著的控訴最後隻歸結為一句話“活著就得拚命掙扎,活著就得乾脆”——絕望中的奮起。
彼時的尹吾和今日千千萬萬為理想打拚的青年們一樣,努力卻又麻木地活著,那時他說自己“就像一只在窗玻璃前百折不回的蒼蠅,放棄或者完成,都倍感力不從心。大多時候,只是順著生活的慣性一味的撲騰來撲騰去,然後眼睜睜的看著日子就這麽一天天的過去。”這與今日大行其道的“喪”文化不無相似——頹廢、絕望、悲觀,卻又艱難地反抗著絕望;對生活提不起勁兒,卻又不甘心放手。隻不過,如今的“廢柴”青年們學會了自嘲與自愈,學會了“葛優躺”,學會了“佛系”,而曾經的“頹廢”青年們也已經步入真正的中年,被迫學會隱藏起鋒芒,有的絕地反擊,有的混起了日子。
第二首是樸樹的《就這樣走了》,也是《大三兒》的片尾曲。神奇的是,這首歌所唱的,似乎與尹吾的那首歌有著某種精神呼應:
就這樣走著/像樣兒地活著/別怕去哪兒都沒有地兒
就這樣走著/像樣兒地活著/別怕到哪兒都慌了神兒
就這樣走著/像樣兒地活著/別怕自己都沒有勁兒
就這樣走著/像樣兒地活著/別怕自己都沒有魂兒
與《你笑著流出了淚》相比,《就這樣走了》有一種令人寬慰的力量。同樣是面對怎樣活得有勁兒的問題,中間卻橫亙著將近20年的時間變化,從前的呐喊變成了如今的告慰,從前的激烈少年變成了如今平靜的中年人。
其實,“喪”並不是90後、80後青年的獨有狀態,它始終存在著。如今的90後更多地受困於打破固化階級壁壘的絕望,買房難、租房也難,工作難、生活更難,“喪”是無目的無動力的集體焦慮使然。而70後作為真正的中年,生存階層已經固定,再也沒有了向上流動的可能,對於仍未掙脫原有階層、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些人來說,“喪”是一種真切的現實,他們的生存處境更為無力也更為脆弱,一場大病一次意外就有可能打破最後的平衡。如果生活的激情沒有了,危機也就來了。因此,怎樣才能活得不喪、有勁兒,直接決定了人們的生存品質。
何謂活得有勁兒,這是“何謂美好生活”的一個提問變體。當然,“活得有勁兒”並不意味著“活得幸福”,這只是一個心理前提,它首先保證的是,我們不是一具活著的行屍走肉。70年代出生的大三兒由此成為一個積極的形象,為正處於中年焦慮和喪文化危機的人們注入了某種力量。

大三兒坐在一片滿地鵝卵石的河灘上,看著珠峰上的太陽一點一點地落山。
“我不是寂寞的人,我有著一顆戰鬥的心”
關於《大三兒》這部紀錄片,很多人表示拍得不夠好,但這並不能埋沒大三兒這個人物的光輝。表面上看來,大三兒不過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努力生活的人,但與大三兒一起長大的佟晟嘉覺得大三兒不一般,而敏銳的樸樹一眼就抓住了大三兒的魂兒,或者說關鍵詞。大三兒固然有他的局限所在,但他更有高於他人的地方。這份高度在於,他活得有勁兒,或者說,他努力活得有勁兒。
在影片裡,我們看到的是重複、平淡、甚至略有些乏味的日常,是內蒙古赤峰小城的一個普通人物的生活,以及他周圍的人物樣態。
隻不過這個普通的大三兒比起其他人又不那麽“普通”,先天性的殘疾使他無法擁有正常人的身高與體能,本為家庭主心骨的兩位哥哥也都先後遭遇車禍離世,後來母親也早早離開,只剩了他與父親。因此常常地,大三兒成為人們眼中的“奇觀”,持續地被關注、被死皮賴臉地圍觀。大三兒笑稱這是“中國特色”,對此他感到難受,但也沒有辦法。但除了身為侏儒,大三兒其實和其他人並沒有什麽不同,都在拚命地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渴望友情,渴望愛情。

大三兒與他的父親正在看電視裡播報的新聞。
印象很深的一段是他談及理想愛情時的那份理想主義:
“她會用感情溫暖著我,我也會用我的感情去溫暖她。哪怕日子過得比較清淡,我也能跟她一起攜手看夕陽。”
大三兒說他比較完美主義,也有自己的主見,自己已經是殘疾了,不想妻子也是殘疾,這樣兩人都累,但健全的人又是無法和他走到一起的。看透了這一點,大三兒也就對愛情不強求了,一直沒有聽人的介紹結婚。“我的期望值太高,我期望的不可能得到,所以我也不太去費那個勁兒了。”
另外印象很深的是大三兒與阿皮、朱朱等人的兄弟情義。在這部片子中,人情大於故事,所出現的人物和大三兒的關係,都是建立在“情”字之上。在這方面,大三兒說自己“有點老思想”,“我是20世紀70年代的人。看的文學就是《水滸傳》《隋唐演義》這些小說。裡面寫的全是英雄、朋友、哥們。”大三兒對人情的那份執著、對友情的那份珍視,很大一部分都是從這些武俠小說裡化來。看到美景,他想到的是拍給朱朱看,當他來到珠峰時,最先想到的也是為朋友朱朱寄明信片。對大三兒來說,“情”字沒有了,活著就沒有滋味了。
或許在影片中,大三兒為我們呈現的是他一生中最有勁兒的狀態,但他畢竟還是個凡人,並不是一直像片子裡那樣,自始至終鉚著一股勁兒。
由於導演的取捨與剪輯,大三兒只是導演想為我們呈現的“大三兒”。他的軟弱,他的局限,他的種種情緒,我們並不能看見。
其實在拍這個片子之前,有那麽三四年的時間,大三兒的狀態是很差的,每天不和人溝通,自己活自己的。有時候導演佟晟嘉打電話問怎樣了,他就經常說“活著真沒意思”。

編: 胡赳赳 版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在紀錄片的同名書籍《大三兒》中,有一些關於大三兒的形象補遺。
大三兒並不晦言自己的局限,有時也會自嘲。有時候,他感覺自己越來越變得跟刺蝟似的,蜷著了,滿身都是刺。
“我挺貪心的,沒發現嗎?我老是想追求別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就好像別人的經濟、別人的交際、別人的愛情,這些東西我也都想得到。”“我沒啥愁心事,愁啥愁,都這德行了還有啥可愁的。現在想太遠了也沒啥用,我都已經嘗試過,我或者是沒有別人說的勇敢攀高峰那種精神吧,我是遇到挫折就掉頭那夥的,啥玩意兒都去撞一下,撞了之後找到自身的缺點或者不足。我看這個不適合我,就轉身走了,就不再去試,它再有啥好我也不去試。”
他也會迷茫,很多時候這種感覺是由重複的生活帶來的。他每天五點鍾下班,下班就在自家樓下彩票站買同一個號碼,買煙就買兩盒白紅塔山,然後回家和父親吃飯,電視永遠是那幾個台。每一天,大三兒都如此度過,所以他經常問導演:“有價值嗎?”對於自己的價值,他也會調侃:“我——我有啥價值,只是這個世界的一個誤會和累贅。”但大三兒也能很快從這種情緒中走出來,認識到重複的價值。“每天重複這種保潔工作。有了這份工作,才有了生活的保障,才有你想去想別的東西、追求更好生活的保障。”
雖然有自己無法跨越的身體局限,也有所有人都會有的精神局限,但大三兒似乎總是能突破自己的局限,活得勁兒勁兒的。當他對人說“我不是寂寞的人,我有著一顆戰鬥的心”的時候,突然感覺,大三兒其實和加繆筆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形象挺像的。

西西弗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觸犯了眾神,諸神為了懲罰他,便要求他把一塊巨石推上山頂,而由於巨石太重,每次未上山頂就又滾下山去,前功盡棄。西西弗斯不斷重複、永無止境地做,生命就在這樣一件無效又無望的勞作當中慢慢消耗殆盡。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法)阿爾貝·加繆(譯者: 丁世中 / 沈世明 / 呂永真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7年1月“在荒誕中奮起反抗。”)
“大三兒”的發現與生成
其實,比起大三兒這個人物的存在,我更在意“發現”大三兒、“塑造”大三兒的人們,以及此類作品產生的背景。將鏡頭對準小人物的電影和紀錄片也不少,比如去年的《大佛普拉斯》,比如1990年的《本命年》,這些影片各有其獨特的精神價值與反思力量,而且不可避免地都帶著一種時代和社會裹挾的“喪”的氣質,更容易引起當下人的共鳴。

電影《大佛普拉斯》(2017)劇照。
發現和塑造“菜埔”和“肚財”的黃信堯試圖剖析社會的無情,發現和塑造“泉子”的謝飛試圖解讀時代的苦悶,而發現和塑造“大三兒”的佟晟嘉呢?他對於“大三兒”這一形象的追蹤與執著或許無意中揭開了當下普遍的“精神症候”:
當未來變得不再可期,當生活變成了日複一日的機械重複,人們開始失去目的、失去動力,滑向頹廢的灰暗狀態,“喪”不僅攻佔了青年的精神陣地,也成為了中年人的行為日常。
“我最理想的狀態是大家看了以後,能對大三兒這個人有印象,能被這種人物所打動,打動本身的部分是他對生活的原動力和他對生活的態度,而不是所謂的勵志。”這是導演佟晟嘉的初衷,在這個層面上,他的想法應當算是實現了。至於片子是否對一部分人產生勵志的效果,這又是另一碼事了。
拍攝《大三兒》,前前後後大概用了四年。事實上,拍攝《大三兒》的過程中,佟晟嘉打過很多次退堂鼓,尤其是在西藏的時候。那時候,各種各樣的問題接連不斷,對大三兒身體的擔心,對參與拍攝的工作人員身體的擔心,對資金與危險環境的擔心等等,他差點兒勸說大三兒放棄西藏之行。但最後他忍住了,因為他覺得大三兒說的話是真的,“這次不去,下次真不一定有機會了。”所以,大三兒去西藏的心願和佟晟嘉拍攝他的心願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相互成全。
但佟晟嘉最初沒有想要拍成類似於如今公路片的效果,去西藏的計劃也是在拍攝過程中產生的。“我拍攝了很久才知道大三兒要去西藏,但就算他不去西藏,片子也照樣拍得成,他有可能組織工友去北戴河,也可能努力評上勞模,一切都是未知的。”

大三兒與好朋友阿皮、導演在布達拉宮下的合影。
在大三兒的這場遠行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大三兒去了西藏,而是他嘗試突破自己局限的這種努力。登上珠峰後,大三兒並沒有忙著去拍照、欣賞景色,而是自己在一個位置靜靜地等待著。他走過帳篷區,走到一片滿地鵝卵石的河灘,坐著,面對著珠峰看了一會兒,看著太陽一點一點隨著珠峰的黑灰之色落山。對於大三兒來說,西藏與其他人的意義是不同的,它無關信仰,也不是盲目的跟風,而是自渡。
“我只是把它作為一個高度,作為一個一般人到這兒的極限,別人由於種種原因如高原反應、條件惡劣或者身體狀況沒能到這裡,但我確實到了這兒,我能到這兒,到這兒還沒啥大事。”“有的人或許比我去得早,有的人或許在路上,但大家都有個積極美好的生活態度。我想表達的也是這點,不是第一個來的,但也不是最後一個來的,沒落下,挺榮幸,挺感謝。”
大三兒看得很透啊。
在大三兒身上,其實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影子,導演的、大三兒周圍人的、你的、我的,所有人盡力生活的掙扎與可能都在大三兒的身上顯現著。我們追逐著“大三兒”,不想被生活打垮,不想喪,努力活得有勁兒,其實是對於自身境遇的一種反抗與表達。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文中所涉及到的紀錄片中沒有的情節與對話,來源於同名書籍《大三兒》(版本: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作者:風小楊;編輯:西西。題圖取材:紀錄片《大三兒》(2018)劇照局部。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