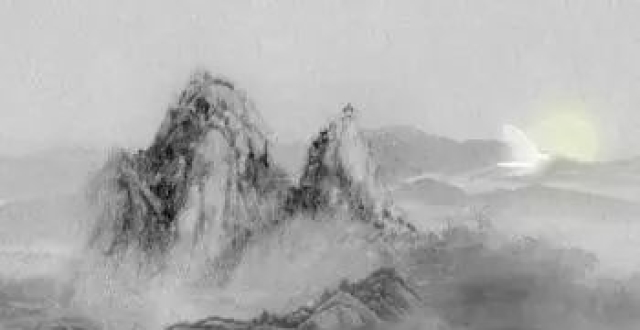恆之博士解讀《詩經》第97篇
【還】
97.1子之還(xuán)兮,遭我乎峱(náo)之間兮。並驅(qū)從(cóng)兩肩兮,揖我謂我儇(xuān)兮。
97.2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97.3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詩序】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鄭玄箋】荒,謂政事廢亂。(《毛詩正義》卷五,2000:387)
【朱子集傳】
獵者交錯於路線,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朱熹《詩集傳》卷五,2011:76)

1
章太炎曾經說過,清末時候有一些二傻子或者文雅一點的話,就是妄人,想要把漢字廢了,用羅馬字。他們根本不知道,沒有文字,還有什麽中華的文化可言。一個國家之所以是一個國家,就是因為有歷史、有文字,如果沒有歷史,沒有文字,那是什麽國家?如果強行地把歷史和文字鏟除掉,那麽這個國家最後還能保留什麽呢?(《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506頁)
章太炎說,他到處講學的目的就在於保存這種文化。因為,他能講,其他人不能講,《詩》雲:“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此之謂也。
妄人從來沒少過。後來,也有人試圖要徹底消滅漢字,認為漢字阻礙了社會發展什麽的。比如說,《詩經》中的《還》篇“還(xuán)”“儇(xuān)”“峱(náo)”之類的,看起來就費勁,如果用ABC之類來表示就不會有難度了。好在是,章太炎所說的妄人們沒有成功,不然我們今天可能也不用讀《詩經》了。雖然後來漢字簡化了很多,但好歹還保留了不少。有時候,保留一些有難度的東西,是必要的。
章太炎在當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崇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上世紀初以來,搞中國學術的最頂級的學者,十之八九和章太炎及其門人弟子都會有一些千絲萬縷的聯繫,友朋?學生?同盟軍?反對者?崇拜者?鄙視者?等等不一而足。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998)就稱,章太炎和胡適兩人是先開一代新風的“大學者”,而不僅僅是經學家、史學家。
這些大學者,既有專業上的專精造詣,為某個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還跨了專業和學科,對學術史造成了影響,可以說是學術史上的漩渦,攪動了學術發展的方向和內容。陳平原稱之為有思想的學問家,因為他們“既是社會思想激蕩的表征,其引領風騷,更構成思想史上絢麗的風景線。”(《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2010,第21頁)他們有各自的學生、友朋和反對者。也就是說,各有一幫人在他們的周圍或者後面,形成了一種勢力,讓後面做研究的人不得不重視他們。
當然,即便是想要漠視之,也得給他們安排一個好位子,比如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中按照《水滸傳》的人物譜系,把章太炎比作舊頭領托塔天王晁蓋,也就是說,如果現代中國的學術是一個像“水鄉梁山泊,賊盜聚眾打劫”的好地方的話,那麽真正讓這個圈子變成了一個有聲勢的地方的人物就是晁蓋。
華夏出版社“偉大傳統”系列中的《詩經二十講》(2009)開篇是章太炎的一篇文字,選擇的是《國學演講錄》(似即曹聚仁整理的《國學概論》)一書中的一篇,題為《經學說略》的講演稿子,其中對《詩經》有這樣的講法: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先有志而後有詩。詩者,志之所發也。然有志亦可發為文。詩之異於文者,以其可歌也。所謂歌永言,即詩與文不同之處。永者,延長其音也。延長其音,而有高下洪纖之別,遂生宮商角徵羽之名。律者,所以定聲音也。既須永言,又須依永,於是不得不有韻。詩之有韻由歌永言來。(《詩經二十講》,第4頁)
這段話看起來很複雜,其實就是對《尚書》的一句話進行了初步的解說。詩歌和人有關,當然,除了人之外還有誰弄詩歌呢?可並非每個人都會弄詩歌的,唱歌的人或許很多,寫歌的永遠是一部分人,得是那些有志的人才會有詩歌。
什麽是“有志的”人呢?不知道。至少應該不是“幼稚的”人吧。有志的人能說會道,說的還能唱出來,唱出來的就是詩,不能唱的就是文。既然能唱,那就不能是一個調子,像蜜蜂只會嗡嗡叫,那就不成為歌,人的詩歌是有韻律脈動的,所謂的律就是固定下來某個節奏的意思。
有志的人自己唱完了,希望別人也跟著唱,所以他們定了調子,後面的人就不會變調了。有志的人是不是領唱呢?難道說古代的詩篇都是大合唱?不太清楚。《詩》雲:“子之還(xuán)兮”意思是說,您真的是很厲害啊,這樣能扯。不,還有更厲害的,“揖我謂我儇(xuān)兮。”
最早人們為什麽會唱歌,和人們為什麽會寫詩,其實不必有直接的關係。詩歌,當然是連在一起的。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有文字的詩篇,而不是口口相傳的某個調子。現在討論的所有的詩歌,一般都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僅僅以某個曲調而存在的東西。以曲調而存在的,沒有文字的,那是另外一種東西,不是詩歌。比如,我們聽到的各種曲子,那不是詩歌。
這個事情討論起來就沒完沒了了,所以還是看看其他的東西為好。比如《詩序》之類的。

2
1921年,出版界編纂了一部《章太炎的白話文》的書,該書的開場白說:
太炎先生是中國文學界的泰鬥,這是誰也知道的,並且誰也樂意承認的。不過他著的書,往往說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氣橫秋”的文言,初學的人,看了總覺得不大舒服。因此便自然發生一種要求:就是,怎樣能直接聽他的講?好了,有了。你們的唯一的講義,就是這本書。
關於詩序,有很多的爭議,現在釋經學中,很少還有堅持《毛序》的,但是很多現代的關於《詩經》解讀的書,都會自己搞一個詩序來,這些書中的詩序,大概有各種辦法,其中最簡單的是把朱子的話用現代漢語翻譯一下,也就差不多了。實在沒有辦法翻譯的,就隨便弄一個主題句放在那裡就行了。對此,章太炎先生是不同意的。他認為朱子的《詩集傳》其實做得並不是很好:
《詩經》用朱子《集傳》,朱子的書惟有《詩傳》最壞,因為聽信了鄭樵的亂話,把《詩序》都削去。若說用三家詩麽(魯詩、韓詩、齊詩,叫作三家詩),三家詩並沒有真本留存,依然用的《毛詩》;記用《毛詩》,又刪去詩序,這是什麽道理?
況且《詩序》所說,《國風》都是關於國政,朱子削了詩序,自去胡猜,把《國風》裡頭許多正經話,說成淫奔期會的詩。諸公要用經典教人修身,到這裡卻矛盾自陷了。《鄭箋》雖則有許多詰詘,大義總沒有差,就說《鄭箋》不大好,《毛傳》原是至精至當的書,略有眼睛的,總曉得比《朱傳》高萬倍呢。
大概注疏本嫌它太繁,單注本卻是不繁,原有刻本,何不將來翻印,卻用這班陋劣荒疏的注本。
還是總領學校的人,不曉得有那種書呢?還是看了這種注本,真個奉為金科玉律?
看來總領學校的人,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教書的人見識差不多。我們要人看經典,不管經文是真是假,注文是好使壞,隻用一句修身的假話去籠罩,又不曉得注文於修身是有利是有害,用意只在迷惘人。(《章太炎的白話文》,第34頁)
我們知道,現在一般的《詩集傳》的單行本都是沒有《詩序》部分的,也沒有《詩序辯說》的。這是因為後來人在編輯書的時候,怕重複,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比如已經有了《詩序》單行本了,《詩集傳》中就不再附錄了。可是,《朱子全書》中的《詩集傳》是有《詩序》部分的,在《五經大全》中的《詩傳大全》也是有《詩序》部分的。我們今天看《詩集傳》,沒有序說,並不代表以前人編纂同樣的書的時候沒有。所以,章太炎的批評只能說可以針對一部分出版物,這樣的人的確是“比半日賣草鞋半日教書的人見識差不多”。
《毛詩序》認為,《還》篇和齊哀公有關,因為他就知道去打獵,他提拔人的唯一標準就是看誰打獵打得好。對此,朱子在《詩序辯說》中說:“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打獵打得好的人是人才,但是不是齊哀公才這樣看,那就不知道了。《詩》雲:“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意思是說,得虧我們還知路線在哪裡,不然就真的被人給騙了。

3
很多人認為宋明以來的學術,或者更甚的說整個中國的學問,在修身方面比較重要,特別是儒家的經書多是修身的。可是如果按照朱子《詩集傳》的解說,詩篇中真的有很多是男歡女愛的。這個和他們講的去私欲的觀點是大相徑庭的,這樣就根本沒有辦法講下去了。最極端的當然就是朱子的後學,要刪掉詩篇中的鄭衛之音了。可是,這樣做基本上是沒有什麽道理的。章太炎還說:
若怕人說經典沒用,就要廢絕,也只要問那個人,歷史還有用麽?如果他說有用,那麽經典是最初的歷史,怎麽可以廢得?
如果他說過去的事,都沒有用,那麽就該轉問他:你看了西洋史,記得希臘羅馬的事。記得二百年前英俄德法奧美的事,要作什麽用處?一樣都是過去的事,和現在都不相乾。
一邊還是本國事,一邊卻是別國事,別國事過去沒用還應該記,本國事過去沒用,就不應該記麽?那邊自然塞口。就要發廢棄經典的妄論,再也沒有立論的根源,不過是狂吠亂叫,總不怕別人會聽信,又何必用修身的名目去保護經典呢。(《章太炎的白話文》,第36頁)
很多搞學問的人,喜歡攻訐別人的人和書。要麽,人是垃圾;要麽,書是垃圾。總之,沒什麽用,統統是垃圾。這就像是“一個人做弓,一個人做箭。做弓的說:只要我的弓,就好射,不必用箭。做箭的說:只要有我的箭,就好射,不必用弓。”(《章太炎的白話文》,第40頁)
搞學問的人這樣講是沒有什麽問題,因為他們做了弓,弄了箭並不是為了去放倒獵物,而是為了掙錢。如果打獵過日子的人要真的聽了這樣的話,去打獵,大概能從野獸那裡逃出來就算幸運的了。
很多人搞學問就是這樣的,聽了別人的說法,就奉之以為經典,順便自己做個中盤,騙騙人而已。騙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大師了。
“比如日本人說陽明學派,是最高的學派,中國人聽了,也就去講陽明學,且不論陽明學是優是劣,但日本人於陽明學,並沒有什麽發明,不過偶然應用,立了幾分功業,就說陽明學好。原來用學說去立功業,本來有應有不應,不是板定的。就像莊子說:能不龜手一也,或以侯,或不免於洴澼絖。本來只是湊機會兒,又應該把中國的歷史翻一翻。明末東南的人,大半是講陽明學派,如果陽明學一定可以立得功業,明朝就應該不亡。”(《章太炎的白話文》,第41頁)
陽明學從民國時代火過一陣子,最近又火起來了,大概情形都差不多。章太炎那個時代是因為日本人說了好,自然有人說好;而今天則是另外的人說了好,也就有一批人覺得好。可惜了,《詩經》似乎還沒有被人這樣說過,關鍵《詩經》也不能拿去治理天下,《論語》還行,所以釋經學中《論語》要比《詩經》火,畢竟有用才是真理。
當然,別人說如何如何,關鍵還在於我們能不能接著說出更多的來,甚至比對方講的更有意思。在這方面,章太炎是做了表率的,所以他是大學者。《詩》雲:“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意思是說,無論對方再精彩,再瀟灑,再有氣派,在我們看來,也就那樣罷了。在我們這裡,得“揖我謂我臧兮”。詩人還真是喜歡自吹自擂。

4
如是,章太炎的提醒值得我們反思:
“夫講學而入於魔道,不如不講。昔之講陰陽五行,今乃有空談之哲學、疑古之史學,皆魔道也。必須掃除此中魔道,而後可與言學。”(《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493頁)
1933年4月18日,章太炎發表了《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中,章氏說,古代的經書不是為平民所作,“大抵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人君讀《春秋》,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範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
即便我們今天已經把孔夫子作為所有老師的老師,我們也要知道,其實從事老師這個行業的人畢竟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都是被教育的,像詩人那樣覺得別人很厲害,而我更厲害的人,畢竟只是少數人。所以,有時候,我們知道詩人很厲害也就差不多了。章太炎說:
余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抵之學之士,當如童蒙,務於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於余者,工夫正須爾也。(《章太炎全集演講集》,第505頁)
當然,今天我們讀古代的書,無論它經典與否,可能很少能背誦下來的,那些能脫口而出背誦了很多東西的人,大概是最強大腦之類的人。一般人看看也就差不多了。因為,絕大多數人,看都不會看,更別說背個什麽東西了。章氏曰:
“文學者,以有文字者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為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有經傳解故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後人擯此於文學外,沾沾焉惟華辭之守,或以論說、記序、碑志、傳狀為文也。獨能說一經者,不在此列,諒由學官弟子,曹偶講習,須以發策決科,其所撰著,猶今經義,是故遮列使不得與也。”(《國故論衡疏證》,第頁)
章氏的這句話說的是,他認為古代的文學,實際上就是用文字做記錄。寫的好的,記得多的就是鴻儒。他們寫了很多東西,有的甚至自成一家了,也就成了某某子了。就跟今天寫小說的人差不多,誰寫的好,誰寫得多,就能在排行榜的前面。最能掙錢的一些人叫作IP,其他的人也就是碼字工人或者鍵盤農民。寫得東西當然什麽都有,類別很多。
講故事的,說道理的,還有一些應用文,生老病死,都得來上一段。古代的文人把文字看得很神聖,很有職業精神,不像現在,基本上是個人都能寫點了,也就沒有什麽文字神聖的概念了。《詩》雲:“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古人看到了比自己厲害的人,非但不會羨慕嫉妒恨,反倒是立馬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感覺,馬上稱讚對方,而那個更牛的一方則寫了首詩來說這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