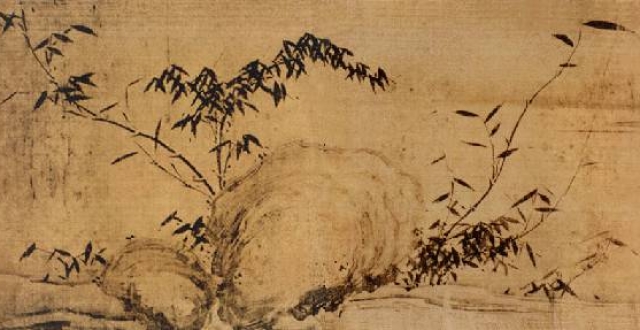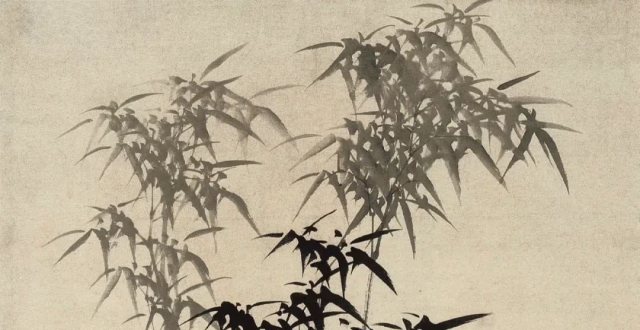無論是創作還是審美都是“眾生隨類各得解”,都有無盡馳騁的空間。

錢鍾書先生曾談到兩種創作方法,一曰即物生情,二曰執情強物;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到“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意思和錢先生基本類似。
即物生情是創作者對事物的感知、諦聽和描繪,是從物事情感到形象語言,再到意境生成的創作過程;執情強物則是主觀先入,是把意念強加於物事,通過自我營設、情境喚起以“違其性而強以就吾心”。
比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蘇軾)、“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等等,是通過客體本具而引發詩意,屬於即物生情;再比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劉禹錫)、“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崔顥)等等,是先有主觀情感統攝,以此觀照客體,屬於執情強物。

前者,多為收縮性寫作,即先對客體產生直觀感應,即心以應物,再動之以情,述之於筆;後者基本上屬於發散型寫作,是所謂不按常理出牌,以主觀意念混淆造物、統領外物。
再比如繪畫,僅舉一例:從來有“喜氣畫蘭,怒氣畫竹”一說,這是即物生情,假使你反其道而行之是否可以成立呢?我以為也是可以成立的,誰說怒氣不能畫蘭、喜氣不可畫竹呢?況且有時非怒非喜,塗上幾筆蘭竹也未見得不精彩,所以,凡事不可太“概念”,“非此”未必“即彼”。王陽明有謂“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是很好的關於主客體的哲學詮釋,不過,話說回來,卻也是典型的“執情強物”。
從各個藝術門類來講,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加以詮釋,畢竟藝術是內在相通的嘛!限於篇幅,就不一一羅列了。
可有時我卻覺得這兩者之間不能完全割裂開來看,而是一種相互作用,或者說彼此圓融,甚至有時不見得那麽好區分。所謂“意與境渾”“意與象合”,是物我相融、彼此打通;朱熹說:“身心內外,初無間隔”,則是心與物化,得心而應手。世間事,殊途可以同歸,陰陽可以互補,主客可以換位,上下可以相傾,藝術創作,也不存在什麽約定俗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

“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孟子),這可以說明審美存在通感,所以才會有共鳴,當然,也有“意不稱物”“心不應物”,即表現不到位的問題;董仲舒提出“詩無達詁”“片言以明百義”,我覺得思路比較開闊,意指藝術有韻外之致,無論是創作還是審美都是“眾生隨類各得解”,都有無盡馳騁的空間。
關於我們:
本公眾號乃上海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新民晚報》副刊《夜光杯》的官方微信,《夜光杯》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副刊,在微信平台,我們將以全新的面貌繼續陪伴您。歡迎免費訂閱,我們將每日精選兩篇新鮮出爐的佳作推送到您的手機。所有文章皆為《夜光杯》作者原創,未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