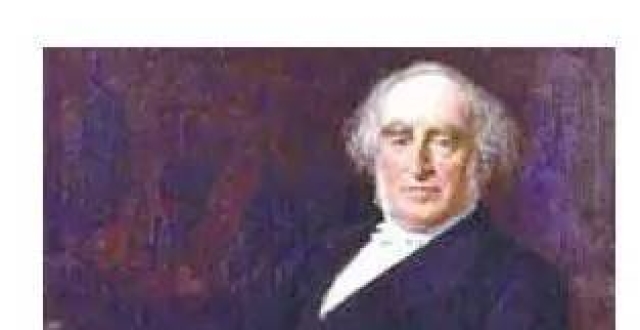朗讀:薛南燕
音樂:Hans Zimmer - One Day(《加勒比海盜》原聲)

編者按:奈保爾出生於英聯邦成員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一個印度婆羅門家庭,後在英國展開學業和創作,最終認祖歸宗,在英國文化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奈保爾的經歷對西方與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碰撞有一定的典型意義,而他對第三世界的觀念也給他招來了不少的批評。
葉兆言 | 橫看成嶺側成峰:讀奈保爾
與西方交流始終是中國文化面臨的大問題。即使一個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也會很輕易明白,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與西方分不開。我們燒香拜佛,我們吃蕃茄,吃西瓜,吃西洋參,我們聽胡琴,聽琵琶,聽羌笛,我們看電影,看電視,習慣了,也就順理成章地變為自然。好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奈保爾的《米格爾大街》,當時並沒有想到這個人會得諾貝爾獎,我甚至都沒有過分在意作者的國籍。對於我來說,奈保爾就是一個外國小說家,不是英國,也不是西方,而是一個來自叫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地方,我的地理知識甚至弄不清楚它究竟在哪個位置。這不由地讓我想起童年時的外國文學態度,只要明白它不是中國就行了,它是一個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外國”。
讀者對外國小說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寬容,我們可以用一種與己無關的心情把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米格爾大街》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麽意想不到的驚喜,也許是有足夠的閱讀經驗,我首先感到的並不是它的獨創,恰恰相反,我感到的是它的熟悉,雖然是本新書,感覺卻好像是舊的。文學藝術不只是喜歡新鮮的陌生,有時候也願意遇到一些熟悉親切的老面孔。換句話說,讓我感到最滿意的,它是一本很不錯的外國小說。對一個讀者來說,外國小說有好有壞,《米格爾大街》恰好屬於好的那一類。

《米格爾大街》很容易讓我想起一連串的美國小說,譬如安德森的《俄亥俄•保士溫》。我還想起了海明威的《在我們的時代裡》,同樣是晨光出版公司的書,它的譯者是馬彥祥。當然不會漏掉呂叔湘先生翻譯的《我叫阿拉木》,作者是美國的亞美尼亞移民,最初的譯名是索洛延,後來變成了流行的薩洛揚,比較完全的一個譯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人間喜劇》。我並不想考證它們之間的關係,很可能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只想強調它們給我帶來的相似聯想。
《米格爾大街》與上述小說近似點在於,都是用差不多的角度來觀察自己熟悉的生活場景。這就好比用差不多外形的玻璃瓶裝酒,用不同的建築材料蓋風格相似的房子,在具體的操作上,有著明顯雷同。這麽說並不是惡作劇的揭秘,而是隨手翻開作者的底牌。簡單的事實只是,世界上很多優秀作家都是這麽做的,好作家壞作家的區別,有時候僅僅在於做得好不好。魯迅談到外國小說的影響,曾說過他每篇小說差不多都有母本。這種驚人的坦白,說明了第三世界小說家的真相,在如何觀察和表現熟悉的生活場景方面,我們都有意無意地借助了已成功的外國小說經驗。不是我們不想獨創,實在是太陽底下已沒什麽新玩意。以西方的文學觀點看待文學,這話聽上去怪怪的,而且有喪自尊,其實當代小說就是這麽回事。我們的小說概念,差不多都是西方給的,連魯迅他老人家也虛心地承認了,我們當小輩的就沒必要再盲目托大。

很顯然,現代中國小說離開了外國小說,根本沒辦法深談,這就仿佛在佛教影響下,我們一本正經談禪,談出世,因為習慣,自以為就是純粹的東方情調,是純粹的本土文化,其實說穿了,都是西化的結果,隻不過這次來自西方的影響更早一些而已。
從《米格爾大街》到《畢斯沃斯先生的房子》,我感到最大的驚奇,不是奈保爾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是他的國籍,已悄悄地從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改成了大英帝國。無論是翻譯者,還是出版社,在寫作者的身份認定上,遭到前所未有的尷尬。這個尷尬同樣也非常客觀地放在全世界的讀者面前,奈保爾究竟應該算作是印度人,還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人,或者說是英國人。既是,又都不是,我們中國人可以說這根本不重要,反正他是一個洋人,用一個含混不清的“外國”,就可以輕易地將奈保爾打發了。對於我們來說,這或許只是一個困擾外國人的問題,中國人何苦再去操心。
毫無疑問,奈保爾已經成了英語文學傳統的一部分。與艾略特加入英國國籍一樣,奈保爾成為英國公民,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歸宗。在展開“歸宗”這兩個字之前,我想先談談奈保爾說話的態度。不同的態度將會產生不同的語調,在《米格爾大街》中,奈保爾顯然找到了一種屬於他的敘述語調。用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就是,童年的聲音加上了中年人的目光,或者說童年的視角揉合著中年的觀點。雖然奈保爾寫《米格爾大街》的時候,剛剛二十二歲,但是因為有良好的文學熏陶,他的語調中已洋溢著一種飽受教育的超然。這是一個有文化的人在訴說著沒文化的事情,目光冷靜,清醒,無奈,因為有洞察力而一針見血,作者投身於小說之中,又忘形於小說之外。平心而論,這種寫作語調本來就是天下作家的公器,隻不過奈保爾利用得更好。奈保爾正是借助這部作品,找到了通往藝術迷宮的鑰匙。

……
奈保爾的敘述方式既古典又現代,既符合世界文學的優良傳統,又因為自身的努力探索,發展和豐富了世界文學。他的嘗試,實際上是所有第三世界作家應該做的事情。當然不是指文化上的簡單歸宗,而是如何準確和有效地展現我們自己世界的精神面貌。文學說穿就是一種態度,一種準確和有效的表達方式。奈保爾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生活,換句話說,用西方人的觀點說殖民地故事。有意無意之間,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落後的一面,暴露了愚昧,暴露了黑暗,揭示了缺少現代教育的真相。奈保爾的藝術實踐帶來了一個直接後果,這就是西方人看到了奇風異俗,第三世界看到了西方人的歧視目光。奈保爾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讓發達世界和不發達國家,通過這種特殊的方式,不同尋常地進行了文化上的交流。

儘管奈保爾接受了典型的英國教育,繼承的是狄更斯以來的英國文學傳統,作品本身已成為英語優秀文體的一部分,曾多次獲得包括毛姆獎布克獎在內的多種文學獎項,並被英國女王授予“騎士”,但是所有這些,仍然改變不了他的殖民地身份。他的小說與純粹大英帝國出身的毛姆,與吉卜林,與福斯特,與波蘭裔的康拉德,有著明顯的淵源和發展,但是他永遠也成不了真正意義的西方人。就像我們看奈保爾是外國人一樣,純粹的西方人觀點與我們也一樣。奈保爾無論在文化上如何歸宗,在今天或未來的文學史中如何有地位,他仍然是一個西方人眼裡的外國人。
對奈保爾的接納或許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權宜之計也可以看作是發達世界的無奈,畢竟世界文學不等同於發達國家的文學。在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西方發達世界的文學水準雖然始終佔據著霸主地步,但是文化的稱雄,畢竟和經濟軍事不一樣,世界文學永遠願意接納有創造性的新玩意,沒有新玩意的世界文學就沒有活路。風水輪流傳,奈保爾的幸運,在於符合他世界文學的需要,迎合了潮流,並且順利地融入主流中間。

(本文節選自丁帆、王堯主編“大家讀大家”叢書分冊《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葉兆言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江蘇明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策劃出品。如需轉載,請聯繫公眾號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