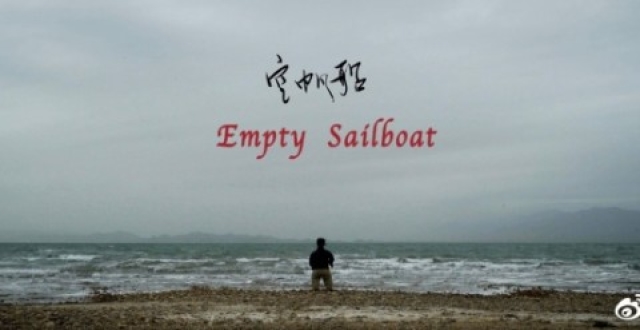《大三兒》導演的話
文/胡赳赳
記者:有人總結這個片子是中國第一個關注小人物的紀錄片,你自己是否認同這樣的看法?
佟晟嘉:我認同。但是我之前確實沒有想過我是不是要關注中國的小人物。更多的我覺得它是普通——我更喜歡用普通人,而不覺得他是個所謂的小人物。我拍的時候覺得他是英雄,尤其在生活方面。生活裡我們特悲壯,在今天這個時代活著就是一件特別不容易的事。所以從一開始,我的動機更多的是想讓大家看到自己在生活面前,我們值得被表揚,尤其是這種看起來特別的人物,他更像屬於自己的一個英雄,家庭的英雄。
記者:這個片子把鏡頭語言放的更低,我們很少用這樣一個視角去看我們這個世界。我們有時候會用搖臂、俯視或者仰視,但很少用平視的方式,但是它又比正常人的視角低。你覺得這個視角意味著什麽?
佟晟嘉:另一個世界。也可以說它是一個侏儒的世界。但我覺得不是,這就是你身邊人的世界。當你面對身邊的人,如果稍微低一下,能看到很多東西,能得到更多的東西。其實大三兒就是這樣。我跟他相處這麽多年以來,有這麽一個朋友,他能從根本上解決你的問題。他比較純粹,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他那種特別本質的東西,要靠這個視角來完成的。不是說他身上有,是你身邊所有人身上都有,就看你怎麽看,就看你怎麽來面對。當然從技術層面來講,我在竭盡全力把“我跟他這麽多年相處裡我覺得他很正常”拍出來,勢必要把鏡頭放低。我一定要跟他在一個世界裡,我把他的世界拿出來,因為他的世界是正常的。那些人和人的關係是正常的。

記者:這個片子裡體現了你對紀錄片的哪些理解?
佟晟嘉:我可以說我對我想象的紀錄片的看法——我一直在力求一種方式,用這種純粹的真實紀錄、陪伴式紀錄、枯竭式紀錄的方式,塑造一部電影出來。我理解的電影是有一套語言體系的,它的語言體系就是它的鏡頭,就像我們寫字一樣,拍好一個電影,寫好一篇文章首先你要會寫字,電影也是這樣,隻不過我們做電影的方式是在不斷地、重複地把它完成。比如說我拍他穿衣服的一場戲,可能要拍十天,每天穿衣服,然後我把這十天穿衣服的場景剪成一場戲。它不影響客觀事實,因為他都是在穿衣服,但在電影的敘述裡面,它會更完整,更有語言體系。我們有句話叫所見即所得,所得即所呈現,所呈現即所表達,如果在這一條體系裡我做到了,那我的紀錄片就成立。這是我對紀錄片的看法。
記者:你說的這種枯竭式的紀錄,在紀錄片中是怎麽樣體現的?
佟晟嘉:我們的拍攝方法是陪伴枯竭式紀錄,從你早上一起床就開始跟著你。你七點起床,我們六點半就到了,在你還沉睡的時候。你起來睜開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們。開始他(大三兒)會有些不適應,需要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時間才適應。它不像傳統紀錄片周期很短,比如說一周的拍攝。我們要的是枯竭式紀錄,就是我給你做個電影,從現在開始,在這三年的時間裡,我們會定期來或者不定期來,你不用管我們,不用搭理我們,該吃吃該喝喝,該睡睡該上廁所上廁所。我們一直存在,慢慢的,我們就像一個台燈。我們的任務就是讓被拍攝者,也就是被紀錄者忘掉我們、習慣我們、把我們當空氣一樣。大概這就是我所謂的枯竭式紀錄,永遠早開機十分鐘,永遠晚關機十分鐘。
記者:《大三兒》紀錄了多少小時的素材?工期大概有多少?
佟晟嘉:從我們第一天開始拍一直到最後大概400多個小時。從開始張羅到完事兒大概是4年左右。後期的時間有半年左右,拍攝大概是兩年,陸陸續續前面的策劃、調研,他(大三兒)的適應時間零零散散有一年左右。

記者:這個紀錄片對你而言最困難的部分在哪兒?
佟晟嘉:最困難的部分是跟他太熟了。
記者:要有距離感?
佟晟嘉:我覺得他活得挺精彩的,可以很牛逼地、毫無羞澀地把我們一個小城市的生活狀態拿出來,把它給放大以後,可以影響更多的人。讓他們知道生活不容易,但生活就是這樣,忍著往前走就行了。我覺得這個東西特別有價值。好朋友這麽多年,我沒什麽可以送你的。送你一部紀錄片,我覺得特別有意義和價值。我也想說一件事,就是好朋友之間必須要這樣。好朋友不僅要互相成就偉大的功業,魚活在水裡,人活在情裡。“情”字沒了,活著就沒有滋味了。這都是我的初衷。
記者:你自己在剪片子的時候哪些地方是最觸動你?
佟晟嘉:他跟他爸對話,“你這個手機鈴聲如何如何,這麽大歲數了還用這個鈴聲”,他爸說他,“你這個好,說白了你這個不怎地,我用個鳥,你用個青蛙”,這種父子關係,在這樣一個家庭裡,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一種狀態。我覺得父子應該是這樣,中國的父子應該是這樣。這是一個,再一個是墓地。他在墓地說他們家人都在那兒,那個資訊我早就知道了,那個不感動我,感動我的是什麽呢?是當我拍攝的時候,他說的那些話。我倆每年年底、清明都會一塊去,因為我有車,他拿那些東西很費勁,我會幫他一下。他念叨那些話就是我們心底裡流露出來的。
當你在攝影器裡看這段素材的時候,我的感受跟觀眾還不一樣,因為我放大了自己的生活。當他幾個頭磕到地上的時候,我看到的是我自己,因為我每年也那樣。然後我認識到了,我們這個民族,東方這個國度裡的人,他所有的寄予,都在那個地方(墓地)。沒有在莊嚴的寺廟裡,也沒有在華麗的教堂中。
這個地方是中國人最牛逼的地方。無限的子孫綿延,無限的祖先回望,一回頭全是祖先,一抬頭全是子孫。所有的東西都在這,極具儀式感,而且數千年來都是這樣。我就覺得我骨子裡這個東西是改不了的。所以我會把片子裡那個部分拿出來,他的願望都在那裡表達出來。
最後極具打動力的,是他告訴我,他寫那封遺書的時候,我挺吃驚。他告訴了朱朱,那個(朱朱)才是他生命中重要的陪伴他的人。大三兒看到珠峰第一個就跟朱朱分享,說我不能自己獨享,朱朱就跟他說,你照顧好自己,有機會我開著我的小三輪拉你去。這話說得對,這話說得太對了,他重複了一遍,讓我覺得挺感動。我覺得這個叫朋友。你看我這樣來了,我沒忘了你,我給你寄張明信片,讓你看看珠峰;你好好照顧好自己,然後到時候我開著小三輪拉你去。真美好。

記者:在這個片子裡頭能看到一種人性的尊嚴,體現在他要寄明信片人家不收他錢,他硬要給錢;他說我喜歡去北京,因為在北京沒有人用異樣的眼光看他。除了尊嚴之外,我們還能夠看到大三兒這樣一個普通的人物,他身上的一種生存策略,你是怎麽理解大三兒,他的有關於生存策略的行為方式的?
佟晟嘉:可能是我跟他太熟了的原因,或者是我比較主觀,他的生存我覺得無異於常人。我們面臨的東西他都面臨,從吃喝拉撒到喜怒哀樂,他有部門,有部門的同事;他有朋友,他也擔心我是不是找誰聚會,聚會我這個月錢夠不夠;我應該怎麽樣讓自己的錢多一點,我是不是要把攢起來的錢買點理財;這個月我是不是多上一天班。
他生存策略最核心的部分,這麽多年他秉持的一個原則,就是不給好朋友添麻煩,這也是為什麽所有的朋友都願意幫助他的原因。包括去西藏也能看得出來,借錢也好,跟我進行博弈也好。他知道事該怎麽處理,說話有分寸。
在生存面前,他本身面臨的問題,他爸說得特別清楚,這裡面沒有任何人有異樣的眼光。我覺得這個既是本質又不讓人討厭。
再有一個,他在生存面前,想的比誰都清楚,因為他的命運他看得特別透,他在中年往回看,不是往前奔著看,計劃著明天。他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未來。他能把一些事悟透特別重要,所以即便去了西藏,他也沒有說要靠神佛保佑自己,他想的都是自己的事。他知道什麽是緣分,有緣千里來相會,他也可以化解,“我跟他們的緣分就這麽長”,跟親人的緣分,跟母親的緣分。
記者:你拍赤峰那個城市拍的也很有煙火氣息,很有質感。
佟晟嘉:它是一個小城市該有的那種感覺。我印象裡我的家鄉就那個樣,我小時候其實就是那樣,其實到現在比我小時候變化很多,但是我還是願意去觸摸那種感覺。
(文章有所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