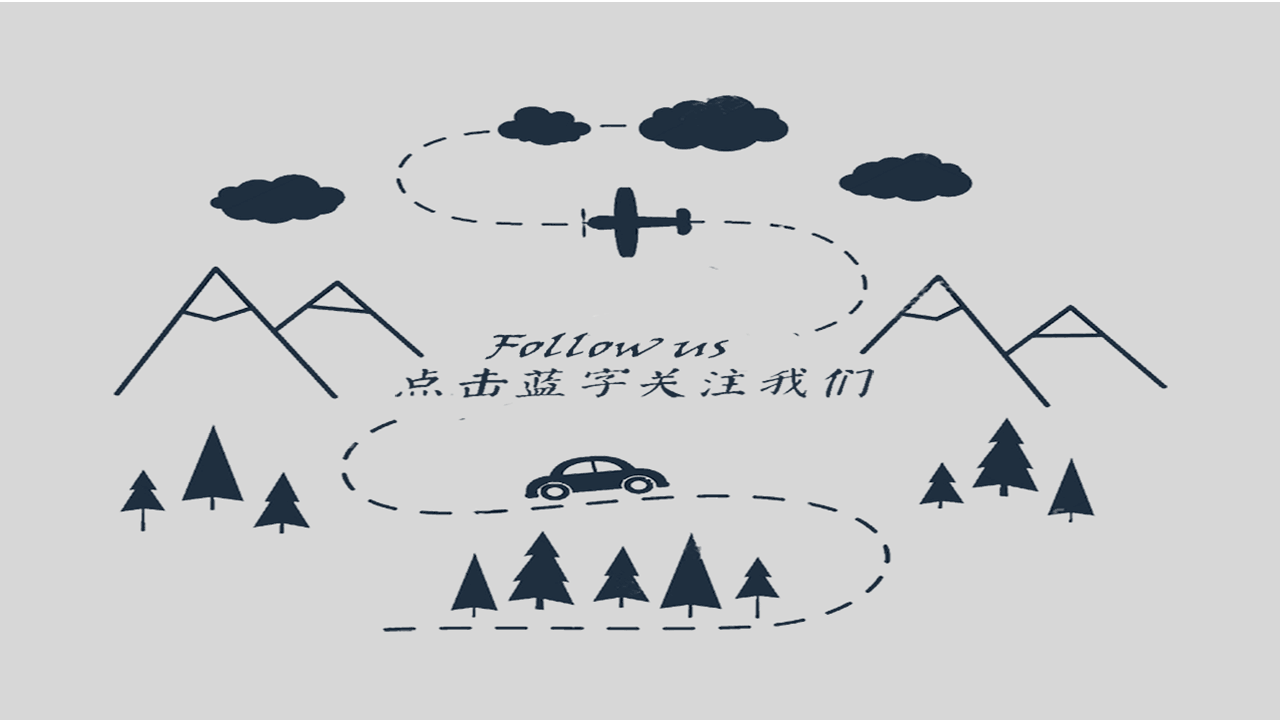當前,中國人口的老齡化程度正在加速加深。截至2017年底,全國人口中60周歲及以上人口有2.41萬人,佔總人口的17.3%,比上年增加了0.6個百分點。預計到202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其中80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067萬。
老齡化面對的首要嚴峻問題就是疾病與護理,而在所有折磨老人的疾病中,最殘酷之一當屬阿爾茲海默症。這種疾病不僅會對患病老人帶來失語、視太空技能等生理損害,更重要的是以記憶障礙、失用、失認等形式表現出來,其痛苦不單由患者承擔,更是讓身邊的親友深陷絕症帶來的漩渦。我國是全世界阿爾茲海默症病患人數最高的國家,迄今已有將近900萬的患者。而這其中的每一位都需要至少兩名親友及護工的照料,換言之,至少有2億中國人正在遭受阿爾茲海默症的折磨。在這個過程中,包括阿爾茲海默症在內的疾病也引發了另一些問題:當個體記憶在逐漸消失,代際記憶將如何延續?老年人的病痛會不會改變年輕人的生活與精神狀態?
對疾病的描述註定是痛苦的,但正視疾病不僅是醫護工作者和社會職能部門的職責,也是所有人應該重視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曾是或將是病痛的主體,也同樣曾是或將是親人病痛的承擔者。前不久,上海圖書館舉辦了一次以「文學如何表現遺忘與記憶」的主題講座。三位主講嘉賓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講述,在老齡社會與衰老、絕症和死亡正面對話的過程中,文學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表現創傷;人類又怎樣通過文字留下這段特殊的時代記憶。


衰老、死亡,
是父輩最後教我們的東西


於是,上海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寫有小說《查無此人》《六翼天使》《事後》以及散文《時間之間》《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杜馬島黑暗塔》等20餘部文學作品。
3個月前,我剛剛出版了一本長篇小說,叫《查無此人》,描寫了一名本想「浪跡天涯」的年輕人因為父親突然患上阿爾茲海默症而改變生活軌跡,一邊照顧父親一邊尋找失落的家族記憶的故事。這本書我前後寫了七八年的時間。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一本小說會寫這麼久?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本書是以我的家庭為原型,也是從我父親剛剛患上阿爾茲海默症時開始寫的。沒錯,我就是這樣在10年前突然變成了阿爾茲海默症所折磨的2億人分之一。
那個時候我還很年輕,大概30歲出頭的樣子。父親患病前,總覺得自己的人生還有很多很多夢想沒有實現,心很野,想要雲遊四方,生活過得也粗糙。但因為父親得病需要照顧,我的整個生活方式突然被改變了,也恍然間因此認識到了一個問題:自己的青年時代結束了。我開始懂得什麼是「老」,意識到自己跟上一代人之間的差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好像這種代際間的距離突然被「疾病」縮短。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會寫這樣一本書,只是因為父親生病了,會在照顧他的當下做一些直覺性的記錄,這些記錄甚至都不能稱為一個句子,就是在陪他散步緊緊抓著他時,偶爾在手機上敲下的一兩個詞語。
這樣的狀態一直延續到父親的疾病發展到中晚期的時候。這時,父親的語言技能、方位感等等已經全部喪失了,我發現我面臨的最大問題反而不是怎樣去照顧他,而是怎麼樣面對「記憶」的問題。一方面,我父親這一代人,是隨新中國的誕生而出生的,他們經歷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重大的變革。以前年紀小的時候不太會去問他們,但到了你有意識想去問的時候,他卻已經忘了。
另一方面,就是家族記憶的斷層。到了父親患病末期時,我們開始幫他聯繫一些家裡人,卻發現我們對此真的知之甚少。父親是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大學生,算是靠著讀大學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一批「移民」。可對於他從前的「根」,父親很少說起,這導致我們這些移民的第二代,很多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從何而來」、「身歸何處」。所以到了這個階段,我意識到,如果用一個完全紀實的手法去寫這樣一種特殊的疾病好像還不夠。所以我決定把它寫成一個小說,只有小說才能夠容納我剛才所說的那些思想和提問。我希望它能從一個殘酷的疾病出發,描述半個世紀以來相當一部分人、一部分家庭的家族記憶和走向。
在怎麼表現阿爾茲海默症給父親和一家人帶來的影響時,我還面臨著一個問題。大家平時看到的社會新聞和文藝作品,很多都容易把阿爾茲海默症這類疾病寫得很戲劇化。我曾看過一個國外的電影,講的是一個90歲的老人,他在確診阿爾茲海默症後,知道自己不久後將喪失記憶,於是他覺得在那之前,一定要去找一個曾經在集中營迫害過他和同胞的納粹軍官。這個故事講的就是這樣一趟復仇之旅。
說實話,這類故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問自己,從戲劇性的角度來講,是不是我也應該編一個類似這樣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呢?後來,經過了很多次的自問,我最終決定還是要寫一個平凡的人,恰恰要把關於疾病、遺忘和面對生命盡頭的情緒沖淡。因為書中的父親是這個時代很多老人的一個縮影,他們曾經歷過很多,但誰都無法停留在歷史的漩渦裡。到書的最後,他其實變成了很多人的父親,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份與老去的父輩之間漸行漸遠的親情。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在書的前言扉頁上寫下「每一個人都有出生入死」這樣的話。生活本身就是戰場,已無需我再在書中製造一些額外的衝突。
而面對這些,書中的女兒王子青其實比我本人要勇敢,她送走了父親之後重新整理了自己的生活。失去父親對任何人來說,都會痛徹心扉。但我不想隻讓這種痛楚停留在撕裂和破壞的層面上,它也應該成為人生的必修課。一位我很喜歡的作家奧格爾曾有這樣的一番話。他說,從小到大,父母都在教我們些什麼呢?他們先是教我們吃飯、說話、走路,等我們稍微再大一點了,他們開始教我們處事之道,教我們怎麼為人。等他們到了晚年的時候,其實他們能夠教我們的就只有疾病、衰老和死亡,這是他們用自己的人生最後教給我們的東西。


因為疾病,
文學為生活做了不尋常的事


黃昱寧,著名作家和英文文學翻譯,資深英美文學編輯,出版有散文集《假作真時》等,同時致力於翻譯譯作及解讀英美經典文學。
菲利普·羅斯是一位去年剛剛去世的美國猶太裔作家,他以小說成名,但在一生的作品中,有一部《遺產》是他很少見的非虛構類作品。
這本書的主人公同樣是他患絕症的父親,但並不是阿爾茲海默症,而是腦瘤。不過與前者相似的是,患病後期,腦瘤也同樣影響到了他父親的記憶和行為。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羅斯回憶起父親留給他的遺產時,他說,這樣東西不是猶太經文,不是錢也不是古董,而是排泄物——因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父親是大小便失禁的。
這種表達方式,所有讀者都會覺得很直接,但又能感受到一種文學的特殊力量。這個經歷,其實只要是有病人需要照顧的家庭裡都會有,但不一定所有的家庭都能有一種文學性的語言去描述它。這個意義上,文字確實是可以被保留下來被大家不停地咀嚼、不停地反思的很好的媒介。
用文字處理遺忘、時間和生命,還有一類作家可以以日裔英國小說家石黑一雄為代表,這樣的主題是他幾乎所有小說的中心問題,無論是他早期的代表作《長日將盡》,還是《被掩埋的巨人》。而且,他的作品涉及的不只是一個個體,還可能是一個民族、一個集體怎麼去面對遺忘。有的時候他會自我欺騙,因為他要面對的東西太傷痛了,裡面可能還有一些不能為人道的東西,比如戰爭和殺戮。文字中,石黑一雄好像把這些東西處理得模模糊糊,隨著閱讀的深入,他再一點點把細節透露給你,你才發現原來他的敘述不像你開頭想像的那樣,也許讀到最後一頁,你才能把整個事情拚成一個完整的形狀。
就像於是這本《查無此人》一樣。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在於,書中表現的兩代移民之間的隔閡,比如新一代移民不理解老一代是怎麼樣來到這裡,為什麼許多年過去了仍然可能會有「水土不服」,甚至他們從來沒有真正融入過這個城市。所有這些不理解,都因為父親的患病而發生了轉折。也許是更為凸顯,也許是找到了答案。正是因為年輕人驟然意識到,父輩的記憶馬上要被奪去了,而後人可能永遠沒有機會再復原那個記憶,所以才會像尋找救命稻草一樣,回到家鄉去追溯家族的記憶。
試想,如果他的父親以別的方式終老,這種不理解可能一輩子都不會被打破。
書裡有一句話:「疾病把我的父親掏空了,我要重構它,也許我只能虛構它。」是的,因為重構幾乎是不可能的,很多時候只能靠想像。而這個時候,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疾病才觸發了年輕一代這樣的需求。從文學的角度來說,這也是我對這個小說特別感興趣的地方。說得殘忍一點,文學不會希望生活就這樣「平常」地過去,它需要這樣一種外力,或許是疾病,或許是衰老甚至死亡,來促使它做一些不尋常的事情,留刻一些印記。


時代語境下,
我們不只談論如何「照料」


潘天舒,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復旦-哈佛醫學人類學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醫學人類學城市社區和商業和技術人類學研究,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基地項目和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老齡化和護理實踐等國內國際研究項目。2002年及2005在美國喬治敦大學和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院任教,主要著作有《政策人類學》《當代人類學十論》等。
我的醫學人類學導師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是當代醫學人類學的重構者,在相關的領域享有非常高的聲譽。他與中國很有淵源,太太瓊是漢學家,而他本人也常來國內做演講和交流。他的學術背景非常豐富,學過歷史,而後又從事醫學和醫學人類學。
而就在他60歲那一年,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妻子被診斷為阿爾茨海默症。身為哈佛大學醫學人類學教授,他周圍的朋友都是頂尖的神經科醫生,對妻子的醫學診斷下得非常快。但即使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醫學技術和資源,對於妻子,凱博文依舊無所適從。
於是,60歲~70歲的那10年,凱博文開始了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妻子的艱難歷程。他在社工的建議下,雇了一位有醫學經驗的照護者,朝九晚五地照顧妻子,使得他白天能繼續講課、出席會議、撰寫論文。而下午5點到第二天早上9點,則是他照顧妻子的漫漫長夜,直到2011年,妻子病逝。而目前,他正在籌劃寫一本書《照顧的靈魂》,講述自己照顧妻子的這10年的所思所得。
當我在閱讀像《查無此人》這類小說的時候,我既逃不脫自身職業帶來的認知方式,也同樣代入了個體作為讀者的一種直觀感受。目前,學界有很多正在進行的關於醫學人類學的定量研究,有滿足各種各樣需求的問卷和調查。但它們到最後可能沒辦法落實在解決一個具體的實實在在照料阿爾茲海默症老人的方法上。
與此同時,國內也有很多學者在做敘事醫學方面的努力,我認為,這本書和類似的內容就可以成為我們敘事醫學做更進一步努力時的參考和方向。
毋庸諱言,我們的小說家經常在研究社會問題上是走在前面的。遺忘和記憶,它們都是人類學裡重要的核心主題。而相關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就在於,寫作不是單純地為了寫照料,而是把這樣的事情植根在日常的生活體驗和時代下,作為一種有普遍性的人文事件、一個道德事件,充滿了複雜的人際情感交織,同時,還對未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隨著我們國家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未來的老年病患照料者人數會越來越多,而且都是處於全球化和時代轉型語境當中的人,有自己的工作,可能很多都會因為照料行為而改變了自己原本的人生。這樣的文學創作在人類學中就是一種典型的「田野研究」,做參與式觀察,在研究對象的生活環境中去生活,學會他們的語言,沉浸到他們的生活中去。
同時,這本書還包含著另外一種關於「死亡」的啟示。社會科學裡,死亡一般是「社會的死亡」和「生物的死亡」的集合體。一般來說,生物的死亡通常都伴隨著社會的死亡。但是小說裡的情節也十分普遍,在父親臨終之際,你要去補充關於他歷史的記憶,回到父親的故鄉,激活很多人對父親的回憶。這是否說明,在社會意義上,你的父親還活著?這也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記憶形式。
而除了對老齡化這個護理實踐的研究之外,我覺得這類文學作品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有關精神障礙心理疾病的汙名化的問題。就像癌症、麻風病人,早期也被汙名化過。費孝通先生說我們要有文化的自省。在我們文化裡,幾千年來都有針對精神疾病的人群不同程度的特殊歧視。而如今,我們又生活在這個高度醫療化的社會裡面,又或多或少都會用科學主義的這種話語來指導自己的生活,這個是免不了的。但這種時候,我認為文學可以幫我們邁出反汙名化的重要一步。
整理/健康報記者魏婉笛
原創聲明:以上為《健康報》原創作品,如若轉載須獲得本報授權。
點擊下方愛心,您的贊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