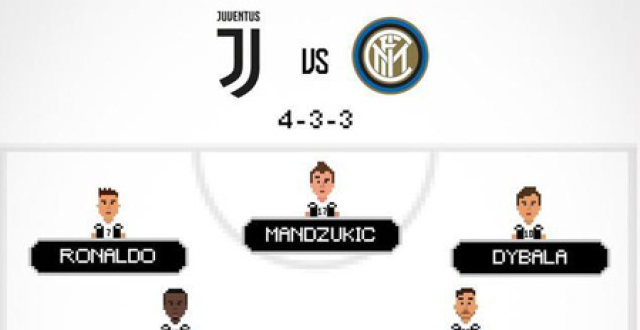摘要:即將爆發的戰爭令教宗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它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僅波及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亞,還會貽害整個歐洲。許多人認為,只有教宗能夠阻止這場戰爭。然而庇護心裡明白,在這麽重要的事情上違抗意大利獨裁者,將會給他們的盟約招致巨大的風險。
墨索裡尼有意逾越雷池
墨索裡尼的野心和自負都在與日俱增。他希望公眾能夠視他為偉人,令羅馬重獲古代的榮光,但是想要達成這個目標,他就必須締造一個帝國。他的目光轉向了埃塞俄比亞,整個非洲只有它和利比裡亞還沒有落入歐洲的掌控之中,而且意大利還有區域優勢,它的兩塊殖民地—意屬索馬裡蘭和厄立特裡亞分別同它接壤。
領袖其實早已暗示過他的意圖。早在1934年末,埃塞俄比亞的武裝力量曾經在瓦爾瓦爾(Wal Wal)開槍襲擊一群越過邊境、從意屬索馬裡蘭深入到埃塞俄比亞境內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的媒體稱這起事件是對意大利國家榮譽的挑釁。墨索裡尼威脅道,除非埃塞俄比亞做出道歉和賠償,否則意大利將發起戰爭。墨索裡尼大張旗鼓地將幾個師的部隊派遣到意屬索馬裡蘭,並且將一支艦隊開進了紅海,囑咐他們聽候進一步的指示。庇護十一世對此非常不滿,他擔心意大利如果入侵埃塞俄比亞,會使得整個非洲的傳教士都陷入險境。

與此同時,教宗也越發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身體力行地主持剛剛過去的那個聖年(於1934年復活節結束)令他筋疲力盡。他已經不再去梵蒂岡花園散步了,甚至簡單的穿越大廳都令他喘不過氣來。炎熱的氣象也開始困擾他。在老城較為貧困的區域以及外圍不斷擴張的棚屋區,電力和自來水仍然十分少見,而肺結核病和沙眼病卻十分猖獗。在過去的一年裡,羅馬爆發了斑疹傷寒症的疫情。1934年夏天,老去的教宗期盼著回到位於阿爾巴諾山的避暑宮殿。“你能看得出來他有多高興,”在教宗出發的那一天,皮扎爾多的助手多梅尼科·塔爾迪尼觀察道,“他就像一個馬上要出門度假的男孩。”塔爾迪尼抓住教宗心情愉悅的機會,為救濟俄國人爭取到了三萬四千里拉的資金。塔爾迪尼寫道:“啊,要是教宗能常常出門度假就好了!”
一位線人報告說,如今的教宗“變得更加易怒、陰沉和多疑”。在執行公共職能的時候,身穿華麗白袍的他猶如帝王般巋然不動,令周圍所有人感到緊張和不安。他的發際點綴著絲絲白發,然而他的聲音依舊堅定且洪亮,至於厚鏡片背後的那雙眼睛,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警覺。儘管他行動已經有所遲緩,但是他仍然堅持過問一切事務,並親自做出決定。
墨索裡尼威脅要入侵埃塞俄比亞,這件事令教宗十分煩惱,但是其他教會人士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博洛尼亞的《意大利未來報》是意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報紙,它回應了法西斯媒體的主張,表示埃塞俄比亞人都是些信仰異教的野蠻人,戰爭能將文明(以及天主教)帶給他們。
這場即將爆發的戰爭令教宗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它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不僅波及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亞,還會貽害整個歐洲。許多人認為,只有教宗能夠阻止這場戰爭,來自世界各地的意見都敦促他警醒墨索裡尼,讓他放棄入侵計劃。然而庇護心裡明白,在這麽重要的事情上違抗意大利獨裁者,將會給他們的盟約招致巨大的風險。

1935年8月27日,來自二十個國家的兩千名天主教護士登上了梵蒂岡的巴士。她們正趕赴會議的最後一幕,在岡多菲堡聆聽教宗的教誨。庇護在講話中褒獎了她們所做的工作,講話時長超過一個小時。然後他為這些護士送上了祝福。負責組織這場會議的皮扎爾多滿面光彩地站在教宗身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教宗並沒有就此離開,而是打開話匣子,突然提起了一個全新的話題。他告訴護士們,人民永遠都不會容忍侵略戰爭。那將是“一場不正義的戰爭,超出了所有想象……它的恐怖令人無法言說”。皮扎爾多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塔爾迪尼蒙席在日記裡寫道:“這些護士多半是外國人,她們興致盎然、饒有趣味地聽著。然而皮扎爾多蒙席膽戰心驚,一點都高興不起來。這簡直是一場災難!”在返程巴士上,為了防止護士們討論教宗最後的話語,皮扎爾多堅持要求她們念誦玫瑰經。當他回到梵蒂岡時,已然涕淚俱下,他看起來“垂頭喪氣、面色慘白、神情絕望”。他嘴裡喃喃念叨著教宗的話語,這是“一場不正義的戰爭,一場不正義的戰爭”。
第二天上午,當教宗的演講傳進意大利駐梵蒂岡代理大使朱塞佩·塔拉莫的耳朵時,他急急忙忙來到梵蒂岡。這位意大利外交官回憶道:“皮扎爾多蒙席的臉上滿是驚慌失措的神色,他告訴我,教宗突然決定發表這番敏感言論之前,沒有表現出任何可疑跡象,他甚至沒有征求過國務卿的建議。”
塔拉莫向皮扎爾多提出了他的要求,梵蒂岡報紙在報導教宗的這番講話時,要盡量緩和其中的針鋒相對。皮扎爾多向他保證,他和他的同仁已經“竭盡全力,盡量弱化教宗這番評論的語氣”。記錄講話內容的《羅馬觀察報》記者在那天傍晚將教宗的演講打字稿提交到梵蒂岡,而塔爾迪尼則對其“動了一場手術”。塔爾迪尼回憶道:“我在這裡刪去一個詞,在那裡又增補一個。我在這裡調整了一個句子,在那裡又抹掉一句。簡而言之,通過細微而富有技巧的改動,我們成功地軟化了教宗演講中特別粗礪的內容。”他們最後修改出來的文章和護士們聽到的那篇譴責侵略的檄文相差甚遠。最終版本只是一系列語義含混的話語,可以對其作出各種解讀。
第二天早上,棘手的問題出現了。塔爾迪尼必須讓教宗同意這篇大肆刪改的文章。當把打字稿遞給庇護時,他盡量讓自己顯得波瀾不驚,方正的臉龐上露出十分誠摯的表情。他解釋道,那位《羅馬觀察報》記者擔心自己沒能記錄下教宗的每一句話,希望能夠得到教宗的原諒,教宗整整講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到最後這位記者已經筋疲力盡了。他當時牙疼得厲害,所以也稍稍有些分心。而且在演講的最後,夕陽(這場接見安排在外面的院子裡)的光芒逐漸消退,他也就更加難以準確地記錄下教宗最後的話語。
教宗開始閱讀文稿時,塔爾迪尼試圖告退,然而庇護抬手阻止了他。教宗把所有的文字都放到一邊,直奔最後的那幾段話。他一邊閱讀,嘴裡一邊發出哼哼聲。教宗每次抬頭看他的時候,塔爾迪尼都試圖隱藏自己緊張的神情。那段關於戰爭的文字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教宗把它大聲朗讀出來,而塔爾迪尼仍然假裝自己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我擺出的那副姿態,就好像是一個人在關心他毫不知情的事情。”他又在括號裡寫道:“其實那部分被改成什麽樣子,我完全心知肚明!”教宗不斷地低頭看看文稿,又抬頭看看塔爾迪尼。他每讀到一句被塔爾迪尼篡改的文字時都會重複道,“我真的沒有這樣說過”。每一次教宗提出異議,塔爾迪尼都會謙卑地表示要修正這些錯誤。不過到最後,教宗只是說道,“算了,這件事就這樣吧”。這個結果正是塔爾迪尼和他的上級(皮扎爾多和帕切利)所希望的。
即便這份文稿的言辭已經大為緩和,然而代理大使仍然對它感到不滿。儘管法西斯媒體斷章取義地引用它的內容,證明教宗支持這場戰爭,但是在意大利國外,經過刪改的評論還是被用來證明教宗是反對這場戰爭的。法西斯媒體的歪曲(它們聲稱教宗的這番話語明白無誤地支持意大利發動戰爭)令教宗感到氣憤,於是他命令梵蒂岡報紙在頭版刊登專文,就其歪曲表示不滿。塔拉莫非常不高興,他告訴墨索裡尼:“教宗真是一個固執的老人,也許這番話有點冒犯,卻離真實情況相差不遠。”
在周五與帕切利的例行會面中,塔拉莫發現這位國務卿與他看法一致。他向墨索裡尼報告說:“國務卿樞機也向我吐露了他的驚慌失措。”
事實上,儘管歐金尼奧·帕切利已經擔任國務卿達數年之久,但是他同教宗的關係仍然非常正式,在情感上保持了距離。那年早些時候,當巴黎大主教讓·韋迪耶(Jean Verdier)到訪羅馬,帕切利曾同他會面。帕切利得知,一場盛大的儀式將於4月在法國盧爾德的朝聖地舉行,這位國務卿很想參加這場儀式,但只有經過庇護首肯他才能夠參加,而他不敢開口提出這個請求。這位國務卿只好難為情地請求韋迪耶向教宗提起這一事宜。而教宗最後答應這次出行,正是通過這條間接的管道。在韋迪耶眼裡,這些年間,帕切利和教宗的關係還算是“友善,至少是這位老教宗的脾氣所能夠允許的友善”。
梵蒂岡對墨索裡尼的約束蕩然無存
9月初,國際聯盟召開會議,就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國際聯盟成員國)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國際聯盟聲稱,如果墨索裡尼敢這麽做,那麽它將對意大利施以嚴厲的經濟製裁。
自從公教進行會紛爭在四年前得到解決之後,教宗越來越公開地表達自己對法西斯政權的支持。1932年9月,數千名加入法西斯黨的海外青年來到羅馬朝聖,教宗在聖彼得大教堂為他們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彌撒。同一個月,數萬名意大利法西斯青年團體成員在羅馬附近進行演習,大量神父陪同了這次演習,他們帽子的十字架下方是一個法西斯黨標誌。教宗在梵蒂岡接見了數百名這類神父,並為他們的重要工作施以祝福。
梵蒂岡對領袖的熱忱在“進軍羅馬事件”十周年時也大放光彩。《羅馬觀察報》對領袖的熱愛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墨索裡尼在“所有公共管理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深刻和卓有成效的改進”,這份梵蒂岡日報報導說。從1921年第一次在國會發表演說起,他“就極力在全世界弘揚無比美妙的公教理念和教會使命”。這份報紙提醒讀者,讓十字架回到這個國家教室和法庭的人正是墨索裡尼,也正是他將宗教教導重新引入學校,並且通過《拉特蘭條約》為教會和國家帶來了和諧友好的關係。

在教宗向護士們發表脫稿演講之後的那幾周裡,帕切利樞機和皮扎爾多蒙席試圖說服教宗,讓他不要宣揚反對墨索裡尼發動埃塞俄比亞戰爭的意見。9月13日,帕切利給墨索裡尼發去消息,表示教宗將不會對侵略提出反對意見。
但是教宗仍然希望自己能夠說服墨索裡尼,放棄這項入侵計劃。9月20日,他口述了一封寄給墨索裡尼的書信,列舉了諸多理由表明這場戰爭何以是一個錯誤。他認為,儘管意大利在軍事力量上佔據優勢,但是埃塞俄比亞部隊卻擁有地利,畢竟那邊的地形十分複雜。教宗未卜先知地預言道,即便意大利攻下這個國家,意軍也將面臨無止境的遊擊戰,更別提高溫和疾病了。
帕切利擔心反戰言論若出現在教宗的正式書信中,很可能會惹怒墨索裡尼,於是他說服教宗派遣塔基·文圖裡以非正式的方式傳達了他的想法。庇護喊來了耶穌會士,遞給他一份文本,告誡他不要被墨索裡尼拿去了。由帕切利準備的這份打字稿首先對侵略計劃的目標表示理解,意大利需要擴張,也需要行使自衛的權利;然後它列舉了教宗關心的幾件事情,並著重強調了其中最可能觸動領袖的一件:如果戰事進展得不順利,那麽墨索裡尼就很有可能受到指責。
然而這些話語絲毫無法動搖墨索裡尼。10月2日晚,他來到威尼斯宮的陽台上,將激動人心的消息傳達給公眾,他已經命令意大利軍隊向埃塞俄比亞進軍。四周的建築隨著數十萬人富有節奏的口號聲而顫抖:“領袖!領袖!領袖!”
在廣場的另一端,瑪格麗塔·薩爾法蒂透過寬大的窗戶注視著這個場景。儘管她已經失去了情婦的光環,儘管近幾年來墨索裡尼愈發疏遠她,但她仍然是他最忠誠、最得力的宣傳人員,尤其是在海外。但是近來,納粹在德國的崛起愈發令她感到恐懼,而無視埃塞俄比亞的國際聯盟成員國身份向其發動戰爭,並且挑釁英法的行為,她明白這只會讓意大利落入希特勒的掌控。這場侵略戰爭絕對是下下策。
薩爾法蒂轉向身旁的一位朋友,評論說:“這將是終結的序曲。”
“為什麽這麽說呢?”他問道,“你覺得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嗎?”
“不……我的意思是我們將不幸地贏得這場戰爭……而他將丟掉他的腦袋。”
第二天,愈發熱心於維護庇護和領袖之間和睦關係的塔基·文圖裡向墨索裡尼保證教宗不會妨礙他的戰爭計劃。“在這個最為危急的時段,”他寫道,“聖父對於我傳達的消息都非常滿意,而且他告訴我要第一時間向您轉達他的意願。”

《教宗與墨索裡尼: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崛起秘史》,【美】大衛I.科澤(David I. Kertzer)著,陶澤慧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出版。
教宗其實也擔心這場戰爭會讓意大利遭到孤立,於是他特意給英國國王喬治五世(George V)發去了一封請求信。這其實也不是頭一回,早在8月份,他就通過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給國王發去了一份消息,而國王在得知大主教的會面請求包含怎樣的實際意味後,找個借口推掉了。
帕切利樞機專門給國王準備了一封英文信。“國王陛下,”這封信如是開頭道,“聖父將這一非常特殊、非常個人的命令委託於我,要以非常機密的方式向陛下陳述如下事宜。”教宗“認為已經無法避免同埃塞俄比亞發生衝突,因為意大利拒絕僅僅將埃塞俄比亞帝國的周邊區域納為託管地區(而非保護地區,教宗認為根據條約意大利有權至少對其進行託管)”。帕切利表示,墨索裡尼的要求合情合理,並解釋說此次牽涉到的埃塞俄比亞區域都被“奴隸製和混亂”所統治,而尼格斯[埃塞俄比亞統治者的尊稱,即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在這些區域並沒有多少影響力。
英國大使震驚地從帕切利手裡接過信封,並用電報傳回倫敦等候指示。英國外交部部長拒絕接收此信。教宗的請求信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
(本文摘自《教宗與墨索裡尼: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崛起秘史》,【美】大衛I.科澤(David I. Kertzer)著,陶澤慧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毛乃高,注釋略,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

大衛I.科澤(David I. Kertzer),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布朗大學社會科學小保羅杜比(Paul Dupee, Jr.)校級教授、人類學系教授和意大利研究系教授,《現代意大利研究》合作創刊人及主編之一。曾任布朗大學教務長,美國社會科學史協會主席和美國歐洲人類學學會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意大利政治歷史、梵蒂岡研究、天主教會和猶太人。科澤曾兩次憑借年度最佳意大利歷史著作獲美國歷史學會意大利歷史研究會馬拉羅獎(Marraro Prize)。其所著《埃德加多摩爾塔拉的綁架》入圍1997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並已被改編成電影;《反猶教宗》入圍馬克林頓歷史獎(Mark Lynton History Prize)決選。
譯者簡介
陶澤慧,畢業於廈門大學英文系,現為譯林出版社圖書編輯,業餘從事文學、歷史翻譯,另譯有《奇想之年》《偷書賊》《午夜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