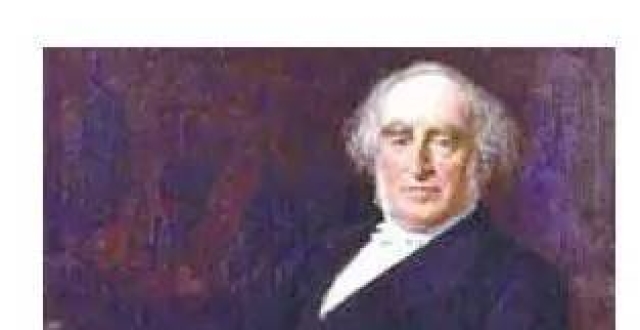明代以降,部分美洲作物被引進到中國,不僅影響了中國社會經濟、科技文化,而且早已積澱成一個儲量驚人的學術富礦,吸引一代又一代學者聚焦於此。傳統史學並無作物史分類,直到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後,梁啟超才主張研究作物史,“中國農業最發達而最長久,資料也很多,非給他做一部好歷史不可。農業、農器、農產物的歷史,都應該做”。至此,作物史研究進入學界關注的視野。回顧百餘年作物史研究歷程,經過萬國鼎等前賢學人的長期耕耘,產生了頗多具分量的作物史研究成果。進入21世紀後,“域外作物引種與中國本土化”課題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學界對南瓜、辣椒、煙草等美洲作物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更有作物史專著出版。花生為明代傳入的油料作物,晚清開始成為重要經濟作物。據筆者調查,當前中國花生史(以下簡稱“花生史”)研究並無專著,已有學術成果的關切點主要傾向於花生的名釋、起源與傳播以及影響,理論視角與行文角度相對缺乏新意,“花生史”的面相沒有能夠完整呈現。本文首先梳理與評述以“花生史”為主題的研究成果,繼而找出解決現有問題的突破點,探討下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構想。
一關於花生名釋考
作物名稱考釋是開展作物史研究的前提,夏緯瑛言:“一個植物名稱本身,就反映著在那個歷史時期我們先人對這種植物的認識程度。搞清楚這些植物名稱,不僅對於生物學史、農學史、藥物學史的研究會有很大幫助,而且對於從事植物學、農學、園藝學及中醫藥學工作的同志也是有所裨益的。”葉靜淵辨析了古籍中記載的“香芋”和“落花生”的聯繫與區別,彌合了農史界對此問題的分歧,認為古籍中記載的花生並不是都指油料作物花生,通過征引《汝南圃史》與《物理小識》落花生詞條,認為前者描述的花生從性狀來看不是當下的花生,後者的文本記載則與現在花生性狀無異;部分古籍中所載“落花生”可能是香芋的一種類型或品種。
中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文獻記載、風俗、語言等差異造成花生有多個別名,這一問題已有學人關注。何炳棣為研究明清人口、土地與食糧之間的矛盾,利用海內外數千種地方志研究了花生等美洲作物在華的引進與傳播,首次清點了花生名稱有“花生、地豆、番豆、豆魁、地果、地蠶、白果、人參豆、落花參、落地松、萬壽果,長生果、延壽果、及第果、相思果、地漏生、滴花生、土露子,無花果”等19種,並羅列了每個別名的文獻來源。孫中瑞認為花生有28種名稱,較何氏的統計新增了“滴漏生、香芋、落地生、落花甜、露下生、土花生、香遜、落生、??”。上述考辨嚴格意義上並不是“標準”的作物名稱考釋,僅簡單羅列了花生名稱及文獻出處,並沒有詳細史學論證,亦缺乏細節考究。筆者在閱讀文獻過程中,粗略統計花生別名至少有61種,細目如下:
花生、長生果、豆鳳、地豆、米凡、番豆、土露子、無花果、香芋、地果、滴露生、獨奈、滴花生、參豆、滴露、仙豆、土豆、千歲子、落花參、滴水生、塗豆、地頭、落地生、落華生、人參果、珠豆、落地豆、落花松、白果、落地松、花松、萬壽果、豆魁、地蠶、泥豆、人參豆、黃土、白土、露花甜、延壽果、露下生、及第果、相思果、落生、香遜、南京豆、及地果、成壽果、唐人豆、金果、長壽果、長果、相思豆、紅豆、匯果、落花甜、中國堅果、??、三眼連、大啟子、過路攬
花生別名眾多,我們在研讀史料時需特別注意異名同物和同物異名現象,以免各持己見,莫衷一是。同時厘清花生的別名及其命名原由,可以為我們探討傳統時代花生這一“物”的歷史提供清晰的研究對象。關於上述花生名稱的考釋,筆者將另撰文討論,本文不擬詳述。
二學術公案:花生是本土還是外來?
花生本來被公認起源於美洲,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浙江、江西等地考古挖掘或發現有疑似炭化花生種子,有學者提出花生可能也起源於中國,由此引發花生是“本土還是外來”之爭。學界常談“孤證不立”,已基本排除花生“本土起源”的說法。筆者依據辯論的思維邏輯,回顧支持與反對“花生中國原產論”學者的觀點,以此厘清爭論的本質與意義。
1960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公布《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遺址發掘出花生、芝麻、蠶豆等種子,“此次從遺址中發現了這些種子以後,可以證實我國在數千年以前已經開始種植這些農作物”。這一結論受到學者質疑。1962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公布《江西修水山背地區考古調查與試掘》報告,遺址出土疑似花生種子,因沒有鑒定報告,又隻發現少量實物,無法下確切結論。1980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彭書琳、周石保從群眾中獲得花生化石一枚,並通過了中科院植物研究院和廣西農學院等有關部門的鑒定認可。該發現在1981年《農業考古》創刊號發表後引起轟動,但也受到諸多質疑,為澄清事實,經過進一步驗證,確定此物為陶製品並非花生化石。因此,只有浙、贛兩處考古發現能為“花生中國原產論”提供論證依據。徐守成、張秉倫均征引此兩處考古報告認定中國為花生起源地,自古就有,並非外來。張勳燎對花生起源問題提出了新觀點,認為“世界範圍內,花生的起源是二元(或多元)的,除了南美洲一部分地區之外,我國也是花生原產地之一”。引《南方草木狀》記載: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跟下,須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恆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
由此認為“千歲子”即為花生。論據有三,首先從文獻記載的植物形態看,“蔓生,子在根下,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完全符合現在花生性狀;其次引蘇聯盧濟娜(3.А.Лузина)觀點“花生是在熱帶和亞熱帶氣候條件下所形成的一種植物”,又千歲子產於交趾(古地名,指五嶺以南一帶地區),符合風土條件。最後是從花生別名“長生果、萬壽果”說起,認為這兩個名稱都是從“千歲子”演變而來的異稱。
孫中瑞認同花生起源多元論觀點,提出上文未交待清楚的問題:首先,既然中國已栽培花生上千年,卻為何直到成書於14世紀的《飲食須知》中才有記載?其次,在被認作為油料作物加以利用前,花生在農業中地位低,這是否影響了其發展?花生別名眾多,是否可能以其他名稱出現在古籍之中。也有學者對花生起源地問題持謹慎態度:中國是否為花生原產地,有待進一步觀察。權威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農業歷史卷》“花生栽培史”條目(王達編)尚未能完全澄清花生原產地爭論。
遊修齡關注“花生原產地”問題的討論,其中讓他不解的是在爭論未釋的情況下,“花生中國原產論”的結論就不斷被出版的書刊征引,如梁家勉《中國農業科技史稿》(1989)、吳存浩《中國農業史》(1996)、王啟柱《中國農業的起源與發展》(台灣,1996)等。為澄清事實,遊作專文探討,從五個方面認定花生確非中國原產:一是文獻記載的缺失,中國有三千多年完整的歷史紀年,栽培的植物即使是很次要的都不會漏記,而花生在文獻中沒有反映出來;二是對考古發現的質疑,如果僅依據浙贛兩處有花生子粒出土,而不考慮花生資源的多樣性、花生植株的形態特徵與生理特性,就說花生的原產地是中國,顯然草率;三是認為花生種類的多樣性並不能證明中國就是花生的原產地,花生的多樣性不是始於新石器時代,而是在花生被引種之後;四是史學界對於花生既出現於新石器晚期,又不見歷史文獻記載的矛盾,無法提供確鑿力證,往往做折中解釋;五是過分強調花生出土的實物和碳十四鑒定,缺乏其他相關的證明或線索,孤證沒有說服力。上述五點論證了中國非花生原產地。至此,學術界關於花生原產地的爭議也就塵埃落地,再無學者對此提出異議。
綜合前文,“花生原產地”的爭議源自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浙江、江西兩省的考古發現,學界對此爭論了將近40年,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已基本認定中國並非花生原產地。由此筆者認為,若無新的考古發現或文獻材料,學界不宜再在此問題上浪費筆墨。
三花生在中國引種與推廣研究
關於花生何時從美洲引入中國的問題,眾說紛紜。1935年實業部國際貿易局編寫的首部《花生》專著中無法確定花生具體何時傳入中國,但認為花生主要分兩次由域外引入,一次為明代中後期引入的小花生,另一次為晚清引進的美國大花生,傳入的路徑也不同,“至於花生之輸入我國,亦不知始自何年,或說明神宗萬歷年間,外人傳入我國廣東、福建、沿海各地。至清鹹豐時代,漸次蔓延於中部諸省……其後美國宣教師,複以美國之大粒種花生,輸入我國,移植於山東各處,品質優良,出產豐富,北方諸省,紛起效尤,遂為我國重要農產品之一”。羅爾綱並不認同美國學者馬羅立(Nalter H. Mallory)在《饑荒的中國》所言光緒年間(約1891)花生才引入的觀點,認為花生最早由海外傳入到福建,時間應為明代萬歷時期,羅氏依據時人徐渭記載以及方志的佐證,具有一定說服力。李長年主編《中國農學遺產選集·油料作物》推測花生大抵在元明間或明代傳入中國,元代三部農書均沒有花生記載,所見最早文獻為1530年前後的《種芋法》,此觀點較羅氏所研究的花生引入時間有所提前。胡先驌依據《酉陽雜俎》記載,認為花生唐代以後已引進到中國,懷疑考古出土的花生為後代混雜進去的。這一觀點較前述花生引入中國的時間再次提前到唐代。公允地說,如果僅依據唐代筆記小說就認為時人已種植花生,這一結論無法立足。萬國鼎從文本從發,論述了我國現在栽培的花生種源出南美,明代至少已有四省栽培花生,最早文獻見於弘治《常熟縣志》(1503)。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所編《中國農學史》認為花生在中國引種為“十六世紀晚期,亦即明萬歷的早年或中年”。唐啟宇闡釋了花生種子是16世紀初由閩粵僑商從南洋葡人中獲得並帶回。美國學者拉塞爾·伍德(Russel Wood)同樣認為花生是16世紀初由葡萄牙人從海路傳入中國。韓茂莉依據元人賈銘《飲食須知》記載,認為花生傳入中國時間應在元代,但也強調元代並沒更多花生的記載。由上可知,學界對中國首次引入花生的時間有“唐代引入說”“元代引入說”“明代中後期引入說”等觀點,當前佔優勢的是“明代中後期引入說”,筆者亦認同此觀點。花生應是地理大發現後才由美洲傳播到世界各地,面世的中文文獻中,對花生開始進行連續性、系統性的記載主要在16世紀,從時間上來說比較吻合,具有更高的學術可信度。

近代美國大花生品種首先在山東登州引種,因其風土適宜,產出經濟效益好,全省普遍種植,繼而逐漸向全國推廣。學界對於大花生在中國的引種、推廣一直有較多關注。中國何時引入大花生種植?學界對此討論較多。趙國蘭所譯《大花生(長生果)入華之歷史》論述了“大花生種子是美國傳教士湯卜遜(Archdeacon Thompson)於1889年傳入中國,然後由梅裡士(Charles Rogers Mills)首先在山東登州府試種,因能榨油,價值大增,成為中國重要海外貿易商品之一”。毛興文對大花生引種時間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大花生可能在1870年前後引入山東,並且傳入不是一次、一路,而是多次、多路。王傳堂修正了上述觀點,考證了“1862年梅裡士博士來山東登州時即首次將美國大花生帶來最為可能”。王氏考證史料豐富,論據詳實,已基本闡釋清楚大花生何時引入中國(山東)問題。
前文已述,花生首先是被引入粵、閩,在東南沿海種植。那它是如何向全國推廣?學界亦有探討。20世紀80年代陝西師范大學史念海積極倡導和發展歷史農業地理學,並組織博士生對歷史時期中國的農業地理進行系統研究,其中斷代區域農業地理研究最早涉及花生在不同地域的引種與傳播,如龔勝生認為湖北種植花生的記載最早見於康熙初年,到清末民初湖北各地都已有花生種植;湖北花生既有直接從域外傳入的,也有從四川輾轉傳入的;湖南在嘉慶年間也已有花生種植,至清末,湖南湘江中上遊地區已成為花生的集中產區。周巨集偉闡述了清中期以後,廣東花生的種植獲得了較大發展,其西部沿海成為最重要的產區;而廣西省的花生是從廣東傳入,最早種植在桂東南一帶。此外,還有馬雪芹《明清河南農業地理》、李令福《明清山東農業地理》、耿佔軍《清代陝西農業地理研究》等對花生的區域推廣也有專論,在此茲不贅述。何炳棣提出,“系統論述作物的遷移離不開大量的方志”。上述對於花生的區域推廣主要基於方志等文獻的記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進入21世紀後,農史學界開始關注“域外作物引種與中國本土化”課題,出現一批碩博論文專門論述花生等域外作物在華傳播史,極大地推進了作物史研究。王寶卿首次對花生在中國的推廣趨勢進行了探討,推斷花生的傳播趨勢大致有兩個:一是16世紀初早期花生以東南沿海為中心向北方傳播,二是19世紀後期大花生由美洲引入,然後以山東半島為中心扇形向西、南、北方傳播,彌補了花生在全國推廣研究的缺口,但並沒有提供傳播路線的論證依據。
四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的切入
花生被引入中國以及推廣的過程,即“花生本土化”,實際是中國人們如何認知與應對以及適應的過程,學界對此研究主要從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視角切入。
晚清以降,花生已成為主要的商品經濟作物,陳為忠研究了“港口-腹地”新模式下的近代華北花生運銷體系,詳述了近代華北花生種植與貿易興起以及煙台(附龍口、威海)、青島、天津(附秦皇島)、上海等運銷系統的情況,強調以鐵路為主體的近代交通方式,與國際市場接軌進而融入國際市場,才是華北農業產業化的加速器。郭聲波、張明認為到20世紀20年代花生除少部分用於播種或自己食用外,大部分都進行了銷售,而歷史上花生貿易的出口地經歷了三次重要轉變:20世紀初期至20年代,花生出口主要是英美等西方國家;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花生主要出口到日本;1949年後,花生主要出口到蘇俄,1978年以後,花生出口地十分廣泛,但最大出口地仍是日本。王保寧論述了近代山東作為花生的主要產區,亦是重要出產地,出口的花生給各產區帶來了高效益,成為農家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以此可彌補糧食短缺帶來的生存問題。丁德超研究了清末民國時期河南花生的產銷狀況,論述該時期河南花生產業格局的嬗替、花生運銷及其集散市場等狀況,討論了花生的產銷對近代河南社會轉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花生種植收益超過糧食作物,優化了農業生產結構,打破了過於單一的農業種植模式;河南花生貿易向世界市場敞開,經營範圍有了很大改變,長距離貿易往來開始增多,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河南封閉落後的社會面貌;近代花生的產銷推動了河南金融業的發展。除上述外,丁德超還探討了近代河南花生業為什麽沒有長時段的發展,只有短時段裂變的原因:主要從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會經濟形態;受世界經濟形勢的影響;種植花生屬於“內卷化的農業”,種植風險大、後勁不足,上述也基本映射了近代中國花生業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韓茂莉強調晚清已降花生經濟效益的體現得益於引進了電力帶動的榨油機器。
張志超研究了英租威海時期花生的產銷對當地鄉村社會的影響,認為花生的種植過程是鄉村社會內部的生產聯合過程,主要從勞動力的雇傭與換工、農具的共有與借用、役畜的飼養、使用與肥料的購買、灌溉中的合作、資金的借貸等方面進行闡述;隨著花生新品種的推廣及由此引起的窮人與富人間衝突的更新,花生公會(鄉村自治力量)開始介入其中,並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鄉村社會內部強製內聚力遭到嚴重破壞,鄉村社會由內聚開始走向開放;花生運銷合作商的建立,是村內外力量相互整合的結果,通過花生運銷合作社售賣花生,規範了鄉民的行為與思想,使花生整齊劃一,徹底改變了過去花生銷售過程中的種種弊端,避免了中間商人的剝削,增加了農民收入。結論認為,花生的種植促進了近代威海鄉村社會由內聚向開放的轉變。我們可透過花生透視到一種轉型中的社會形態,即從相對封閉落後的傳統社會向開放性的近現代社會轉變。這是首次從社會史視角來研究花生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的嘗試,拓寬了“花生史”的研究視域,有助於更加深刻地勾勒出花生嵌入社會的深度與廣度。
近年來,一些學者從飲食文化史、食療史的視角來研究“花生史”問題。張箭認為花生傳入中國後,逐漸成為中國人最主要的乾果零食品食品,成了中國人重要的菜肴副食品和植物烹調油油料之一,有助於促進中國人向溫文爾雅、熱情好客的性格發展;花生還影響了中國的語言文化,這在謎語、農諺中不乏相關例子;花生具有良好的藥用功能,是重要的常見的中藥材。王思明認為花生的引入增添了人們的食物營養和飲食情趣,還增加了食用油原料的種類,豐富了我國食用油的品味:如花生傳入之初主要作為果品直接食用或做成菜肴、糕點食用,後來其油用價值被人們所認識,發展迅速,很快成為僅次於大豆的第二大油料作物。
五總結與前瞻
綜上所述,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學界對“花生史”研究已取得有分量的學術成果。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研究取向為中國是否為花生原產地,各學科數位學者從跨學科角度對其進行了數十年的爭論,已廓清花生的起源地問題,認為中國不是花生的起源地,所栽培種由美洲引入;20世紀80年代後,學界考證了花生的名釋,對花生在中國的引種時間、傳播路線以及影響有較多探討,還從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視角研究了花生本土化過程中的諸多面向,不斷給“花生史”研究帶來新的衝擊,極大地提升了“花生史”的研究水準。
縱觀前賢的研究,在資料使用、研究方法等層面仍存在不足。當前“花生史”研究運用的史料主要局限於地方志、古農書等方面,研究視域較為狹隘,不利於“花生史”研究的深化。筆者認為,面向花生的專史研究,我們可以采擷正史、政書、起居注、實錄、東華錄、聖訓、專題書(含農書、醫書、科技書等)、傳紀、日記、書信、文集、筆記、明清檔案以及類書和叢書等傳統文獻中的資料,也可積極搜集近代(1840—1949)與“花生史”選題相關的各類期刊、報刊(如《申報》《大公報》)以及官方調查報告,如研究近代花生對外貿易,就需要《中國舊海關資料》《實業雜誌》《國際貿易導報》等資料。另外,由外國人著錄的文本材料我們也需重視。如日本人所撰“滿鐵資料”“中國經濟全書”“中國省區別志”以及其他經濟調查報告;西人在華創辦、出版的英文期刊,如《北華捷報》/《字林西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等,上述外文文獻可以與中文文獻進行相互印證。史料是學術研究的基礎,我們通過拓寬史料的來源,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花生史”研究。研究方法是學術研究的靈魂,“花生史”研究面臨著研究方法的轉向問題,當前新文化史、後現代史學、微觀史、物質文化史、人類文化學等新史學流派逐漸在大陸史學界擴散,不少新視野、新材料、新方法的研究成果面世,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借鑒多學科知識與方法非常有必要。在新史學潮流的衝擊下,筆者亦在思考如何將作物史(花生史)研究與它們結合起來,以此推動作物史研究,肇建新的學術增長點。
除此之外,筆者僅就自身學養提出“花生史”研究還需關注的幾點問題,以求教於大方之家。具體地研究“花生史”,花生在中國的引種時間、傳播範圍與流通過程是“花生史”研究不可逾越的前提;花生是如何與歷史時期具象化的“人”產生內在聯繫,是如何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對人們的生活又產生什麽影響;處理好“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關係,厘清有哪些社會階層參與了花生這一“物的世界”(生產、運輸、分配、消費),花生與人的互動又可能構成怎樣的社會文化與人際網絡;積極學習和倡導“總體史”或“全面史”的研究路徑,避免陷入單一的“花生史”研究。上述將是“花生史”研究者進一步努力與思考的方向。
六結語
俗話說:“花生雖小,可以喻大。”為重構一部鮮活的、有數百餘年流淌軌跡的中國花生史,當下除了繼續挖掘文獻資料,更適宜調整研究的理念與方法,擺脫成式窠臼。在方法論層面可采擷作物史研究尚未系統運用的後現代史學、新文化史與微觀史學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並樹立自下而上的歷史觀、底層史學觀,拓寬研究視域,以花生為具體而微的切口,“神入”到歷史現場,勾連、貫通其蘊含的歷史節點、時代課題。著重論述和審視學界尚未深入涉及自晚明以逮花生技術史、國內外貿易以及對社會、文化“眾生相”的影響。以小見大,從整體史觀來考察花生與其場域的關聯與互動,以此來管窺晚明以降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的歷史本相。同時,亦可滴定出歷史智慧來回應當下花生發展的需要。這要求我們樹立多維度的重構歷史現場、還原歷史情境的研究傾向。我們亦可以嘗試通過敘述、描摹一種“物”的歷史來呈現史學研究的複雜性、豐富性和多面性。
發表於《科學文化評論》2018年第2期.
作者簡介:
陳明,1990年生,湖南邵陽人,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農業史;王思明,1961年生,湖南株洲人,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業史。

本文來源:農史研究資訊
轉自:青年人文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