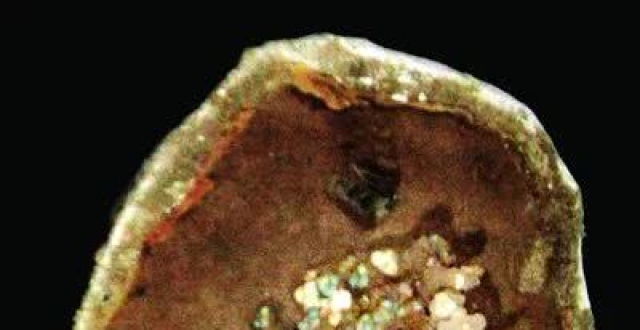文|新京報記者 祖一飛
編輯|胡傑 校對 | 危卓
本文約7218字,閱讀全文約需12分鐘
朱路路第一次上新聞,是因為出現在南京一座有600多年歷史的古墓裡。墓的主人也姓朱,確切地說,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個女兒,名號福清公主。
過去的半年多時間,朱路路幾乎每個晚上都睡在墓園的亭子下面。天亮之後,把鋪蓋卷起來抱進墓裡,再去附近的地鐵站廣場上等活兒乾。
像他這樣生活的農民工,最多時有二三十個。原本陰暗潮濕的古墓,被這群人用作倉庫和住房,成了一座臨時庇護所。
福清公主墓的後室,相當於一個20平米大小的房間。正中央擺放著一座2.87米長、1.6米寬的石棺床,一套破舊的被褥鋪在上面。東、西、南三側的壁龕中,各種雜物堆成了小山。西邊的一團衣服下,還藏著一袋鹽、一小包洗衣粉和一瓶橫躺著的老陳醋。
因為覺得濕氣太重,朱路路從沒在墓裡睡過覺。平時只有一個不愛說話的內蒙古小夥睡在墓裡。當地記者採訪那天,墓裡沒有其他人,進來放東西的朱路路就這樣被鏡頭捕捉到。他看起來有些不好意思:“我們沒找到活兒……身上有錢,但天天住賓館的話哪兒能住得起呢。”
金庸小說《神雕俠侶》中,“古墓派”因隱居在古墓中而得名。現實版的“古墓派”最近卻沒了清淨。圍繞他們,一場關於農民工生存現狀的討論正在進行。有人提及了農民工素質問題,有人認為應加強文物保護,還有網友發問:“死人與活人孰輕孰重”?
現實版“古墓派”
朱路路今年30歲,患有癲癇、因打架坐過牢的他,始終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父母早年間離開老家安徽,長住上海打工。姐姐也已經在常州安了家。但朱路路很少跟家人聯繫,甚至連姐姐的電話都沒有。
他向別人解釋,自己是被家人拋棄,不得已過上眼前的生活。“父母要是在乎我,早來找我了。看我沒什麽指望,就想把我甩掉。”
整個三月,朱路路打工收入1610元。其中,搬四天鋼管掙了800元;酒店傳菜兩天,每天9個小時,按照15元時薪算總共270元;鋪兩天草坪,原本應得420元,老闆考慮到沒管飯又多給了20元;最後一次是3月24日,搬了兩小時的醫療器材,收入整100元。剩下的時間,他基本上是在墓園、街頭和地鐵站廣場之間來回晃蕩。

往常每個月,朱路路還會有300元的額外收入,那是父母打給他買抗癲癇藥的。但直到整個三月過完,朱路路還是沒有收到這筆錢。別人問起,他囁嚅著抱怨:“那個哩……前兩天我媽在電話裡說,讓我去死。”
一位年長的人聽完教育道:“你都這麽大了,還想讓父母管到啥時候?不讓你管就不錯了。”朱路路默不作聲。過了片刻,他對另外一個人張了口:“我跟家裡人的關係就像開火車一樣,不是一條線路,它跑不到一塊兒去。”
2019年春節,朱路路是在南京過的。他買了點熟食,在古墓邊擺了幾道菜。陪他一起留守的,還有一位74歲、自稱是在“修道”的江西人。
江西人名叫王奉安,平時也住在亭子下的長廊裡。區別在於,他靠撿廢品為生,偶爾還會有好心人送來衣物和吃食。腳上那雙40碼的361°運動鞋,就是一位遊客向他問了碼數,特意買下送來的。
兒子們打電話關心,王奉安很少會接,“你管你的,我管我的”。王奉安甚至想在今年斷絕這種往來,“我不跟你講話,不要你的錢,看看會不會成功”。
除了家庭特殊和經歷奇特的人,流落至此的也有普通打工族。陳廣虎的家在安徽馬鞍山,距離南京只有幾十公里,近到“騎著電動車就可以回去”。每年收完水稻、老家沒活乾的時候,他就跑來南京打短工,一個月收入三四千元。
為了省錢,陳廣虎的住宿問題也經常在墓園裡解決。有時候,他會跑到不遠處的鼓樓醫院,和患者家屬一樣,在走廊上打地鋪睡。除此之外,肯德基也是一個好去處。唯一要注意的是,早晨必須在五點多鍾醒來,否則就會被保安趕。

這些年在外露宿的經歷,陳廣虎從來沒告訴過妻子和孩子。“這哪能讓他們知道呢?”
沒活乾的時候,他就一個人到街上閑逛,最多一天走了8萬多步,微信運動經常佔領封面。每次穿過燈紅酒綠的城市,陳廣虎只是邊走邊看,不會通過吃飯以外的任何消費去嘗試融入。“很明顯,我和這裡遠得不是一點半點。”
“窮到連鬼都不怕了”
4月2日這天,朱路路站在地鐵站廣場上算了算,意識到自己最近一次乾活已經是8天前,“銀行卡裡只剩下幾百塊”。具體數字是多少,他沒有透露,隻說過去半年多一直處於缺錢狀態。
朱路路也曾想過改變。3月中旬的時候,他聽說有家電子廠在招人,一個月算上加班費能拿4000多元,便打算去做份長期工。
結果沒出三天,他就吵著要離開。“天天過閘機門,什麽都沒帶它就是響,響了就要重新過,我急眼了就不幹了。”事實上,除了管理規定,還有一個原因是,他進廠後發現收入似乎達不到被承諾的那麽多。
就這樣,朱路路又回到了街頭。沒有固定的工作,他要考慮節流,盡可能地減少生活成本。吃住問題排在首位。但比起吃飯,住宿對他來說更好解決,將就一下也能過得去。
距離福清公主墓不到一公里遠的安德門地鐵站附近,隱藏著一些廉價旅館。它們沒有安裝標牌,只能從磚牆上隱約辨認出用白色顏料塗抹的“住宿”兩個字。
在一家廉價旅館,十幾平方米的屋子裡滿滿當當地塞進5個鐵架床,兩個房間一共20張床位。上鋪收費12元,下鋪要貴上3元。就算所有床位住滿,一天營收也不過270元。

床鋪上的被子花色不一,全部敞開在床上,看起來已經有段時間沒有洗過。屋頂還能發現雨天漏水的痕跡。這裡無需遵循禁煙規定,需不需要登記身份證,全在於老闆的心情。
為了省錢,一些農民工連這樣的旅館也不願去住。十幾塊錢拿來買飯吃、買酒喝,對他們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到了夏天,露宿在外的成本開始提升。睡覺之前,朱路路會在頭和腳的位置各點一盤蚊香,夜裡若是被咬醒,還得續上兩盤新的。“買一盒蚊香,基本上兩三天就能用完。”除了蚊子,蟑螂、蜈蚣也不時和他碰面。晚上失眠的時候,他就爬起來抽幾支三塊五毛錢一包的一品梅香煙。“這煙勁兒大,我睡不著了才抽。”
相比之下,冬天的大風和低溫對農民工們來說更難熬。王奉安上了年紀,尤其怕冷。他有些得意地告訴記者,自己一共儲備了7條棉被。下雪的時候,身下鋪三層,上面再蓋四層,出門還有兩身軍大衣可以穿。這些物資,王奉安已經記不清哪些來自城管,哪些來自社區,他統一歸結為“國家給的”。有了這些,他能過得舒坦許多。
不考慮惡劣氣象的影響,亭子下的環境其實不算太差,最大的好處在於開闊、通風。福清公主墓由於處在地下,常年見不到太陽,空氣要差得多,墓室內還長有一些黴菌。
內蒙古小夥似乎並不在意這些。有網友表示同情的同時開起玩笑,說他“窮到連鬼都不怕了”。他不屑地反問道:“能有啥事?啥也沒有。”

從穿著上看,內蒙古小夥確實有些寒酸:外衣右側已經開裂,星星點點的棉絮露了出來,腳上的鞋子破了好幾個洞。
朱路路觀察到,沒活兒的時候,內蒙古小夥白天也待在墓裡,到了飯點才出來買飯,吃完又回去,躺在石棺床上繼續玩手機。他由此得出一個結論:“這人也懶得很,什麽時候沒錢了才出來乾活,有錢就不幹了。”
“也”字背後的現實是,大部分農民工等活兒的時間要比乾活的時間長。
今天又是沒老闆
農民工選擇住在福清公主墓旁邊,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它離安德門地鐵站不遠。地鐵站附近原本有一個勞務市場,2017年底遷到了十幾公里外的地方。很多人習慣了這裡,不願再跑遠。
等活兒的人也記不大清楚,用工需求大幅減少是從哪一年開始的。在他們看來,以前的局面是師傅搶手,如今成了老闆難求。陳廣虎形容,“每次有老闆來,人就跟馬蜂一樣轟上去了”。為了搶活,有人把老闆圍起來,“像抱小孩一樣抱住”;有人不顧勸阻,硬是擠上了老闆的車;肢體衝突也不是沒有發生過。朱路路覺得,正是這些事情把老闆們搞怕了,很多人不願意來。

技術活兒少了,但需求總還在,這時候就顯現出好活兒與孬活兒的區別。有酒店來招臨時洗碗工,4個小時給80元,算下來時薪也不低,很多人嘴上說著可以去,遲遲不見報名。有人騎著電動車來找建築工,立馬兒吸引了一大批人圍上去。最終,一位被挑中的大工坐上了車,沒地方可坐的小工只能背著包,一路跟在車後面跑。
日薪不超過150元的工地活兒,朱路路已經很少去,他覺得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他有自己的選擇標準,但這個標準是靈活可變的,如果身上沒錢了,一切另說。
71歲的劉佔強也在等待好活兒。他是這群農民工裡年齡最大的,從安徽來到南京已經兩年,雖然身體看上去很硬朗,年齡問題還是對他有影響。“一個月零七天了,我一直沒找到活兒。”他的生活成本已經壓縮到極致:一天兩個饅頭,只要2塊4毛錢。熱水可以到肯德基去接,不要錢。
有一次,他差點就撈到好活兒。那是一家自來水廠來招工,找人給沉澱池撈淤泥,一個月5000元,管住不管吃。最終,四位農民工得到了這份工作,其中一位已經60多歲。劉佔強感到很可惜,他當時就站在不遠的地方,趕到時已經錯過了好機會。
又一個沒等到活兒的夜晚,劉佔強跟工友們坐在馬路牙子上閑聊。工友為他算了筆账:“辛辛苦苦種一畝地,能收八九百斤糧食,一斤糧食1塊多錢,除去農藥、化肥、種子,一年下來比不上人家打工一個月。”這就是他們寧願乾等著,也不願回家務農的原因。既然是等,就要嚴格控制損耗。“你說,農民工不睡馬路,誰睡馬路呢?”
他們中的一些人,原本也睡在福清公主墓旁邊的亭子下。媒體報導後,城管、社區等部門來到墓園巡查,對夜晚留宿的農民工予以勸離。有人把鋪蓋搬到了地鐵站旁邊的公廁下,那裡的房簷伸出來一截,簷下剛好有一圈平地。對無處可睡的人來說,已經是個不錯的棲身之所。
農民工搬走後,墓園的長亭下顯得有些冷清。四周的柱子上還留著他們待過的痕跡。靠近古墓的一側,有人用粉筆寫了一段對白:你想幹什麽?我想當總統。對面柱子上的七個字看起來更現實:今天又是沒老闆。

打遊擊
3月28日下午,一群城管隊員和幾名社區幹部出現在長廊裡。看到旁邊的高壓電塔下掛著毛巾、內褲,欄杆上擺著一些衣物,領頭的人下了命令,要求全部清掉。很快,它們被集中到垃圾桶旁邊。
作為重點清理區域,福清公主墓相當於接受了一次大掃除。墓裡所有的雜物都被清理出來,在墓室門口靠牆壘成一堆。墓室內部被仔細清掃了一遍。作為旅遊景點的公主墓重新恢復整潔。

農民工們明顯感覺到,這一次行動的力度要比以前大很多。
幾位得到消息的農民工趕忙轉移。有人心存僥幸,把被褥藏到了樹叢裡,也有人把行李挪到了亭子背面。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忍受臭味。平日裡,一些農民工習慣在隱蔽處大小便,而不願去幾十米外的廁所。如今,氣味反過來熏到了他們。
每天來晨練的市民鄧堯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他發現亭子下的農民工少了很多。
提起墓園裡的農民工, 負責這一區域的街道城管科科長陳德平很頭疼。他告訴記者,之前有人在亭子下生火做飯,城管部門在處理時,“有人拿出一把刀,威脅我們隊員。”“挨罵就更常見了。”
類似的事情,鄧府山社區黨支部書記譚寧也曾聽說過。“有農民工拿著刀,在附近一個社區門口堵了兩天。”原因是,“你勸他走,他認為你動了他的窩”。譚寧對自己的安全問題有過擔心,她知道勸離工作面臨著一定的危險。社區為此專門作出規定:女同志去巡查時,必須有人陪同。
譚寧說,墓園公共空間被侵佔的現象,之前就已經存在。墓園下方至今立著一塊告示牌,牌子上稱呼農民工為“民工兄弟”,勸告他們“自覺遵守文物保護法規,不再將墓園作為住宿生活的場所”,落款時間是2016年5月。

如今回過頭看,這三年間情況並未好轉。幾個部門的負責人不約而同地提到“打遊擊”的說法,“你來他走,你走了他又來了”。
冬天下大雪的時候,社區和民政部門曾為墓園裡的農民工送過大衣和棉被,也聯繫過一些廉價賓館,請農民工們免費住宿,但一些人始終持抗拒態度。“把他們送去救助站,也是一下車就跑了。”譚寧覺得,很多農民工並不在乎生活質量能否得到保障,他們喜歡的是在街頭的自由。想乾活的時候乾活,不想乾活就閑著。
譚寧告訴記者,雨花台區勞動局正在制定計劃,以後每周四、周五公布一批專場招聘信息;街道則把招聘信息製作成冊子,寫清楚公交線路,看到農民工就發放。他們希望通過就業這個關鍵點來解決問題。
文保困局
空間資源的矛盾,因為文物的存在多了一重複雜性。就福清公主墓來說,保民生還是保文物,雖然不是一道單選題,但在現實面前,解決起來並不容易。
部分農民工對文物保護認識有限。拿朱路路來說,他雖然知道墓是舊的,但認為“那是裝飾品,主要是給遊客看的”。一會兒又說墓是假的,“不敢把真墓放在這邊,放在這兒會被盜的”。
朱路路的依據是,福清公主墓並非一開始就在這座墓園裡。在他的理解中,從別處遷過來的古墓算不上多麽好的文物。
實際上,墓確實是從別處遷移過來的。1998年,南京市文物部門對福清公主墓進行考古發掘。由於早年間屢遭盜擾,墓內出土的文物相當有限,但墓葬本身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它在當時被認定為我國發現並保留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結構複雜、規格宏大的明代公主墓。換句話說,整座墓就相當於一件大型文物。
2000年,經專家和南京市文物局決定,福清公主墓易地重建,搬到了雨花台區的鄧府山石刻藝術園。
雨花台區文保所所長台健勝回憶,福清公主墓出土時隻發現了金紐扣等少數文物,但墓磚上刻有字,“和明城牆一樣,都是工部督造”,其本身也是文物。當初選擇遷移重建,納入鄧府山石刻園,是為了公益性展示。“向老百姓敞開,提供一個休閑嬉戲、尋古探幽的場所。”
易地重建後,福清公主墓的規格也在提升。2006年,它從區級文物保護部門升級為南京市文物保護部門。

台健勝告訴記者,在一年兩次的巡查中,文保所沒有發現墓園內的文物有明顯的人為損傷,“只有風化、剝落等自然損耗”。文物保護與農民工問題產生碰撞,他認為是管理缺失的結果。
“疏永遠好於堵,農民工本身屬於弱勢群體,不能采取強製手段。”對於有人建議在古墓邊設立欄杆等做法,他也明確反對,因為古墓就是文物本體,不能在上面打孔。“只能通過管理去改變。”
新一輪的媒體報導,給文保所在內的有關部門帶來不小的壓力,他們已經籌劃出新的解決辦法。正在實施的,是按照屬地管理原則,由警察、城管、街道組成工作小組,進行24小時的勸離。之後還將增設崗亭,對整個園區引入物業,“進行全面、長效的管理”。

“安德門個個是人才”
被勸離的農民工,又流回到安德門地鐵站旁邊的廣場上。朱路路早就把鋪蓋轉移了過去,王奉安要稍晚幾天。夜裡城管人員離開後,他偷偷溜到古墓的亭子下睡過四晚。直到第五天,才放棄像躲貓貓一樣的睡前“遊戲”。
午後,廣場上的氣氛變得安詳。有人坐在小馬扎上看書,書名叫《一隻獵雕的遭遇》;有人抱著一瓶30元的白酒,打開喝了一口又擰緊蓋子;還有人頂著陽光湊在一個唱戲機螢幕前,喇叭裡傳出電視劇《亮劍》的聲音。

唱戲機是這位農民工十幾天前花費300元購買的,“現在沒錢吃飯了,想200塊錢賣掉”。有人出價70元,他沒捨得賣。
人聚到一起後,物品便以不同的方式流動著。一個胖女人不知道從哪裡搞來幾條活魚,在廣場上逢人就問要不要。有農民工買了一條,幾分鐘後有點後悔,問她:“你這魚還能活多久?”得到的回答是“你問魚去。”有位老太太抱來一堆衣服,朱路路看了看,花五塊錢買了件黃色的衝鋒衣,衣服上印著“XX外賣”四個字。一家餐館中午的飯菜沒賣完,下午便以五元一盒的價格填進了幾位農民工的肚子。
夜幕降臨後,廣場上走過一名女子,朱路路扭過頭小聲嘀咕,“她就是乾那個的”。
朱路路說,曾經有位中年男人找到他,掏出300塊錢叫他去附近的公園“玩”。到了之後才發現對方是想讓他幫忙解決生理問題,“我一腳給他踹到台階下面去了”。
朱路路不是沒有拿身體換過錢,他的方式是獻血小板。一個月2次,每次可以拿到100塊錢現金、2張蔬果卡和一些吃的。最後一次去的時候,他突然犯了癲癇,清醒後被人告知“以後不要再來了”。
通過各種方式掙來的錢,相當一部分被換成了酒。對於大部分農民工來說,即使身上再沒錢,酒也是不能少的。
張平是廣場上有名的酒鬼之一。沒活兒的時候,他每天中午都要喝上半斤白酒。3月30日下午三點,張平已經躺倒在馬路邊的停車位上,吐出來的汙穢流出去幾米遠。
第二天酒醒之後,張平不願再提起醉酒的事。他擺擺手,直說丟人丟大了。他有些後悔昨天喝過了一斤,“白酒不能多喝,喝多就成傻子了”。他多次看到有人喝完酒後,沒有任何緣由就將玻璃瓶摔碎在地上。清潔工已經習慣等人散去再過去打掃,不會發出一點怨言。“跟盲流沒有道理可講。”
平時,張平算是農民工圈子裡受敬重的那一類人。他愛好書法,每天早晨都要給自己寫一個招牌。老家開封的他,習慣在“瓦工”前面加上“東京汴梁”四個字。手機號碼也被他設計成花式。一個人在外,張平懂得如何讓生活多點樂趣。但有一樣東西,從來都是他的心病,那就是家。“不能談家,我的悲劇太大。”張平已經14年沒回過家,打工時碰見一位老鄉,他也只是問了問房子的情況。“只要房子沒塌就行了。”最近,他還作了一首詩“滿天星頭離走屋,兩輪駕我耳風呼。安德大街是終點,希望聘臨貴公司”,題目叫《吟早》。

捨不得買紙,張平就四處搜集可以寫字的東西。肯德基裡別人沒用過的餐巾紙、垃圾桶旁被丟棄的泡沫廣告板、撿來的中華煙煙盒和快遞紙袋,全被他寫上了毛筆字。有工友需要寫工作介紹,他的收費是10元。
除了張平這樣的“書法家”,廣場上還有“科學家”和“演說家”。
安徽人盧劍自稱曾因打架、做違法生意入獄六年。在獄中,他有空就看書,從醫學、哲學到科學一樣不落。出獄後,他想要將沉澱下來的一些想法變成現實。從時速3000公里的雙層超級高鐵,到一井多廂的超級電梯,再到20年之內實現6小時全國直達的超級物流,都在盧劍的計劃之列。
盧劍說,他想通過參加江蘇衛視《夢想成真》來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最近他才知道,這檔節目在2012年開播不久後就已停播。
公廁旁邊,風頭正聚集到一名年輕男子身上。從哥倫布到歐洲宗教,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越南戰爭,他慷慨激昂,嘴裡像機關槍一樣吐個不停。
一旁的朱路路聽得直發笑,他很早就聽過一句話——安德門的農民工,個個都是人才。還有一句是“安德門這地方,十個人裡有八個鬼”。朱路路承認,自己也算在其中。
聽了一會兒“演說”後,朱路路捧起手機,連上了公廁裡的免費Wi-Fi。睡覺前,他想看幾集86版的《西遊記》。下載列表中,還有電視劇《飛虎隊》和趙本山小品大全。
有人在離開前留下一句“回家去嘍”,朱路路笑著對那人說:“回什麽家呢?安德門不是你的家啊。”
(文中王奉安、陳廣虎、劉佔強、鄧堯、盧劍為化名。)